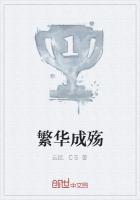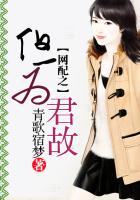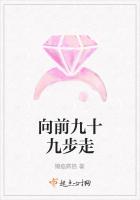解放前同他师傅来村里擀毡,因留恋一位寡妇,就留下了。一位光棍老头去世了,梁毡匠就住了他的一孔窑洞,登记户口时,他自称是光棍老头的儿子,就留驻在村里,成了一位村民。
听人说,梁毡匠在老家其实是有老婆的,他赌博输了钱,就把老婆哄到一个几十里外的村子,将她卖了。然后就投奔一位擀毡师傅,远走异乡了。
梁毡匠在村里口碑不太好。他给村民擀毡,扛了弹羊毛用的大弓,背了水壶油壶等一应家什,一进门就拖着唱腔,用陕西话说道:“吃好点,喝好点,活给你做好点!”言下之意,吃喝招待不周,他就会做手脚。一些贫苦的农民,好不容易积攒下一点羊毛,能擀两条毡子,因没有能力招待好毡匠,所擀的毡在炕上铺了两个月就开了一个大洞。
梁毡匠到我们村里一直没有结婚。他孤身独居,平时也和村人甚少来往。闲了,就扛起一把铁锹,信马由缰地在山野里乱走。我们这里有吃黄老鼠的习俗,他似乎是去挖老鼠,但也没有见他挖出一只两只黄老鼠拿回来。
谁知天缘凑巧,低标准时候的一个秋天,早晨起来,冷雾弥漫、冻雨潇潇。梁毡匠仍旧扛了铁锹,到山野里乱走。他来到了马家台子(名曰马家台子,其实是我们村通往山外的一条便道),眼前一亮,就发现有个人躺在地上。梁毡匠跑过去,扶起她,见是一个中年女人。她穿着一件破旧的棉袄,已经湿透了。一块红色头巾,包裹着她的头脸、鼻孔。嘴角都结了微霜。她蜷缩在冰冷的土地上,气息已经微弱。她大约是饿昏了。梁毡匠二话不说,背起她就回了家,他用热米汤救活了她。
之后,人们了解到,那女人姓马,宁夏固原人,回族,逃荒至此。在村人的撮合下,她竟然同意住下,和梁毡匠做起了夫妻。后来,村里就流行起一首民谣性质的顺口溜:
梁毡匠,真能行,
马家台子拾了个人,
晚上回来人摞人,
第二年生了梁登明。
梁毡匠有了儿子,小窑洞的烟囱里,在傍晚,在黄昏,袅袅地升起了炊烟,婴儿的啼哭和马氏匆忙的背影在这小窑洞里成就了生活的温馨和甜蜜。常有人看见,梁毡匠端起漂满红油辣子的大海碗,坐在门口吸溜吸溜地吃面。他还穿上了新做的棉袄、布鞋,脸庞渗出了好看的红润。他似乎年轻了,村人再也没有看见他扛着铁锹在山野里乱走。
平静的生活持续了两年。有一天早上,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传遍了全村。四个戴着白帽帽的回族男人驾着一辆马车,突然出现在村里。人们猜测,马氏原先的男人找她来了。
梁毡匠的小院、垴畔围满了看热闹的村人。回族男人将马氏五花大绑了,抬起来,扔在马车上。梁毡匠的儿子目睹着这人间发生的一切,清澈的眸子里闪烁着惶恐与惊疑,他不停地挥动着小手,喊着要妈妈。梁毡匠蹲在灶火圪里悄然垂泪,不知所措,也没有表现出任何英雄气概。那为首的回族男人,指着他说:“老梁,你老婊子儿听着,马氏是我的老婆,不许你来找她!”说完,一把揪起梁毡匠的衣领,“啪啪”就是两个耳光。打完,驾着马车,轰隆隆地离开了,远处传来了马氏撕心裂肺的哭喊……
梁毡匠失去了老婆,生活复又陷入死寂、平淡。小窑洞的垴畔上不见了往日缭绕的炊烟,中年鳏夫带着一个刚满周岁的孩子,冰锅冷灶,苦捱时日。马氏在村里生活了两年多时间,和一些村妇有些交往,人们都认为她是憨厚诚实的人。她被抢回,在村里还是赢得了不少同情。所以经常有农妇送一罐羊奶、一碗小米,接济了毡匠父子,使他的儿子能够成长起来。
梁毡匠后来和早先那位寡妇又有了来往。那寡妇弄走了他半生擀毡积存的一点钱财,使他一贫如洗,但最后又抛弃了他。
毡匠的儿子梁登明和我是小学同学。小学毕业后,他就回村务农了,也没有去考初中。
有一次,他和父亲因为一件琐事吵了一架。大约是对父亲的一些做法有意见,情急之中,他把毡匠推了一把,毡匠被推倒在地上,等儿子将他扶起时,他已断了气。
秃老刘
秃老刘,大名刘德勋,四川绵阳人,是一位老红军。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在一次战役中,他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随后辗转流落到这里。
我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再去找部队。有时问起,秃老刘都含含糊糊、闪烁其词,不愿正面回答。我怀疑他是革命意志衰退,或者年轻时陷入温柔之乡,不愿再过艰苦生活了吧?!柳宗元说过,流徙之人,不宜在过于清冷之处久居。同样,一个革命者也不宜沉溺于温柔之乡。
他在我们村里成了家,老婆是此地一位“著名”土匪的压寨夫人,名叫李小花。李小花其实也是贫苦农民的女儿,年轻时有些姿色。我们这里,解放前,土匪劫路、绑票的事频发。李小花十五岁那年,村里来了土匪。她母亲在慌乱中,把锅黑给她脸上抹了一些,谁知那为首的土匪还是透过脸蛋上的锅黑,发现了她的绝世姿容,就把她绑在马背上带走了。1936年红军解放了盐池,这股土匪被消灭,李小花被共产党的干部送回了原籍。原来风姿绰约的村姑变成了风尘压身的少妇。秃老刘那时还年轻,他仰慕李小花的姿容,托人说了媒,就把她娶了回来。尽管夫妻感情很好,但结婚多年,也没有子嗣。秃老刘四十岁的时候,用一头牛在内蒙鄂托克旗换了一个男孩,名叫满满。满满长大了,娶妻生子,从此刘家才人丁兴旺。秃老刘为人谦逊随和。这个家庭尽管结构奇特,但却和谐美满,从来也没听见刘家的人因为什么吵过嘴。
秃老刘是村里的能人。他精明能干,农活里耕、锄、磨、耪、割样样在行。他会弹口弦子、拉二胡,会剪窗花。他剪的窗花,技艺之精湛,村里的姑娘们也自叹不如。他还是远近闻名的土匠、泥瓦匠,甚至还能给人看“风水”。
地处宁南山区的黄土高原是个苦焦地方,人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地终日劳作,也不一定能够温饱。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是人们第一位的追求,所以精神上就容易憔悴,容易褴褛,容易麻木。秃老刘和这里的农民有所不同,他身上保留着童心和童趣。在我的记忆中,他很会哄着我们孩子玩。冬天里,他教我们用鲁迅小说《故乡》里闰土的办法去捕鸟。大雪封山的时候,他在场院里扫出一片空地,撒上荞麦、糜子。然后找来一把竹筛,在一根木棒上拴上细长的绳子,用细棒顶起竹筛,用手牵着绳子远远地等着。饿极了的野鸽、乌鸦、麻雀沙鸡们蜂拥而至,秃老刘把握好时机,一声令下,我们就拉了绳子,竹筛倒下去,就把那些鸟雀们扣在了底下。有时收获颇丰,一次竟能捕到十几只。秃老刘高兴地用手抚摸着光头,咧开大嘴酣畅淋漓地笑着,俨然一个五岁的顽童。
生产队的时候,秃老刘最喜欢晚上看场。场院里堆满了正在打碾的糜谷、荞麦,晚上须有人看守。每逢这样的任务下来,秃老刘总是第一个报名。我们一群孩子,最喜欢跟他看场。夜幕降临了,牛羊归圈,周围的大山陷入沉寂,一弯新月从山背后升起,挂在冰冷的山顶。场院里留下一个看守。秃老刘拿了手电、毛毡、木棍,带着我们几个大点的孩子,蹑手蹑脚地来到门前的深沟。几十米的深沟里,有山洪冲刷出的水洞,冬天里成群的野鸽就栖息在洞里。我们悄无声息地入洞,用毛毡堵了洞口,然后打开手电,野鸽们顿时惊起,“刷——轰——”
洞里的野鸽此起彼伏,或互相撞击,或撞在洞壁上、撞在人身上。羽毛、鸽粪、灰尘在洞中翻飞。翅膀的扇动声、惊恐中的鸣叫声,形成一片混乱。秃老刘激动了,他模仿着神话小说里的口吻喊道:“小的们,给我动起来!”我们几个立时抡起木棍打将起来。酣战过后,遍地是野鸽的尸体:有的在扑腾,有的在流血,有的在呻吟……我们取来口袋,装了,抬到场院里。秃老刘视察了战利品,笑道:“小的们,一人几只,拿回家去吧!”于是场院里沉浸在喜悦的气氛中。
在夏夜里看场,就没有这样的好事了。但秃老刘还有绝活,给我们说书。
他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说话啷个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他讲起了《三国演义》;“说话啷个有一个读书人,深夜在古庙里用功,突然……”他讲起了《聊斋志异》。
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古典小说中的场景、细节、人物,经他用四川话轻轻加以渲染,就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金戈、铁马、箭雨呼啸而至,狐仙、鬼怪、书生翩然而来……他讲得情趣盎然,我们听得如醉如痴。故事正到了关键紧要处,秃老刘干咳两声,“小的们,给我点锅烟。”他接过烟锅,猛吸一口,一股浓烈的旱烟从他的嘴角、鼻孔袅袅地溢出,“哈咝——”他长长地出口气。故事马上就要继续了,他却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明晚分解。直让我们遗憾得捶胸顿足,但心里充满了快乐。
多少个夜晚,我们围坐在他身旁,听他讲《水浒传》,讲《西游记》,讲《说岳全传》,讲《三侠五义》……不知不觉间,晨露沾衣,东方既白。在生活单调枯寂的乡村,他在我们眼前打开了一个个五彩缤纷的世界,让我们饥渴的心灵得到慰藉和滋润,感到精神的清凉。这是我最早接受的有关文学的教育,至今无法忘怀。我们村里的几个孩子,后来都报考了大学的中文系,终生从事着与文学有关的工作,或许都是受了他的影响。呜呼,“先生”之泽远矣。
1979年,我离开了村子,就再也没有见过秃老刘。1998年的一天,我同县里一位领导到村里扶贫,秃老刘的孙子李继业那时是村党支部书记。晚上住下,他向我介绍了一些爷爷的情况:秃老刘享了高寿,八十六岁时,因劳动后受寒,卧病不起。临终时头脑依然十分清晰,他把孙子叫到跟前,嘱托了一些后事。还说,左腿的内裤裤脚不平,孙子伸手替他拉平,随后他安然而去,脸上似乎还挂着淡淡的笑容。我听了,一夜无眠,心里充满了感叹与唏嘘。
第二天下午,李继业陪我到了秃老刘的坟前,他说:“爷爷,你看谁来看你来了!”我在坟头献上一束野花,不禁泪流满面。
墓草萋萋,落照昏黄,话犹在耳,斯人邈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