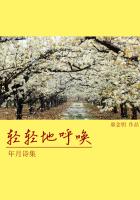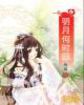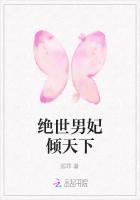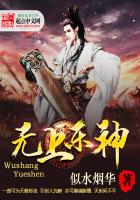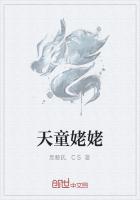1970年,我在村里的小学校读一年级。
那一年,我经历了记忆中最寒冷的冬天。
刚一入冬,寒冷就席卷了我们这个北方黄土高原上的小村,席卷了这个世界。早晨我还睡在土窑洞的热炕上,母亲就早已起来,开始了她一天的辛勤劳作。她从羊圈里背来一背篓羊粪沫子填在炕洞里,边干边叹息着说:“这么冷的天,学校的教室里又不生火,手脚冻坏了,可怎么过?”她是在替我的学习生活担忧。几天后,母亲就为我缝制了新棉袄、新棉裤,走学校的早晨,她又嘱我穿上“毡窝窝”、“皮滚滚”。
学校的教室是一孔简陋的窑洞,课桌是土坯制成的炕面,被支了起来,凳子是几块木板放在砖砌的土墙上。那时候,贫困乡村的农人们劳作一年,所得果腹犹难,哪有钱买煤炭取暖。
名曰教室,其实与“冰窖”无异。老师摇了摇手里的铃铛,走进了教室。一个学校,三个年级的学生都在同一个教室上课,总共十二个学生,由于天气寒冷,只来了四五个。老师望着瑟缩在桌凳上的我们,叹了口气说,开始上课吧!他转身在身后的黑板上写了几个汉语拼音的韵母,就开始教我们拼读。
天空里阴云密布,飘起了雪花,窑洞里的能见度已经很低。有一个同学,他家远在十几里外的邻村。他每天来回跑几十里路到这所小学校读书。老师就说:雪天路滑,今天的课咱们就上到这儿吧!现在放假,等天晴了,大家再来。我们几个同学“噢——”一声长叫,提着书包,冲出了教室,有一种被解放了的快感。
那雪一直下了三天三夜。开始还是细小的雪沫,三心二意地抛撒着,后来就疯狂起来,飞絮扯棉般扑向这个世界,下得铺天盖地,下得地暗天昏。诗人李白写诗说:“燕山雪花大如席。”这当然是在夸张,但我们这里的雪花,说它大如手掌,还是不过分的。到了第三天早晨,平地里积雪二尺有余,整个世界只剩下白茫茫一片。《水浒传》里这样描写大雪:“凛凛严凝雾气昏,空中祥瑞降纷纷,须臾田野难分路,顷刻千山不见痕。银世界、玉乾坤,望中隐隐接昆仑,若还下到三更后,仿佛填平玉帝门。”这正是这场大雪的真实写照!
雪停了,紧接着北风开始怒吼。早晨起来,满世界又是另外一番情形。大北风就像一个高明的雕塑师,用它锋利的尖刀,刻画出雪的不同形状。处在风口上的积雪,早已被吹得干干净净,裸露出冬日田野的斑驳、草原的苍凉。而田埂边、山峁上、背洼里,积雪却堆积起来,像牛,像马,像大象,像巨龙,像面目狰狞的鬼怪,像白须飘飘的仙人……有的是巨峰上的岩层,刀砍斧劈一般,远望峥嵘峻峭;有的像海洋里的生物,或珊瑚,或海藻,或螺,或贝,纹理清晰,晶莹剔透,栩栩如生。一切都带着狂傲北风的痕迹。
最冷的是雪停风住之后,呼吸还没有从鼻孔里钻出来,就已结了霜。冻得人头皮发麻,小不出便。村里曾有一个笑话,说是一个老光棍半夜里起来,到茅厕里小便,将东西从裤子里掏出来,立马被冻成了冰棒,再就没有扳倒过。这当然是乡村里的幽默。但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夜里出门小便,手冻得连裤子都系不上,只能提着裤子跑回家,却是常事。回到屋里,赶紧将两只红馒头似的小手,伸在热炕的毛毡下,过一会儿才能焐热。曾有一位六旬老汉,有一次赶着毛驴车去看他女儿。女儿嫁到十几里外的邻村。下午天空飘起了雪花,半个小时后,世界就一片迷茫。我们这里属黄土高原的丘陵地带,到处都是形状相似的馒头一样的大小山包。后来,他就迷了路,转了山向。赶着驴车走了一夜,天亮的时候发现自己还在原地徘徊。村里人说他遇上了“迷猴子”,但谁也不知道“迷猴子”长得什么样。总之,他被迷住了。大雪封山的隆冬时刻,他穿着毡靴的双脚被冻得失去了知觉。等人发现时,老汉已不会走路了。他被救了回来,被送到了最近的一家医院,但双脚还是没有保住,被医生锯掉了,成了残废。寒冷的淫威,再一次使乡人们咂舌感叹。
那时,每逢雪天,队里的高音喇叭就传来了队长的声音。他要求饲养员们保护好产羔的母羊,最好弄些麦草铺在羊圈里,麦草暄软而且蓄热,保护羊们母子平安。有一位饲养员别出心裁,他将自己家的旧棉袄、破毛毡拿到羊圈里,披在母羊的身上。结果那个冬天,他饲养管理的羊只成活率最高,第二年春乏时,淘汰得最少。他的先进事迹还上了省报的头条,县委书记还给他戴了大红花。
寒冬里最温馨的一片地方是热炕——羊粪沫子煨热的土炕。它是乡村冬天里的投靠和归宿。热炕让你有家,让你出去了还想着回来。乡人们用热炕去烙他那疲惫的腰身、酸痛的筋骨、困倦的精神。在热炕上“抹纸牌”、“打评活”,在热炕上放纵情欲、生儿育女。我离开乡村二十几年,城里的床和城市的喧嚣已使我身心俱疲,太需要在老家土窑的热炕上松一松筋骨。尽管这热炕有时把人的精神捆绑得苟且、卑琐,但我依然十分想念那使人舒坦得想哭的感觉,我需要这种感觉来软化血管,来滋养灵魂。
坦率地说,我喜欢寒冷的冬天。冬天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热度。冬天让我们向往温暖,懂得温暖,珍惜温暖。它使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收拢起来,不至于飘散。聚在热炕上的人们,会暂时忘却蝇营狗苟,尔虞我诈。一杯烧酒、一块羊肉,酒酣耳热之后,或许还有心灵的坦诚与沟通,还有仇恨的消除、误会的化解。“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是一种境界;“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是一种境界。这都很美。但《红楼梦》里“白茫茫一片真干净”更是一种境界,它让世界暂时没有了污浊和龌龊,让人的心灵变得澄澈、透明。
我常想,如果一个冬天没有雪,那是什么冬天;如果冬天不冷,或者冷得不够味,冷得没有力度,那还算是什么冬天。
冬天就应该有个冬天的样子,让寒冷留在人的记忆中,让雪花和坚冰留在人的记忆中;让料峭如尖刀的寒风在温暖的时候,吹过记忆的湖面,提醒人们,让人们感叹:那个冬天,那时候的冬天啊!
许多年都没有像样的冬天了。有时候,整个一个冬天,都没有雪花飘落,简直是干冬或者是暖冬。北风卷着黄沙在肆虐,空气里弥漫着沙尘和病菌,瘟疫也因而流行开来。
2006年11月上旬,我坐车经过银川黄河大轿,我从车窗里瞥了一眼黄河,本该是玉洁冰清的河面,此时依然是波涛汹涌,有快艇载着游人在河面上飞驰,溅起一串串浑浊的浪花,似乎在告诉我,这里是深秋。公园里是什么情景呢?高大挺拔的杨树,黄叶一片两片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树枝,在悠然飘落,树身的皮肤下却隐约着青翠,不见冬日的苍黑。湖里的荷叶,依然亭亭玉立般地傲慢着,显出对冬天的不屑。就如老舍先生笔下的济南的冬天,湖水“不但不结冰,倒反在绿萍上冒着点热气,水藻真绿,把终年储蓄的绿色全拿出来了”。游人们脱了毛衣,提在手里,看出他们脸颊、额头上有轻轻的汗渍。
好不容易迎来了一场大雪,雪花轻盈得如同三月的杨花柳絮,在空中优哉。它们轻轻地落在地上,顷刻间化成一汪碧水。举目四望:原野上,有的地方雪厚点,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树枝上的积雪一串一串地滑落,经不住轻风的摇撼;街道上到处湿漉漉的,就像狗舔了一般,给人脏兮兮的感觉。这是早春吧?这似乎是“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早春。有报道称,宁夏固原农田里的冬小麦,竟然在十一月里拔节疯长,梨树竟然含苞待放,似乎将要提前迎来繁花满枝的春天。
一直以来,我都有一个心愿,在一个鹅毛大雪的午后,带上我穿着羊毛衫、羽绒服的上初中的女儿来到郊外,来到原野,去踏着雪花漫步。就像俄罗斯诗人叶赛宁描写的那样,我愿将自己的双臂,也嫁接在树枝上,来欢呼这漫天飞雪。我想让女儿在每个冬天都能欣赏“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壮美意境,让她体验一下久违的寒冷的感觉,去寻找心灵的洁净与惬意。但这一切,又怎么能够呢?大雪和寒冷仿佛要远离这个世界。“滴水成冰”、“寒风刺骨”这样的词汇,难道要从现代汉语里消失吗?
我突然想起曾经看到的一篇文章。它说,21世纪人类面临的危机不是战争、瘟疫和天灾,而是人类自身的退化。男人的精液越来越少,越来越稀,以至于丧失生殖的能力。气候在变暖,生存环境在退化。不是有一句名言说,人是环境的产物吗?由此看来,人的退化或许也将难免,有一天人将变得不是人了。远古时代的恐龙,不就变成了化石吗?这样一想,我感到自己的脊背有冷汗沁出,以至浑身每个毛孔都充满了深深的恐惧。
我怀念寒冷,怀念童年时那些冷得让人小不出便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