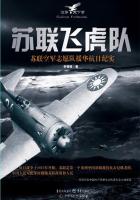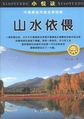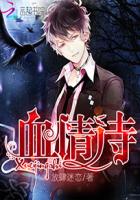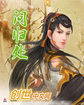但仍然是“木有”。于是这该死的破麦,便数年如一日地毁掉了课堂上的一切。
又及:“周董”当年有首歌,叫《千里之外》。也就是说,即便我的无线巡航半径达到亿万公里,后排的同学仍然要向外太空逃逸的。但没有关系。我的巡航能力对我自己来说是重要的,所以即便发生《三体III·死神永生》的大规模逃逸,那也不过是每一个个体的自由选择、个人理解。总之在讲台上当一只固定的狗熊是不爽的。我的航母群和歼星舰群不承认限制。
“古板的老教授”
给本科低班开课如同当幼师——乐在其中。幼师的责任,绝不仅仅是“看住”儿童哟。
当低班生在为学术海绵宝宝欢呼,或痴笑着奔向旋转木马的时候,高班同学则毫无同情心地送来鄙夷的眼神,而发愁于自己脸上的青春学术粉刺了……然而旋转木马是好的,没有旋转木马,就不会有青春美丽痘,就会有童年阴影……青春美丽痘是好的,孕育着文艺青年永不“2B”的希望。所以要一条龙服务。
盼着多年以后,某蜚声海内外的大学者说:“我清楚地记得,在大一第一堂文学概论课上……”小老儿也就跟着青史留名了……
为什么许多同学提到,刚看到文学概论的法定课本后,认为第一节课走进教室的应该是“古板的老教授”呢?是的,这是儿童思维方式,是一切联想的基础,是最真实的。这课是在糟蹋教师的形象,祸首是教材。
一位同学说:“书中多次出现‘我们认为……是片面的或错误的’,我真想问书的作者‘我们’是谁们。是指你们编者,还是包括我们这些读者?”
是的,课本就是这样败坏了学科和教师的形象的。所以教师要自救,并自行拯救学科,要“波士顿倾茶”,要“保尔·瑞维尔星夜飞驰”,要“莱克星顿的枪声”。
看来临到我快退休,白发苍颜还在教文学概论的时候,第一节课我没准儿得穿成谢贤style。这也是被逼的,因为绝不给课本陪绑,做“古板的老教授”。
有些试卷是白匪,我的试卷是红军
如下是一位同学答在答题纸上的话,全文是照抄的。
我这个出题者的姿态显得是否谦虚的问题,此刻,比不上让该同学的voice 让大家听见更重要。
我想起小时候看的革命电影,一支军队救逃难的人民群众于水火,人民群众问:你们是?
一个小战士或排长敬一个真正的军礼回答说:我们是红军,是人民群众的军队。
以下是照抄,姓名隐去。
我想先表达一下对这张卷子的敬意。我说一个故事。
我刚上初一的时候,有次历史考试,最后一题主观题“请谈谈你对李世民这个人的看法”。我当时还小,很不懂事,真的洋洋洒洒写了一堆自己的看法,正反功过,评得比评书都认真。结果发了卷老师说“这题书上最后一段不是有评价吗,怎么不照着写?”我说不是让谈自己的看法吗?(我当时不是装酷,是真不懂事。)老师无奈感叹:“你还是先照抄吧,等上了大学再说。”(我还窃喜自己有上大学的水平。)
所以我来了。感谢命运没有再一次欺骗我。虽然这些自己的看法不怎么样,但完成了我小时候的梦想。
看到这本教材之前我想可能会是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先生站在台上说陈词滥调,我很没放在心上,还选了一个很薄的笔记本做笔记。走走过场嘛。
但从第一节课开始我就明白我没选错中文系。这门课给了我太多,验证了我从小到大的空想、猜想、瞎想,让我想清楚了好多事。比如我初一的时候看完《家》,告诉别人这是一本烂小说,别人都骂我不知天高地厚,因为我说的原因是“写得太没意思”;我现在依然觉得很烂,但我说得出为什么烂。比如“跳出式话语”用得太过啊,人物性格刻画太怪异啊……这时候别人就开始半信半疑了。其实我还是我,我对《家》的评价也没有变,变的就是我手里有了把磨得很快的刀,再加上中文系的牌子。
人是多么容易被忽悠啊。
为了不轻易被人忽悠,这门课对我而言意义重大。我清楚地感受到这半年以来的我对任何人、任何事、任何作品的看法都不再偏重一面,思维可以疯狂的跳跃、肯定、质疑,对质疑本身再质疑……直接导致的结果是,生活比较容易让我开心了。
有一个朋友说自己写过许多小说,然而学了理论就不会写小说了。我说我正相反。我以前很想写但一直写不下去,觉得自己的专长是散文、议论文。在完全放弃了写小说后,偶然间翻到一本戴维·洛奇(他长得真帅)的《小说的艺术》,让我一下子明白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于是我很快地写完了人生中的第一篇小说(写得很差,但总归写完了)——像一个散文集一样。
至于课堂本身,我有一个想法,我想多数人都明白(至少现在明白)一些基本的细读、慢读的道理,但苦于素养不够,很难从一段文字中看出很多东西来。例如这张考卷中的两道材料题,方法是不缺的,关键是材料本身比较难读出许多东西。先生何不多选取一些名篇名段当堂解构呢?(就像《寻梦者》和《革命时期的爱情》,我很喜欢这个。)
纸还有点空余,我还有很多话想说,不过实在是没力气了。看着这些零散、凌乱,没有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文不成文的东西,我还是很开心,因为它们,都是属于我的。
一个同学说了点儿什么
在“大学语文”(出给一个理工科院系的)考卷上,一个同学说了点儿什么。我就喜欢同学能说点儿什么,我很感激同学能说点儿什么,我的任务就是鼓励同学能说点儿什么,并放大之。于是我就毫不在意压在我身上的一大堆任务了,中断阅卷,把该同学说的这点儿什么,录入下来。(而且我还要“滥用职权”,利用“本科教务系统”唯一的一个“人性化”功能,来观览一下很有才的同学的玉照。感谢“本科教务系统”的唯一“人性化”功能,使得我能够将150个名字与玉照一一挂钩,寻到这位率真、性情的同学的真容,虽然照片只有1K左右大小,而且都是高三准考证上的,一个个如同存栏的“少年犯”。)
在11题和12题之间挣扎了一下,还是选了这道可能因为“说真话”而“一失足成千古恨”祸及全盘的问题。只是因为我发现自己在大学教育体制下还能“说点什么”,也庆幸自己在“放空”一个学期语文课后发现原来不是考“俳赋的发展”以及“简述李杜诗歌的影响”或者是“诗经有多少篇”这种二百五问题时自己还能“说点什么”。(此处略去一句话。)
语文课的教室地理位置绝佳,左手的窗户外面是一棵大树,每次我都在树荫笼罩下昏昏欲睡,又在不远处工地施工声中醒来,然后在数着更远处的体育馆有多少个窗户中又睡去……我从不认为大学语文仅限于一门课程的学习,正如声音好听的老师(我一度认为这种声音睡觉时听特舒服所以才会睡觉……)。说这只是十多次探讨文学的机会,让大家坐到一起谈谈文学罢了。我是不是该庆幸能在这最后一次“会晤”中替自己申申冤。我一直不太爱“出风头”,也不适应在众多人面前表露自己。这一点我从初中时就想改。我妈还托关系送我去演讲培训,不过太让她老人家失望了。直到大学,我仍然没有逆袭。我还是没能在某一次课堂上说“其实,那个,我声音不错,我来读一下《归园田居》吧”,我也没能在课堂上表达,其实戴望舒是个很会运用色彩的诗人,《寻梦者》里颜色很丰富呀,更没能给大家分享我十分喜爱的勃朗特、托尔斯泰、伍尔芙。
还好不是考“诗经有多少篇”,不然可能会纠结于“诗三百”是实数还是虚数的郁闷,在朋友“靠,你们还学语文啊”的羡慕语气中,发现自己虚度时光的懊悔中“抑郁至死”……
这同学很有文采。比如在赞叹“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简洁——“用衣领来代替思念的男子”时说,若是用“装逼的现代文学”来表达同样的意思,也许是“携带着暮霭和星辰的男子,像盗天火的普罗米修斯,只一个不经意间撒落的火种,便让我心底的火势蔓延成火海”。
教学的几块试金石
1.关于office hour。
office hour一周两次,就是考虑到同学们事多,避免时间冲突。若无法习惯于此,倾向于在这两个时段之外突然出现于办公室门前,则缺乏现代意识,过马路也是乱走,在食堂也不排队。谈学问谈民主自由革命也都是不具备素质,瞎掰。
2.关于假谦虚和恭维。
完全不需要。关键是要看是否真的能学会平等讨论,能听得见别人的观点。教师不是税务、城管、工商,不必哄他。
3.忽冷忽热。
一个同学突然求知欲勃发,则需警惕之。因为很可能一两个月后,此人将是躲避你最厉害的,如同躲避麻风病。这叫没长性。
(老盼望着这样的同学有一天会跟我说:“老师,我后来兴趣转向了或忙上别的事了,但您当初确实帮助我走过了成长的一个阶段”……我,会真心感谢这样的同学,让我心头的“第二只靴子”落地,并默默地在心头给如此有始有终的同学打高分……可惜,这样的同学不多见。)
4.逼宫。
在前三者的集大成者基础之上,在毕业论文截止日期前一周才交稿,接着恭维和哭嚷没时间等。
5.出国留学推荐信写成后,再无消息。
把教师当成母猪,生完猪崽儿就不去管它了。
6.综上所述,皆为中华民族的“缺德”部分之文化基因:不把人当人看。
7.接着补充。把教师当半仙、卜者。
无论是想出国还是去香港还是考研,不去看相关机构第一手网站信息,而是道听途说,或者请教师庙算。而建议之在掌握一手资料后欢迎来进行深入探讨后,就再也不出现了。
8.匿名。
电子邮件等皆为匿名,好做到零风险。
9.凡是激情澎湃来信谈对学术如何执著而无具体内容者,须疑之。
我的两副教育面孔
也就是说一副极热,一副极冷。对经历了从第一副向第二副转变的学生来说,则觉寒风彻骨。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圣经·创世纪》)——这头一日的光,是热的,普照在一年级新生的脸颊上和心灵中。他们得到的是鼓励和赞美,不管他们是从来也不敢回答问题的人,还是因为不敢说话所以才发电子邮件问问题但仍然不敢署名的人,还是连匿名电子邮件也不敢发而终日打电子游戏的人。
鼓励和赞美是必要的,因为据莎士比亚说,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而青年人更应该是这样。有极少数的这样的青年,在鼓励和赞美中,迅速地按照“精华”和“灵长”的路子成长,早晚会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以后拄着拐棍,在下面回忆、打盹儿。
但极其不幸的是,由于人性本身的千古问题,以及中华文明的千古问题,以及国际国内的非千古问题,绝大多数同学就一直从来也不敢回答问题,因为不敢说话,所以才发电子邮件问问题,但仍然不敢署名,或者连匿名电子邮件也不敢发而终日打电子游戏,或者沦为学术控——满足于自己追求不食人间烟火的爱智慧幻像而不是实事求是的判断力本身,或者沦为人人网上的大群犬儒——如同孔子说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或者沦为以自恋和YY为内核的假宝玉。
不过这也是千古以来的正常比例。广种薄收才是正经事。所以明知如此,“热”的面孔也是必须的,否则会走向法西斯的专制的精英博雅主义,否则草根中的72贤者无法脱颖而出,否则无法躬行孔子的“因材施教”。
但同时,“冷”的面孔,也是必须的。因为提供安慰剂是不好的,是误人子弟,也是不尊重对方的人格。子曰,“知耻而近乎勇”。禅宗式的当头棒喝,可以当做催化剂,也可以当做试金石,是最后的教育手段。那脆弱的小心灵如果就此躲避,则躲避吧。那脆弱的小心灵如果得到反观自省,则成长吧。
最后,我的“热”,永远是民主自由的而非法西斯专制式“精英博雅”的,即永远以苏格拉底而不是以柏拉图的方式,照向那多数人里面的少数人。你们是光,是世上的盐,是时间的种子,是银河系共和国最后的希望。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路啊路,飘满红罂粟
走吧
路啊路
飘满红罂粟
——北岛
清明节,有任务不能北归,因为为中山大学自主招生人文类的面试拟题并做面试评委。(已经解密,可以说了。)
一整天,详细检阅了太多的高中青春的灵魂和头脑。
我们的读书种子们,可能是世界上最训练有素的,最规矩的,且有着纯正的梦想。他们来自我所熟悉的全国各地名牌高中们……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检阅他们,这就如同时间的回放,回到了现在大学生们的高中时代。
见了这些还差半年就要上大学的高中生的头脑状态,我才意识到我所致力于的大一的文学概论课有多么残酷。我们的中学,能提供出世界上最训练有素、规矩、单纯的头脑。但是,这与通常意义上的should—be大学完全不接轨。大学本身有问题,中学也有问题。在半年后,最残酷的事情就要发生,卡夫卡式的。(不分哪所学校。)而且,问题是无解的。谁认真谁痛苦,师与生都算上。不认真,则是麻木,哀莫大于心死。
我低估了文学概论的痛苦度了。让人头痛欲裂是不人道的。
木马病毒早已植入。绝大多数人在大学入学一百天之内将罹难,切除脑额叶,忘记了半年前自己的样子——我在自主招生现场所看到的样子(木马病毒还没有到发作的之前的日子)。那些春寒料峭的青春,那些真诚地说着“我要为中华的崛起而读书”,或“我要做《在路上》的迪恩”的青春,前者来自农村,后者来自北上广,其实都没什么区别。前者已经被植入了“简单淳朴地去读对的书、做应该做的事”的木马病毒,后者被植入了“优柔寡断、怀疑也终归是无用”的木马病毒。
“当我们来到大学,当我们已然成年。高中时代的自己迅然崩塌的同时却发现自己无力,有心无力,无心无力去构建新的面貌。一切都混沌,但似乎这样也还OK。勤于思考敢于疑问成为屁话。在黑屋子的人未必熟睡,也许也隐隐觉得不妥了,但只是闭眼假寐。反正,管他呢,大家都还没起来。且死不了。似乎这样可以安心再续上刚刚做的梦,但终究也只是假寐。有时会突然怀念高中的单纯,多想回到过去在黑屋中死睡的时刻,不必像现在这样半梦半醒地煎熬。更偏执一点,更无奈一点,就让我们在熟睡中死去好了,究竟也算得安乐死的一种了。眼下算什么呢?知我怀璞玉,未打算雕琢?(笑)”(一位同学的话。)
鲁迅先生所说的“几乎无事的悲剧”;今何在笔下的“中国式青春”?
而鲁迅先生则又说,“你现在大声喊起来,你倒认为对得起他们么?”所以是不近情理的没人性的。但面对着这一切,什么也不说,同样是不近情理的没人性的。
我也不愿意修饰修辞,什么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了。就用这最笨拙的,无可破解的语言吧,也无所谓被理解或不被理解,也不想讨好任何人,也无所谓冒犯任何人。
一切为了我自己的神经系统健康。是的,只是因为面对残酷,需要保护自己的神经系统健康,需要说话,并且不负说话的责任。
What should I do? 或者To be or not to be…是每一个人自己的事情。
文科该怎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