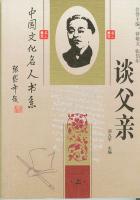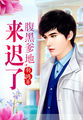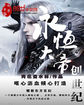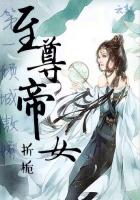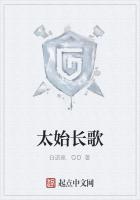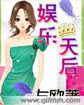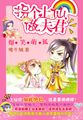果然在当年11月,我们东五中队全体学员意外地进入成都市第三建筑公司当上了建筑工人。市建三公司的领导把我们当成了宝贝,对我们寄予了厚望。三公司工会主席祝谦逊第一次给我们讲话时就说:“公司很看重你们,我们的老工人很多至今都未办工作证,而你们一来就办了工作证就是证明,希望你们好好干!”
到市建三公司后,我们仍是实行军事化管理,集体吃住行。饭前、会前、上工前仍要集合整队唱歌呼口号。“驼背”仍然是我们的中队长。在“驼背”等干部带领下,我们最先参与的劳动是三公司驻地的路面维修工作。
成都市建三公司成立于1965年初,当时三公司本部设在九眼桥附近致民路的一个大杂院内,因组建仅一年,设施设备还相当不完善。
一进公司大门,路面及院坝内场地均很破烂,我们十分卖力地参加修路工作。当路面修好后,全中队集体参加了砌墙、勾缝、抹灰浆等技能培训。技能培训结束后,公司又把我们分成砖工、机械工、抹灰工、架子工等小组,配备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带我们。
我被分到架子工组。当时建筑工地修房用大南竹搭架(不似现在的标准钢构件),带我的师傅姓颜,年龄有四十余岁。有人说:“李小娃个子这么小,学啥子架子工”。颜师傅看来很喜欢我,他说:“别看他个子小,但灵活,爬架子正合适。何况,他以后肯定是要长高的。”见师傅帮我说话,我心里很感激他,下决心要好好干。1965年12月底,我们小组到位于牛市口的红旗铁工厂修厂房,我在高高的脚手架上爬上爬下,干得很是卖劲。
到了1966年2月,不知怎么回事,我们全中队市建三公司正式工人又回到了青训班。当时我年纪小,也不太关心周围的事,并不知道为啥子不当工人又回到青训班,只知道跟着大伙走就是了。后来才听人说:我们这期学员中也是有领导层的(即四期学员部的头头们),因为他们到市委、市府坚决要求说:我们是要上山下乡干革命的,不应留在城里当工人!市委市府领导无奈,各建筑公司领导更是无法。于是,我们在“驼背”等中队干部的带领下,全中队又整齐地回到青训班。
转眼间,1966年春节即将来临,青训班要组织文艺汇演。东五中队以“驼背”为首的几个高六五届大哥们编排出话剧《东山血泪》,反映龙泉山区抓壮丁的故事。剧情是:解放前夕,国民党为扩充兵源抓壮丁,连十三四岁的娃娃也不放过,一个叫“水娃”的娃娃被国民党“丘八”抓了壮丁,因不忍与母亲分离,他多次逃跑后又被抓住并押往前线,后来在半路上,共产党的地下游击队打退了“丘八”,解救下水娃及壮丁们。
“驼背”既是导演、编剧又是演员,他自然是出演共产党游击队的领导。我有幸被”驼背”及其他编剧选为演员出演“水娃”一角。整个剧中水娃除有许多在舞台上逃来逃去、跑上跑下动作外,仅有一个字的台词,即最后被“丘八”们抓住与母亲分离时,演母亲的演员凄惨地大喊:“还我儿子!”此时,水娃则哭着大叫:“妈!”说也奇怪,我无论如何不能入戏,不管“驼背”和导演们如何启发、诱导,我整死也喊不出那个“妈”字。无奈,最后决定在正式演出时,当“我”被两个国民党“丘八”拉着,只管摆出一个挣扎的造型,幕内一人帮我带着哭腔喊出那个要命的“妈”字。
这是我在舞台上扮演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角色。
1966年春节过后,2月11日(农历正月十五)正是过大年的日子,也正好是我17岁生日,我和八名东五中队学员,上山下乡到成都市龙泉区长松公社红花二队当知青。
“驼背”也是那天和我们同时出发下的乡。他到的是与红花二队一山之隔的龙泉区茶店公社石经九队。
石经九队位于龙泉山着名古寺石经寺背后,“驼背”与“鱼皮”(大名王帮跃,也是高65届知青)同在一个知青组,他们的住房正对着石经寺后面巨大的柏树林,“驼背”是他们组的组长。石经九队与我们红花二队仅隔一匹山,从红花二队知青点到“驼背”处仅十余里山路。在下乡的头几年(1966年至1971年)知青之间常串队走人户,石经九队是我走得最勤的知青户。
因为我比较勤快,又喜欢炒菜做饭,每次到“驼背”的知青组时,便帮他们择菜、淘米、洗红苕、做饭炒菜,故很受知青们欢迎。每每吃完饭后,大家便各自端根板凳坐在石经寺后面巨大的柏树林藩下谈天说地,很是愉快。“驼背”、“鱼皮”及其他几个知青,都是高65届的大哥,据说早在七中读高中时,“驼背”与“鱼皮”等人就开始诗词、小说、剧本的创作了。每当他们引经据典、谈古说今大摆龙门阵时,我便是忠实的听众。“驼背”性情稳重、思维活跃,早在那时,他与知青大哥们谈论的话题已经是知青运动的方向与前途,文化大革命的产生、发展与结局,中国农民之命运等大事了。而此时的我对政治问题毫无兴趣,思想认识尚处于混沌未开状态,对于他们忧国忧民的谈论与有时激烈的争论,我完全插不上嘴,仅凝神细听而已。“驼背”组上的知青“鱼皮”常发感叹:“真是奇怪,李小娃一个初中生,咋和我们这些高中生耍得这么好呢?”可能,当忠实的听众、仔细聆听与勤快是其主要原因。
“驼背”与”鱼皮”下乡时,带了很多书籍,从马列大部头到众多中外小说。每次从石经九队走人户后回红花二队时,我都要满载而归,带上几本书回来读。他们那里简直成了我免费借阅的图书馆。在那段时间,我借读了《儒林外史》、《今古奇观》、《悲惨世界》、《约翰·克利斯朵夫》、《少女贞德》、《草原林莽黑旋风》等各种凡是能借到手的中外书籍。
从“驼背”和“鱼皮”等那批高65届的大哥们那里,我获得了很多书本和社会学方面的知识,真是受益匪浅。
刚下乡时,我们这拨来往密切的知青们约定:下乡第一年不回成都。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履行了这一诺言,实际上,我们几个最要好的知青均在农村待了两年多后才回成都耍了一次。那是1968年春节,我们几位到每个知青朋友成都的家中“团年”,吃一顿团年饭。每到一处,各家父母都准备了最好的饭菜,亮出了最好的手艺招待知青朋友,同时,我们还受到各家兄弟姐妹的热情款待。浓浓亲情和无私友情融为一体,那段愉快而幸福的日子真是永世难忘。
1971年初,当我组的知青们因招工离开红花二队,偌大的知青点仅剩我一个人时,石经九队的知青户也仅剩“驼背”一人。
1972春节后的一天,我和“驼背”相约从成都过年后共同返回龙泉。在龙泉街上,有朋友对“驼背”说:“公社干部在找你,可能有好事。”“驼背”颇有预感地对我说:“看来今年你我两人的命运可能有所改变了。”
果然,回到红花二队后,我也得到公社中心校领导通知,调我到凉风二小任代课教师,“驼背”则被调到茶店中学任代课教师。我二人居然同时调离生产队当代课教师,大概这也是一种缘分吧。
我与“驼背”命运相似还有一个明证。我在长松公社卫生院当医生六年后(此前我仅当代课教师一年)的1978年8月,因长松公社不能解决我的城镇户口问题,我顶替提前退休的母亲调回成都二十六中。几乎在同时,“驼背”在茶店中学任教六年后,靠当时所谓的“三抽一”政策(即家有三个知青,可以抽一个知青回城)得以调回农科所工作。
凭着“驼背”的能力、才华和勤奋出色的工作,他很快走上领导岗位,先任农科所畜牧兽医研究所所长,后研究所改为畜牧兽医研究院,“驼背”任院领导至今。
“鱼皮”的大名叫王帮跃,是“驼背”读七中时高中同班同学,下乡时与“驼背”同在一个知青组,“驼背”任组长,“鱼皮”是组员之一。据说,在读高中时,“鱼皮”最爱吃“鱼皮”
花生,故落得一小名“鱼皮”。
“鱼皮”的身材与“驼背”相比矮了许多,整个人也是胖胖的,较圆的脸常常油光光的,大概是“鱼皮”花生吃得多的缘故。他眼睛近视度很高,侧面看他的眼镜片,有无数个一层又一层的圆圈。“鱼皮”的头也是圆圆的,因很早就开始秃顶,擦了无数生发油也无济于事,反而使额头显得又大又光亮。圆圆的额头加上圆圆的油光光的脸,真像是一颗膨胀无数倍的“鱼皮”花生米。
“鱼皮”极好读书与写作,早在高中时代,就开始编剧本、写小说、作诗填词了。他常常手不释卷且不知疲倦地看书,我每一次见“鱼皮”时,他手中未曾离开过书,只要一有空,便在看书。书看得多,头脑里便装满各种各样的知识和稀奇古怪的故事。他记忆力特好,给我讲起书中的故事来眉飞色舞,凡故事中的人物、情节、时间、地点均记得一清二楚,很少有说错的时候。“鱼皮”的谈兴也极浓,大凡谈到他擅长的话题时便滔滔不绝,口若悬河,故事便从嘴里喷薄而出,不给其他人插话的机会。每每讲到高兴之处,“鱼皮”便哈哈大笑,怡然自得,仿佛从无忧愁之事。
“鱼皮”为人豁达大方,和知青朋友在一起从不分彼此,每次大家到他处,他均要慷慨解囊尽力招待知青们。“鱼皮”从来都是高高兴兴、无忧无虑的,他最愉快之时,往往是吃完饭后搬把椅子斜躺着,手捧一本书一面晒太阳一面说:“吃饱了饭晒肚皮,真是快活如神仙也!”
“鱼皮”也常到红花二队来走人户,他来时,我们也是倾其所有,尽量改善伙食接待他。当然我们的条件要差得多,弄出的饮食大不如在他处,但他从未有过闲话。令人奇怪的是,每次他来,几乎都要碰上半夜三更有社员喊我出夜诊(1968年初我即开始当大队赤脚医生)。1969年12月的一天,“鱼皮”来到我处串门,12月的山区夜里已经较寒冷了。我们几个好友摆完龙门阵上床,时间已是12点过了。对门半山坡上一姓都的社员隔着山坡长声吆吆地“喊”我出诊。“鱼皮”看着外面黑沉沉的寒夜,不由自主地发出感叹说:“望山跑死马,何况是晚上,李小娃真是太辛苦了!”
当“鱼皮”了解到我出夜诊的辛苦及“危险”经历后,当即决定将他心爱的小黄狗送给我,陪我出夜诊。“鱼皮”回石经九队那天,我陪他返回顺便去领小黄。回红花二队时“鱼皮”送我,那小黄似乎与我特别有缘,未及旧主人打招呼,它便跟着我一路蹦蹦跳跳地来到红花二队。自从有了小黄,出夜诊也变为愉悦之事了。
小黄对我忠诚有加且情意深重,它陪伴我达三年之久,尤其是在我独守知青屋的那一年,它是我的保护神,也是我形影不离的好伙伴。
小黄的悲惨结局,是我终身遗憾之事。
1972年,当我调到凉风二小任代课教师时,小黄不便带走。“鱼皮”及其他调到龙泉灯泡厂的知青闻讯赶到我家,他们把小黄吊死在树上,将它剥皮熬汤,知青们痛痛快快打了顿牙祭,小黄也物归原主地回到“鱼皮”腹中。我因不忍看他们处理小黄而走得远远的。后来,我没有吃小黄的肉,但仍然喝了它的汤。对于忠实的伙伴小黄的死,至今我常有犯罪的感觉与内疚且深深地自责。
1971年初,龙泉区灯泡厂在全区知青中招工,一下便招走了长松、茶店、大兴三个公社的知青好几十人,“鱼皮”也是其中之一。大部分到厂的知青均作为普通工人,分在烧制玻璃器皿的高温炉前上班。20世纪70年代的灯泡厂刚由街道工业演变为区属企业,设施设备简陋,条件极差。工人劳作几乎是原始作坊式操作,尤其是在制作白炽灯泡时,除手脚并用外,还得用嘴对着空心铁管一面吹气,一面用手不停地旋转,使空心铁管前端沾浮的玻璃液体在吹气及旋转过程中膨大成灯泡状。每次我到灯泡厂看“鱼皮”,走进那条件极为恶劣的高温车间,看着工人们的劳作场面,感觉那环境之差和劳动强度之大,比当知青还苦。
几年以后,龙泉灯泡厂因效益极差而被成都玻璃器皿厂兼并,“鱼皮”得以调到位于成都市同仁路的成都玻璃器皿厂。当时,该厂亟需配方人员,“鱼皮”正好凭借配方技艺,理所当然地成为配方技术员。经多年的磨炼与继续钻研,“鱼皮”在玻璃配方领域已是如鱼得水且小有名气了。他能在原材料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有把握地配制出各种彩色玻璃和技术含量很高的双层乳白色玻璃。在成都玻璃制品厂陈列室内,我看过经“鱼皮”之手配方生产出的各种彩色玻璃器皿,如各种形状的花瓶、各种灯具、茶具及桌案小摆件,其色彩艳丽、五光十色、鲜艳夺目,真是漂亮极了。
如今的“鱼皮”已经退休,有一个聪明儿子的小家庭更显热闹非凡……老喻是我所在的红花二队知青户组长,全名喻小庠。“老喻”是大家对他的尊称。他出身教师世家,父母均为教师,他出生在乡间小学故名小庠。“庠”即学校,“小庠”即小学校。
老喻身材不是很高大,但结实有力。下乡时,他带有一副吊环,那吊环在闭塞的红花山村成为稀罕之物。老喻将吊环挂在知青点大门门厅横梁上。下乡头几周,每当早晚他在吊环上运动时,均要引来无数观众。年长的社员见他在两个小小的圆圈上做引体向上、收腹翻腕转体、十字悬垂等动作时,常惊叹不已、咋舌称赞。当然,老喻的那些动作若与专业运动员相比是微不足道且十分不规范的,但对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从未见过此项运动的闭塞的红花山区社员来说,那已经是十分了不起的了。那些半截子幺爸们看见他的“惊险”动作与运动时肩臂部鼓鼓的肌肉,更是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刚下乡时,我组知青点暂设在蒋家老房子。
蒋家老房子位于红花二队地势较高处的一山凹处,屋基坐西向东,背后的坡地向上延伸与红花三队相连。老房子的右侧是一山坡,山坡上长有许多两人来高的小松树,得名松林坡。沿松林坡往上行约两里,有一陡峭似鱼背的山脊梁,人称青龙埂。顺青龙埂向上行,左边是一深沟名红岩沟,因沟内中部有一堵高大的红岩而得名。红岩上方属龙泉区长松公社红花三队,红岩以下则属简阳县地盘。踏在青龙埂的山脊上,即踩在成都市与简阳县分界线上,左脚是简阳,右脚属成都。
下乡的第二天,生产队长叫我们休息并熟悉环境。知青们未出工,在组长老喻带领下,我们九位知青沿松林坡爬上青龙埂,竟意外发现青龙埂上有一土地庙。所谓土地庙,不过是一柜子般大小的石屋子,石屋内端坐着一对小石人(一男一女)。社员说,这就是土地爷爷和土地娘娘。小石屋门楣上雕刻有花纹及一行字“青龙土地”。站在土地庙前,我们脚踏成都与简阳分界线,很有一番自豪感。我们九人异常兴奋,扯起喉咙大喊:“龙泉山,我们来啦!”喊声在松树坡及红岩沟内久久回转,余音袅袅……蒋家老房子在当时的红花二队,是规模最大、修建得也最为宽阔高大的青堂瓦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