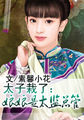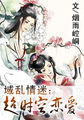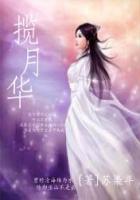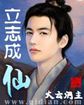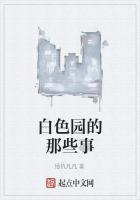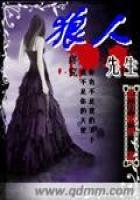但朝中却有人对父王调兵之事颇有不满,董商更是上表道:“如今皇城只有精兵十万,若是那韩王拥兵自重,带着那四十万人打入了皇城又该如何?”子煌对此并没发表意见,只是他的旨意上写的是东北边防虽然吃紧,但西北边防更不能松,料韩王兵务繁重,难以分身,特派钦差将大军领回,韩王不必动劳。
这就相当于在削减父王的兵权。
我实在无法猜测父王会做出什么反应。
又过了三日,商容与史魏书回来了。国库的钱粮大半都送到了前线,他们也无力再去掌管水利的事情,只好将一切交待妥当便还了朝。之后史魏书领了命,又从地方上调集了将近十万人马,送往了前线。
这时,父王的奏折也到了。
早上便听紫宸殿升殿的钟声响了数次,之后便是所有人的翘首等待。
父亲是忠于朝廷的。他所做的事情,都是为永络国好。
我一直是这样想。
从小就是。
但不知为何,自从入了宫闱后,我便有些不自信了。
如今更是心忧,心忧的浑身发抖。
傍晚掌灯时分,便听宫门响动。连忙出去迎,跪在地上,子煌也没说起来,更没去扶我,直到他入了内室小禄子才道:“娘娘您快起来吧,皇上找您呢。”
我心里顿时有了不好的预感。
随着小禄子进去,便见子煌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一本奏折,用力的攥着。
我给他行了礼,就跪在地上,等他说话。
屋子里猛然静的发紧。甚至可以听到自己有些急促的心跳声。
也不知过了多久,才听子煌道:“这是你父王带来的奏折,你……自己看看吧。”他的语气有些叹息,起身扶我,道:“我先回水苑,你若是想清楚了,就过来给我个答复。”
他把走着放到我的手里,漆黑的眸子沉的不像真的。
我只觉得那奏折有些灼热的烫人。
见他走了,我才有些不安的将奏折翻开,细细的读了一遍,便觉的似有一瓢夹着寒冰的凉水从头上浇下,整个人都蒙了。
“臣边关军务紧急,难于脱身,而皇上所要四十万兵马救急滋事重大,臣实难放心交与他人。想臣之女娉兰,自幼随臣戎马练兵,素有雄才大略,实乃军中奇才。边关将士更是不弃娉兰年幼,尊她才智。如今又为皇上之妻,故臣下以为,遣娉兰为都帅,统领大军前往东北最为得当,也表臣一家忠君效国之心……”
奏表“啪嗒”一声摔在了地上,我却是充耳未闻,只浑身酸软的往后退了两步,跌坐在了椅子上。呆愣了许久才猛地回神,身上不由得哆嗦了下,连叫来定儿,道:“你拿着我的玉牌去御史所,把我哥哥叫过来。”
定儿有点犹豫,道:“主子,现在宫门都已经下了匙,您又没皇后的牌碟,这怕是……”
我打断她:“你别管,去就好了。”
她支吾的道了个是,出去了。我却忽地想起了一件事,连忙叫回她:“等等。”踌躇了番才道:“定儿你说的也是,天太晚了,哥哥也不方便入宫,明日再说吧。”
她方下去了。
我重新捡起奏表,坐回了椅子上,心里却波涛彭湃大江翻涌般的难受。
子煌下的调兵之旨,在本质上相当于削了父王的兵权。四十万的大军,一旦调入东北便极有可能有去无还。
而父王的意图也十分明显,他不愿放弃这四十万的人马,但是边疆的形势又容不得他不发兵,也只好将大军交到自家人的手里。
哥哥自是不成了,若是派遣他过去,定会招致满朝人的不满,尤其是董张二相,他们忌惮父王的兵权已久,决不会放弃如此打消父王势力的机会。
所以父王才会发来此等表奏。
我是皇妃,在这个时代女子征戎出战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而我又是王族之人,挂帅出兵自会有种振奋军心的作用。这点董张二相也无法反驳。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乃华家的子女,是将门之后。征战沙场,本是职责所在。最后又加上我父王略有威逼般的奏表,一切都变得理所当然了。
但子煌……他心中又做何感想?
心中思量了许久,也终究只有一叹。
我与他,终究还是无法逃过权势的纠葛。
这夜过得分外漫长。
寿德宫内只剩了两盏孤灯,拉了我的影子轻轻摇晃。领兵打仗,这只在前世电视小说中才有的事情,却没想竟是发生在了我的身上。我该如何是好?
宫中邦鼓打过,已到了四更天。
远远的却听水苑那边传来了幽长的笛音。低沉暗哑,宛若低诉。
我静静的听着,本是烦乱的心绪竟是慢慢的沉淀了下来。想起了自我进宫后的日子,想起了我未能出世的孩子。想起了那揪痛的,心酸的,绝望的一切的一切。
本不该如此的。
我垂了头,深深吸了口气,心中却暗暗下了决定:我会领军出征。会带着那四十万人马,在永络国的疆土上,建立自己的事业。
这不是为了父王,而是为了我自己,为了我与子煌,为了我们以后的日子……
我也无法顾及他会不会怪我。
因为逝子的伤痛,我再也承受不起……
明纪1090年十二月。永络国华氏淑妃娉兰,拜二路援军兵马元帅,领军四十万出征北疆,抵大容国入侵之急。
皇都之内点齐了三万军士,与希琰,商容,史魏书等人往西北进发,没想到刚出皇城,尚未进入锦州,就遇见了父王派遣来的军队。原来父王早已发兵,但压住了消息,未将大军驻扎锦州的情况报回皇城。
父王的用意我大概明白了三分,却不敢妄加推断,只连忙交接了帅印兵符,往东北边境秦城而去。
此次发兵,虽是援军,却兵将众多。
且先不说那四十万精兵,光大将便有六十余人,其中四十多人是从西北随军调集过来的。另外还有副将一百七十人,文官书记三十人。
先锋官是袁跻秉的二儿子袁戎得。今年二十多岁,身长一丈有余,粗膀熊腰,面色黢黑,虽然年纪青青却长满了一腮有如虬龙般的胡子。
此人天生一幅好力气,手底下耍着两只车轮大斧,骁勇善战。只脾气有些暴躁,过于近利。
希琰因是初入朝廷,只作为了我的随身护卫从军而来。史魏书是军师,商容做了压粮官,兼管营中大小事物。
若说笑起来,倒也算是现在的后勤部长了。
大军浩浩荡荡行了五日,已近了北疆。此时年关将近,天气就愈发的严冷。
这时军中忽然来了个意想不到的故人——陆青。
我与他仅在北疆时有过一面之缘,就是那个随着希琰四处打劫官富暴吏的年轻人。
矮矮的个子,胖胖的脸,比希琰小上两三岁,做事总喜欢横冲直撞的,像个小牛犊子。
希琰见到他自是开心,兄弟俩抱在一起又笑又闹的,我这才第一次在出征后看到希琰的笑脸。
也是这个时候,我才明白只有欢笑才适合希琰这样光一样的男子。他随着我太忧伤,许多许多他不该承受的东西,全因着我被他强担了起来。
我对不起他。
过了午后前线来了捷报,细细的览过就交给了史魏书,要他宣读给众将听。
前军大捷,追出大容国兵六十里,并收复了昌舟城。如今正在安抚百姓,整顿军务。打算不日趁胜追击,将另外两座城池一道收回来。
折子里写的十分乐观,我却隐隐觉得有些忧虑,看着堂下众将欢喜的神色,也不好说出来,只得吩咐下去今晚抓紧休息,天明启程。
可到了晚上却睡不安稳,总觉得这个捷报来的有些蹊跷。想大容国戎马出身,兵将多为骠捍之辈,人数上也多于前军数倍,又连胜了数日,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怎么可能如此一败而退,又失了本已到手的城池?
心里寻思了半晌,却找不到头绪。烦躁的起身出了军帐,外面已是夜幕深沉。
营中只燃着几点灯火,远处断断续续的有巡夜军人那种整齐的脚步声。
初冬的夜晚,空气夹了一点潮湿,又阴又冷。
忍不住扣紧了软甲,不停的哈着气。
“都冷成这样了,怎么还出来。”
身旁的人皱着眉,解下了自己的披风裹在我身上。
他一身整齐的铠甲,似是未曾休息的样子。
“都这么晚了,还没去睡?”
“今晚我当值。”
“是么……”
我任他帮我系上披风的带子,他离我很近,能感到他铠甲上隐隐的透出的寒气。
“琰。”
“嗯?”
“陪我走走吧……”
在前世心烦意乱时,总喜欢拉着煌琰满世界的乱转。
从东北的长白山到青海西藏,或者仅仅是城市里的某条不起眼的街道。
拉着他的手,随着性子到处走。他就在我身后任我拉着,不管有多累,都没说过一句怨言。而我每次回头时,也总能看到他那包容的笑。
而这次,他依旧是在我身后,离我不过一个转身的距离。
我知道他一直在守着我,在我看不到的地方默默的守着我。
他本不该是这种人,有时候我更想念他的贫嘴与无赖。
这样走了许久,快要出辕门时,我忽然停下步子回头问他。
“琰,你不是最喜欢自由么?可为什么偏偏要来军中。外面的天下那么大,哪里不比这里要好……”
他听了只是微微一怔,然后就歪着头笑眯眯的望着我。
笑也不是真的笑,那双眼里有愁似水,满的快要流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