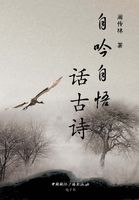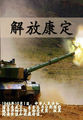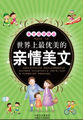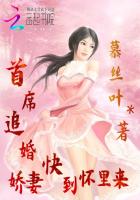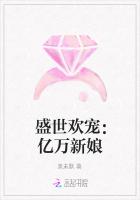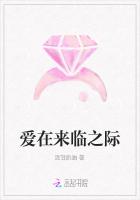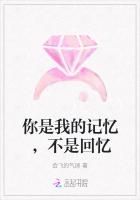严绍璗在本书第二章《日本古代短歌诗型中的汉文学形态》,通过大量的具体作品的分析,认为原始形态的和歌(“记纪”神话中的歌谣)是不具备“五七音音律数”的,而是从三个音到九个音,参差不齐,诗行也是奇数与偶数并存。而汉诗在日本的流传,日本人大量的写作汉诗,对和歌韵律的定型起了重要作用,并推断“和歌形态发展中的韵律化和短歌的定型,在很大程度上是模拟了中国歌骚体及乐府体诗歌中内含的节奏韵律”。在第四章《日本古代小说的产生与中国文学的关联》中,作者认为,在日本古代神话到“物语”小说的形成期这一过程中,还经历了一个以古汉文小说的创作为主要内容的过渡阶段。这一过渡阶段,以《浦岛子传》为代表,在小说的题材、构思与创作手法诸方面,都从中国文学,特别是从六朝小说与唐代传奇中吸取了诸多的营养;这种早于“物语”小说而产生的以中国文学为模拟对象的汉文的翻案作品,为此后的“物语”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准备了条件。
作者还详细分析了日本“物语”文学的鼻祖《竹取物语》所受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影响,并总结了三个要点。第一,《竹取物语》全面接受了中国汉民族自秦汉以来关于“仙人”的观念,将原来的“月神”改为“月宫”,作为仙人们的生活之所,这一观念成为全篇小说构思的基础;第二,《竹取物语》接受了中国汉代方士们所编造的“嫦娥”的形象,并把她改造为美貌无瑕的日本式女子,作为全书的主人公;第三,《竹取物语》采用了中国嫦娥神话中的“不死之药”的情节,并把它与作为日本国象征的富士山连接起来,构成故事的结尾……严绍璗在这些研究中充分吸收和消化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在使用丰富的文献材料支持学术结论方面,在立论点的明确性和深入性方面,超出了此前的研究。
严绍璗在古代中日文学关系的研究中,有着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他在后来提出的“原典性的实证研究”方法(《双边文化关系研究与“原典性的实证”的方法论问题》,见《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1期),可视为他的研究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实证”的方法作为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运用非常普遍,历史也很久远。但在人文科学研究这种主观性、人文性很强的“软性”学科中如何运用“实证”方法,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严绍璗认为,“原典性实证研究”是一个可以操作的系统,它由四个层面构成:第一,确证相互关系的材料的原典性;第二,原典材料的确实性;第三,实证的二重性;第四,双边(或多边)文化氛围的实证性。这里强调的是以原始典籍为证的追根究底、正本溯源的研究。
而这一点,恐怕是来自作者文学研究中的深切体验。严绍璗是我国比较文学界并不多见的具有深厚文献学功底的学者。1980年他出版了《日本的中国学家》,在此基础上1992年他出版了《日本中国学史》,近年又推出《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日藏汉籍善本目录》等文献学或以文献学见长的成果。文献学的功力体现在他的中日古代文学研究中,表现为材料的尽量的丰富和完备,一切都从文献资料和作品文本的分析出发,不发大而无当的空论和宏论。同时,读者阅读他的著作的时候,也没有被淹没在材料中的那种沉闷感,因为作者以自己明确的学术思想将材料有机统一起来了。
这种学术思想,还不仅是方法论层面上的,而且时常体现为高远的文化哲学的视点。他在《文化的传递和不正确理解的形态》(《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第4期)一文中,引用并强调了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讲演录》中提出的“历史是事实的描述,亦是事实的本身”和马克思提出的在文化传递中“不正确理解的形式正好是普遍的形式,并且在社会的一定的阶段上,是适合于普遍使用的形式”的论断,指出:“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者面临着一个更艰巨的工作,那就是在‘不正确的理解’中,通过文化传递的轨迹,从各种‘变异形态’的文化中,来复原‘事实的文化’。”
1990年,严绍璗与王晓平合著了《中国文学在日本》一书,作为花城出版社“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之一出版。著者在“前言”中称:“《中国文学在日本》的写作,其目的是力图描述中国文学在日本流传的轨迹和方式,阐明日本接受中国文学的过程中,本民族文学在内在层次上所产生的诸种变异;探讨日本人的中国文学观的形成、发展和变革,对日本学者翻译、评论和研究中国文学过程中形成的学术流派、研究特点、成就、发展趋向做概括的评介。”可以说,本书达到了著者预期的这些目的。
关于“中国文学在日本”的研究,日本人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这本书融会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在许多地方体现了作者自己的学术见解,将中国文学在日本的从古到今的流传与影响的轨迹大体勾勒出来,是很有益的。当然,这是一个大题目,本书以三十来万字的篇幅,只能是以点代面式的,还有许多问题未能涉及,或未能展开。1996年,严绍璗和日本学者中西进联袂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文学卷》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录了中日两国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该书的序论和第一章、第三章由严绍璗执笔,涉及中日神话和物语同中国小说的交流,基本上是在《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的基础上改写的,但在内容材料上有所丰富、补充和深化。这部《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文学卷》实质上是一部结构较松散的论文集,书中不少章节的选题显得有些随意,缺乏系统性,因而未能反映出中日文学交流完整的或基本的面貌。虽号称“大系”中之一卷,实际上既不算“大”(只有三十万字),也不成“系”。但这恐怕是“大系”的体例问题,非严先生之责。总体看来,严绍璗在中日古代文学比较研究中的贡献是显著的、富有开创性的。尤其是他的《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堪称他本人的代表作,也是20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精品之作,其中所体现出的学术研究的方法论和扎实严谨的学风,尤为可贵和值得称道。
王晓平(1947—)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从事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之一,在中日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的比较研究中取得了卓越的成果。早在80年代初期,他就发表了《〈万叶集〉对〈诗经〉的借鉴》(《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4期),1984年又发表《论〈今昔物语集〉中的中国物语》(《中国比较文学》创刊号)等有影响的文章。1987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王晓平的《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这部书和上述严绍璗的《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都属于《比较文学丛书》,也可以说是珠联璧合的姊妹篇。《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内容极为丰富,学术信息量很大,填补了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和知识领域中的空白。可以说,20年来我国读者关于中日近代文学关系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这本书。关于中日近代文学的研究,日本学者开始得早,成果也很多。王晓平的著作充分吸收和借鉴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将有关的成果进行甄别、提炼和提升,并在学术水平上有了明显的超越。
《中日近代文学交流史稿》所涉及的“近代”大体上是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年的半个多世纪,在日本是指从维新之前的江户时代后期到整个明治年间,在中国则是指从鸦片战争前夕到清末民初。这一时期是中日文学交流较为活跃频繁而又颇为错综复杂的时期。这是日本文人作家的汉文学教养空前普及和提高、中国文学的影响空前多样化、曲折化的时期,同时也是日本文学转向西洋世界,中国文学的影响逐渐式微的时期。
另一方面,长期充当日本文学之“先生”角色的中国文学,在这一时期里却逐渐转变了角色,开始以“学生”的姿态学习和借鉴日本文学。王晓平的《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准确地展现了近代中日文学关系的这一历史趋势和历史面貌。全书共有二十章,每章均以一个专题的方式,集中论述中日近代文学关系中的某一重要课题。它以传播与影响研究为基本方法,体现出扎实严谨的文献学功底,对中日文学双向交流的线索、途径和方式,做了清晰的描绘。由于作者能够得心应手地驾驭和运用材料,在影响的描述和考辨中,时有画龙点睛的理论分析,表现出作者的识见。
因此,这不是死板的、堆砌材料的传播与影响研究,而是将文献资料与理论分析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传播与影响研究,为比较文学的传播与影响研究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当然,这部著作也有不足的地方。由于涉及的问题点较多,有些问题在有限的篇幅内难以充分地展开和深化;另外,作为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它没有在书后列出“参考文献”。日本学术界研究中日文学关系的著作有很多,在本书中有哪些内容是借鉴日本人的研究成果,哪些是作者自己的超越和独创,光有脚注还不够,还应该通过“参考文献”加以清理和说明。
1990年,王晓平的《佛典·志怪·物语》出版。这部书以印度的佛典、中国的志怪、日本的物语为切入点,将亚洲三国的古典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纳入比较研究的范围。这是一个十分诱人的研究领域。历史上,中国的志怪小说受到印度佛经的影响,而汉译佛经、中国志怪又对日本物语文学产生了影响,可以说,佛典、志怪、物语是印度、中国和日本文学交流的三个基本点,并且三点连成一线。王晓平在这三点一线上展开研究,表现出相当大的选题智慧。全书分为“导论篇”、“浸润篇”、“溯游篇”、“渊海篇”共四个部分。在“引言”中,王晓平写道:
佛典、志怪、物语三者的比较研究,既要找出和证明其间影响的存在,更要深入到中古时代艺术理解和评价诸问题中去。志怪和物语在接受佛教故事的构思时,绝不是原封不动地挪用移植其中的全部因素,即便是抄袭式的“搬移”或直译式地转述,思想内容也有某种扩展或重新限定。接受者的联想指向也在发生位移。中国人并没有全盘接受印度人无拘无束、漫无边际的幻想方式,日本人也是尽量脱去中国小说中文士想象的庄重拘谨气氛,来发展自己的想象体系的。通过对一系列问题(接受者保存了哪些,扬弃了哪些,原始材料为何与如何被吸收和同化,接受之后发生了哪些变化,等等)的探讨,将会增加我们的文学史知识,增进我们对早期小说创作过程的了解和对作品的艺术理解;对那些并没有谁影响过谁这种关系的异国作品进行主题的分类与剖析,将其放在国际文化交流的氛围中作整体观察,则更会有助于对三国文学的倾向性、文学传统的探讨。
《佛典·志怪·物语》就是这样,灵活运用比较文学的传播研究、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方法,对印度、中国、日本三国文学的复杂关系,进行了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上的研究。在“浸润篇”中,作者通过对《日本灵异记》、《今昔物语集》、《江谈抄》等几部重要作品的分析,考察了中国志怪小说在当时日本的传播情况;“溯游篇”则以平行研究的主题学的方法,从几个共同的主题、母题和题材——如弃老、蛇婚、乱宫的母题、复仇主题、龟报故事——出发,进行了比较研究;“渊海篇”则从影响研究的角度,梳理了中国经史叙事文学对日本物语文学的浸润与影响,乃至对日本近代作家创作的启发。总之,《佛典·志怪·物语》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中迄今为止的仅有的一部将亚洲三国文学打通、进行多角度比较研究的著作。无论在选题方法还是研究方法上,都将对后学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1995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王晓平和日本的中西进教授合著的《智水仁山——中日诗歌自然意象对谈录》。该书以日本的《万叶集》和中国的《诗经》为谈论的中心,围绕“自然意象”问题,从月亮、星辰、花草、树木、鸟儿等自然意象为切入点,进行了多方面微观的分析和比较。作为《万叶集》研究权威的中西进,和作为《诗经》研究专家的王晓平,凭借对作品的熟知和比较文学的广阔视野,在“对谈”中知微见著,相互阐发,取得了珠联璧合的效果。“对谈”这种方式在中国的学术界还不太流行,但在日本和西方,则是常见的一种著作形式。而对于比较文学研究来说,不同国家学者的“对谈”本身,就富有强烈的跨文化对话的意味,因而也最能体现“比较文学”的目的和宗旨。
在中日传统小说的比较研究方面,南开大学教授李树果(1923—)的《日本读本小说与明清小说——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透视》一书是独占鳌头的大作。李树果多年从事日本和歌、俳句、戏曲、小说的研究,在日本古典文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在《日语学习与研究》等期刊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他还倾数年之功,将日本读本小说的代表作《南总里见八犬传》(简称《八犬传》)翻译成中文出版,因而对日本读本小说有着切身的体会。《日本读本小说与明清小说》是李树果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所谓“读本”,是日本江户时代流行的,与其他各种以图画为主的读物相区别的通俗小说。读本中的很多作品,在故事情节、框架结构、人物设置等方面,模仿和改编中国小说,对这种模仿与改编,日本人称为“翻案”,李树果称为“翻改”。对此,日本学者已经出版了大量的成果,研究读本小说与中国小说的关系,特别是指出读本小说的“出典”,即它是哪部中国小说的“翻案”。李树果的这部书,吸收和借鉴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时将那些成果加以概括和简化,以中国学者所擅长的精练,将读本小说与中国文学的关联清晰明了地揭示出来。他指出:尽管日本读本小说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千头万绪——
但归根溯源,我认为可以概括为三部书。一是《剪灯新话》(包括《余话》)的影响,从而使日本产生了翻改小说,为读本的创作提供了一种别具特色的方法。二是“三言”,通过翻改“三言”便产生了日本前期读本。三是《水浒传》,通过翻改《水浒传》便产生了日本后期读本。
李树果的这部书就是以上述三部中国小说为中心,探讨它们对日本读本小说的影响,并涉及其他中国小说对日本读本小说的影响。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在中日古代文学的交流史和古代文学比较研究方面,做出了成绩。如辽宁大学的马兴国(1946—)从1987年至1993年间,在《日本问题》等杂志上陆续发表研究文章,内容涉及中国古代小说《游仙窟》《三国演义》《搜神记》《西游记》《世说新语》、“三言二拍”、《金瓶梅》《红楼梦》《水浒传》等作品在日本的流传及对日本文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