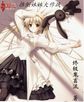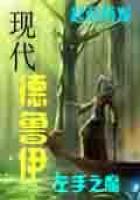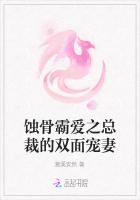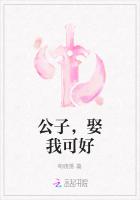在第一、二章中,作者从翻译文学史的角度,细致地梳理、描述了屠格涅夫作品的汉译情况、评介和研究情况,指出了不同时期的翻译家们在屠格涅夫翻译中的贡献。在第三章中,作者特别研究了屠格涅夫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重要的中介因素,即国外学者、翻译家的著译在中国所起的作用。对这种“中介”环节的研究,应当是比较文学传播研究中的重要的环节,孙乃修是我国中外文学关系与交流史研究中最早注意研究这一环节的学者,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在第四章和第五章研究的中心是“屠格涅夫与中国现代作家”,分节论述了包括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瞿秋白、巴金、沈从文、王统照、艾芜等在内的14位作家的创作与屠格涅夫的关系。
在这部分内容中,作者将实证研究与作家作品的审美的比较分析结合起来,将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结合起来,令人信服地展示了这些作家与屠格涅夫创作之间的关联,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揭示了这些作家创作的内面。作者最后总结说:屠格涅夫作品的主题、人物性格、艺术技巧、文体以及那种温婉、缠绵、带有脉脉感伤情调的抒情风格,都对中国现代作家产生了极其深刻的文学影响。一个外国作家有如此巨大的艺术魅力,在半个多世纪里对持续三代乃至四代作家产生如此深刻的文学影响,这的确是罕见的。同时,作者也辩证地指出:屠格涅夫在中国产生了如此长久的影响,“恰好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的某种迟滞性”。总体看来,孙乃修的《屠格涅夫与中国》一书,是中俄比较文学个案问题研究中的成功之作,是一个“小题大做”的、做得全、做得深的课题,可以预言,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孙乃修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都是难以被超越的。
托尔斯泰与中国的比较研究,特别是托尔斯泰与东方文化、中国文化之关系的比较研究,是中俄文学比较研究中历史最长、成果较多的领域。1930年代以来,不断有这方面的文章与著作出现。
特别是80—90代的二十年间,戈宝权的《托尔斯泰和中国》(《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为发轫之作,我国各学术期刊上发表近二十篇相关的研究论文。2000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吴泽霖(1948—)的《托尔斯泰与中国古典文化思想》一书,可以说是我国的托尔斯泰与中国文化比较研究的扛鼎之作。吴泽霖认为,现有的研究只是集中在中国古代哲学文化思想如何影响托尔斯泰的思想,并且往往过高地估计了这种影响,甚至认为托尔斯泰只是因为研读了东方的中国的古代哲人的著作才茅塞顿开,从而形成了“托尔斯泰主义”。而实际上,托尔斯泰从未悉心地认同过任何一种哲学思想,他对中国古代哲学文化的接受,“远非一种虚怀若谷的皈依”。
因此,吴泽霖特别注意在托尔斯泰一生的整个思想和创作历程的清理描述中,分析他如何将中国古典文化哲学思想加以独特的误读、理解和改造,如何将中国古典文化哲学思想融入他复杂的精神探索过程中,并力图恰当地估价中国古典哲学文化思想在托尔斯泰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托尔斯泰与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上编《托尔斯泰精神探索的东方走向》就体现了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该编的七章内容,将托尔斯泰的思想发展进程划分为若干不同的阶段,从历时的、动态的分析中,揭示出东方、中国的古典文化思想在托尔斯泰思想长河中的流贯轨迹。吴泽霖还指出,在现有的相关研究中,往往孤立地、单个地讨论托尔斯泰和先秦诸子的关系,这是不够的。事实上,托尔斯泰对先秦诸子的思想分野把握得并不那么清楚,常常加以混淆,因此,研究托尔斯泰与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关系,不能字斟句酌地牵强比附,而应从整个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体系的宏观角度进行综合研究,而且单纯的影响研究还不够,还必须将影响研究与平行的比较研究结合起来。
该书的下编《托尔斯泰思想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比较》的四章内容,主要是托尔斯泰思想与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平行的、对比的研究。其中涉及托尔斯泰的“上帝”和中国的“天”、托尔斯泰的“人”和中国的“人”,托尔斯泰的认识论和中国古典“知论”,托尔斯泰的艺术论与中国古典文艺思想等内容。通过这样的对比研究,作者指出,在托尔斯泰的思想中,有些是来源于或受启发于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而某些相似或相近的思想却未必是受到来自中国的影响,而是思维上的不期而然的吻合和相似。总之,吴泽霖的著作系统、全面、深入地清理和论述了托尔斯泰与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关系,对于读者进一步了解中俄文学与文化关系史、对于深入理解托尔斯泰的思想与创作,都是一部值得阅读的重要的书。
普希金也是最受中国读者欢迎的俄罗斯作家之一。
从20世纪初开始,他的作品就被陆续译为中文,长期以来,中国读者把普希金视为反对暴政、讴歌自由的“革命诗人”或者“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而予以高度的评价。其作品在中国翻译很多,传播甚广。特别是80年代后,中文版本的《普希金文集》和《普希金全集》以及传记、研究资料集、大量的单篇的研究论文等连续出版和发表,有关部门还举行了普希金诞辰的隆重的纪念活动。到了2000年,《普希金与中国》一书由长沙岳麓书社出版,可以说是一部普希金与中国的比较研究的集大成的书。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是“普希金笔下的中国形象”;第二、三章是“20世纪上半叶普希金在中国的接受”;第四、五章是“20世纪下半叶普希金在中国的接受”;第六章是“普希金与20世纪中国文学”,分别论述了普希金对中国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的影响。
在全书中,第二至五章占了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是该书的核心,也是最有特色的部分。这四章内容以普希金在中国的翻译家、研究家和出版家为中心,专文单节地评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家、学者在普希金译介与研究中的贡献,依次有戢翼翬、鲁迅、瞿秋白、温佩筠、孟十还、甦夫、戈宝权、余振、吕荧、查良铮、卢永福、高莽、王智量、李明滨、冯春、张铁夫、陈训明、刘文飞、查晓燕等。这种以翻译家、研究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使中俄文学关系史的研究立足于中国文学,突出了接受者的主体性。正如张铁夫在“引言”中所说,“把一代代翻译家、出版家、研究家的事迹连结起来,就是一部普希金在中国的接受史”,也是一部以普希金为纽带、以中国的翻译家、研究家为中介的中俄文学、文化交流史。对普希金的翻译家和研究者,特别是对当代翻译家和研究者的研究,作者除了利用现有的书面的、译本的材料外,还做了不少的调查、访问工作,这些工作是开创性的。这就为今后系统地研究清理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史打下了基础,也为今后的《中国的俄罗斯翻译文学史》之类的著作提供了经验,准备了条件。
((第二节))中英文学关系研究
一、中国文学在英国的传播与影响研究
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在英国的传播与影响的研究而言,范存忠的《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在英国,有一些研究中国文化与文学的专门著作,但系统地研究中国文学在英国的传播与影响的著作却一直付之阙如。据说我国学者钱钟书20世纪30年代在英国留学期间用英文写有一本题为《十七与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的书,可惜此书一直未见正式出版。范存忠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中英文化关系史的研究,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80年代完成的《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一书,是他的研究的集大成。该书所研究的范围虽然是“文化”,但主要的研究对象和所依据的主要材料是文学。该书共有十章。作者充分接触、消化和利用了大量第一手的材料,由于掌握材料的充分与完备,每一章、每一个问题都写得那样有血有肉,娓娓道来,从容不迫,将原本枯燥的学术问题处理得轻松自然。同时,作者又显然在追求“无一句无来历”的严谨学风,在每章之后都列出了大量的引文注释,标明材料的来源,并为后学者提供线索。当然,作为中英文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开山作品,范存忠先生的这部书涉及的只是中英文化文学关系的一个时段——18世纪启蒙时期的英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中的若干个重要的“点”,也就是说,其研究还是扼要的、初步的、示范性的,正因为如此,他也为后来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范存忠的上述著作出版后不久,张弘(1945—)的《中国文学在英国》也由广州花城出版社作为《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之一种,于1992年年底出版。这部著作以二十八万字的篇幅,分九章系统全面地评述了中国文学在英国的传播、译介和接受的历史进程。作者在“小引”中指出,“从1589年英国人乔治·普腾汉《诗艺》介绍中国古典诗歌格律算起,中国文学传入英国至今足有四百年之久。这四百年里,中国文学怎样在英伦传播,受到了什么样评价,如何影响英国的文学与文化……
我们之中有许多人是不大了解的。尽管钱钟书、杨周翰、范存忠、方重等学界耆宿先后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但那是先行者在黎明原野的足迹,还未曾引起更多人的注意。”显然,张弘在写作此书的时候,范存忠的著作还没有出版,但《中国文学在英国》在研究的广度上乃至深度上,是较范著有所推进的。可以说,它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在英国的传播史方面的专著,填补了一个重要的空白。全书采用由总论到分论、由纵向描述到专题研究的方法,勾勒了从十七世纪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在英国的过程。作者在第一章中,首先交待了中国文学在十七至十八世纪进入英国的文化背景。他指出,由于商业及传教的现实需要,从十七世纪始,英国出现了一股“中国崇拜”,首先是各种各样的中国游记的热销,这些游记并非真实的旅行记录,而是传闻加想像的向壁虚构。
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受到推崇,而威廉·坦普尔爵士则是“中国崇拜”的登峰造极者。而1699年坦普尔爵士的去世,则预示着中国在十八世纪英国人心目中的理想色彩的消退。十八世纪的英国在国力增强的同时也随之自傲起来,他们“绝对容忍不了大不列颠王国不堪与中国大帝国相媲美的论调”,他们的作家对中国的批评越来越多,以笛福为代表的作家对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否定的看法为其他的英国作家描述中国奠定了基调。但同时,即使在英国作家的这些充满无知与偏见的批评中,也有一些真知卓见。张弘认为,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十七至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已经出现了“中国主题”,而“中国主题”进入英国,标志着中英两国建立了一定的联系,也是中国文化影响英国的一种表现。
张弘所说的“中国主题”具体指的是:一,借用中国作品的素材,包括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二,写实的或虚构的中国社会生活、自然环境及幻想世界;三,当作作品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特色”;四,受到中国观念意识的启发,或对中国观念意识的阐释;五,描写或涉及的实际的中国事件与人物。张弘指出,埃坎纳·塞特尔的五幕悲剧《鞑靼征服中国记》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表现中国主题的作品。此后,笛福的讽刺小说、艾迪生和斯蒂尔的故事与杂文,霍拉斯·沃普尔的《中国人信札》、哥尔斯密的《世界公民》,无名氏的《和尚——中国隐修士》以及约翰·斯格特的题为《李白,或贤明君主》的诗,哈切特的剧本《中国孤儿》等,都是重要的“中国主题”的作品。关于十八世纪英国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张弘指出,当时英国懂汉语的人寥寥无几,翻译的情况也很复杂,有的是假托的“伪译”,有的是面目全非的改写,也有认真的翻译。
其中最重要的翻译首推配尔西翻译的《好逑传及其他》,还有威廉·琼斯直接从中文翻译出来的《诗经》等,并随之出现了若干评论中国文学的文章。但总的来说,十八世纪中国文学在英国还只是一个模糊的身影。作者在第二章中,展示了十九世纪后英国译介中国文学的新局面——出现了一批汉学家,如理雅格、德庇时、翟理斯、韦利等人;出版了一批汉学著作,特别是中国文学的研究著作,如翟理思的《中国文学史》等。张弘对翟理思的《中国文学史》(1901)做了较深入的分析评价,认为本书“可以说是十九世纪英国汉学界翻译、介绍与研究中国文学的一个总结,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整个西方对中国文学整体面貌的最初概观。”本章还总结了十九世纪后英国接受中国的一般特征,即主要通过译本来接受,专题的研究不多,且在研究中受日本研究成果的影响;在译介中偏重古典作家作品等。
在《中国文学在英国》的第三章至第六章中,作者以文学体裁样式为中心,分别评述了中国古典诗歌(诗经、楚辞、汉赋、唐诗、词)和古典诗人(陶渊明、李白、袁宏道等公安派诗人、袁枚)、中国古代小说(《聊斋志异》、《古今小说》、《金瓶梅》、《西游记》、《红楼梦》、《镜花缘》等)和古代戏剧文学在英国的翻译和研究情况。
作者对英国人的独特的关注对象、研究角度、方法及独特的结论做了评析,例如,在谈到英国人为什么对“赋”这种即使在中国也很少有人阅读的文学样式特别感兴趣时,他认为原因就在于赋特别讲究词语修辞,而二十世纪风行英美的注重语言文本的文学研究思潮,决定了他们把注意力转向赋;在谈到陶渊明、李白等诗人在英国的际遇的时候,作者指出了由于文化的差异,中国诗人所遭到的误解与误读——进入英国的陶渊明不知不觉地被染上了存在主义色彩,而李白在守旧的英国式眼光的审视下,竟然被加上了“不道德”的恶名。
汉学家韦利在《李白的诗歌与生平》一书中,说李白是一个自夸自负、挥霍放荡的酒鬼。作者写道:通过韦利的介绍,“英国人反而增加了误解,李白的伟大也受到损害。李白的英名再度在英伦之岛回响,但我们并未感到一丝一毫的荣光。”又如,翟理斯在介绍蒲松龄及《聊斋志异》的时候,却将蒲松龄与英国鼓吹英雄崇拜的历史学家卡莱尔相提并论,认为“在西方,唯有卡莱尔的风格可同蒲松龄相比较”,张弘指出,尽管这种比较出乎中国人意料,但比起华裔学者张心沁的那种几乎不从英国文学中寻址任何参照物的径直的介绍和研究,对于我们的比较文学来说更有兴味和价值。在第七和第八章中,作者介绍了英国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