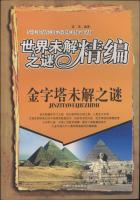她起身,收拾收拾出门去。
木子坐在妇科等待区。这里聚集着需要一个细胞以及有需要除掉一个细胞的女子们。木子面前坐着一名孕妇,长发。白净。他的丈夫轻轻用手抚摸着她的肚子。而他们并不知道,也并不在意他们的对面,有一个名叫木子的女人备受触动地坐在冰冷的椅子上忍不住用头发掩着脸哭了起来。
站在屋外的木子蓬头垢面,她深吸几口气握着钥匙握着门把想直接开门进去又改为敲门。扣扣扣。门缝一点点地变大,逐渐拓宽的视野里平倚在玄关柜上,居高临下地看着她。木子嗫嚅着:我很难受孕。但调理好得话还是可以。我可以很好地照顾我们的孩子……
平藐视着她。那又如何,你作为个不健全的女人……木子愤怒地质问:这么多天我已经忍够久了。你有没有把我当做你的妻子?你娶我的理由呢?我们这两年的感情呢?这就是你出轨的理由吗?我们能有孩子……平脸上露出略有点抱歉的神情:‘开始的时候我还是挺喜欢你的。可是不好意思,我现在腻了。你要理解我们男人。’
‘平,你他妈凭什么这么对我?’木子听到这句话几乎要气疯了,她感到自己的尊严被践踏在脚下。她冲过去抓住平的衣领:‘我嫁到你家来,什么都不收,全心全意为你付出,你有对我比你的小三好吗?就这么几个月?就这么几个月!你简直是个畜生!’
平借着之前和同事拼酒的酒胆霍地站起来扇了木子一巴掌。
他表达鄙视的鼻孔翻起:‘我还没骂你倒是拽起来了,你个贱女人。不要太把自己当人了。你有什么。你本来就低贱。生不了老子更不用把你当人看。’
轰。木子全身瞬间冷下来。头脑冷静,愤怒的情绪也消失。她先是露出心痛的笑容看着这幅光景。再也没解释什么。两行眼泪在干燥的脸上蜿蜒地滑下来。是的。木子自知现在无法给予平更多东西了。耻辱是一群乌鸦盘旋在她的颅腔。她再一次深刻感受到自己对未来的茫然。电视机发出有秩序的声响,楼上的孩子正在弹钢琴。节奏欢快的土耳其进行曲……此刻有多少人在正常的……积极地生活着……而现在的木子——她连谈尊严都不配。她捂着热乎乎的脸,跌跌撞撞地走出了家门。
离婚吧。她没有坐电梯,她在黑暗的安全通道里扶着生锈的铁栏杆一步步跌跌撞撞地走下去,这里真是个糟透的地方这四线小城市……脑子里一百万次地回想平不可理喻的比变色龙转变还快的那副嘴脸……离婚吧。站在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前,行人们摩肩擦踵地小跑着踩着绿灯闪烁的节奏通过马路,只有一个人,她慢悠悠地踱着步,有种想被撞死的冲动。离婚吧。这只是个再通俗不过的故事。此刻说不定有不少同病相怜的人呢。说不定还有更惨的,都可以被写作新闻的故事。所以不要再犹豫了,离婚吧。刚揽上客的黑车司机还没反应过来,一个穿着红衣衫的女人走到了斑马线上,也走到了他的车轮前。
‘你这是红灯啊小姐!有没有素质!’他忍住破口大骂的冲动。而这个女人只是旁若无人地向前走着,衣服擦过车灯也没见有半点停留。
‘真是个****。’他摇上车窗开走了。卷起的一阵风刮起木子衣服口袋里掉落的一张卡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