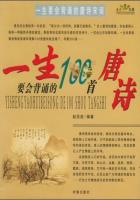认认真真地去做小说,是我眼下唯一的事情。当然我还要工作(我的职业是文学编辑),还要吃饭睡觉和恋爱,还要干一点别的,比如玩扑克输掉或者赢来一顿饭钱,比如在天气转暖之后游泳或踢球。但做小说仍然是我唯一的事情。在其他事情与它之间,并不存在第一第二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我不允许其他事情干扰我写作。如果那些我非干不可的其他事情不但不能干扰我写作,反而还能有益我写作,那会让我享受到多重的快乐。
所以,在一个适当的时候静下心来整理自己,我认为,这有可能成为一种出乎意料的别样的快乐。
A.小说家与小说
不可否认,小说家是小说制造者,小说是小说家的产品,它们之间符合某种逻辑上的从属关系。但我们还是不该就此认为,小说与小说家只具有一种被动联系。创生小说的话语天然存在,它们在被书写出来之后构成小说。可是写作的实践告诉我们,在书写之前,即使是小说家本人也不清楚,这些话语究竟是什么。如果愿意借用一个蹩脚的譬喻,我们尽可以这样理解:小说是一只拴不住的野兽,它只不过是选择了一个适当的时机,选择了一个适当的人,假他之手打开囚笼,脱逃出来。而呼风唤雨的小说家,在这个时候,只不过是那个恰好被小说选中了的开锁之人。
当然小说家作为主体的事实不容颠覆,我们也没必要复杂化和神秘化小说写作。并且,小说家并非一种可以享受终生的荣誉头衔,它允许是对一个人的阶段性称呼。
好像是一种前世的命定,小说家是一些只为小说而存在的人,写作是他呼吸的另一种方式。小说家也可能因为种种因素去做别的,但走过一遭他往往发现,其实他必然能够做好的事情,只是小说写作。即使他的确异禀突出多才多艺,有能力也成功了其他事情,但最后的感觉还是一如从前:任何其他事情的成功,都不及小说写作给予他的快乐那样巨大和美丽。对于小说家来说,最要紧的只能是小说。至于小说家与其他种种事物所发生的关系,不难证明,那些有利于小说的关系便是好的关系,反之常常是不好的关系。而真正有利于小说的关系只有一个,那就是能最大质量地将小说家的心灵敏感度唤醒和激活的关系。一个小说家,他所面对的两个敌人都由自己派生:一个是满足,另一个是死亡。小说写作是一种智力游戏(游戏并不排除严肃。政治、商业经营、恋爱与博弈、摆积木、卡拉OK,在本质上它们完全一致),一旦对智力的高度发生了怀疑,遁入虚无是唯一的可能。而死亡,它是人类全部本能的终结者。
如果一定要说是小说家创造了小说,那也不是父母创造了儿女那样一种简单化的结果。大仲马把他的儿子和他的小说混为一谈,肯定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小说家创造了小说,其实是圣徒创造了上帝。只有小说这个上帝把小说家作为它的选民规定下来,小说家才算找到了他最后的栖身之地。
B.小说家与生活(1)
照理说,上边的问题,没必要进入我的思考范围。把小说家与生活人为地割裂开来,对于小说家本人来说是作茧自缚,对于非小说家的判断来说,要么是隔行如隔山,要么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小说家的根本任务,是要传达对人类经验的精确印象,表现个人认识自己和发现自己的整个过程,揭示人的存在的可能。要达到这样一个主观目的,不论是否自觉,小说家所要倚仗的,必然是涣漫的客观背景。可事实上,用主观和客观来解释小说与生活的关系,完全是机械甚至荒谬的认知态度。人类的全部生活包罗万象,小说的制作即是星罗棋布的生活天幕上一颗若明若暗的神奇星斗,它根本就无法置身于生活之外。生活无处不在绝非诡辩而是真理。如果有人把一次阅读的体验一次恋爱的体验或者一次饥饿的体验看得低于一次战争的体验一次春种秋收的体验或者一次经商做官住监狱的体验,我们至少可以认为他对生活的理解太过粗疏。小说家所唯一必需的,不是他自己是否曾经或者正在当军人当农民当商人当工人当官员当犯人,而只是那些他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最早进入他生命深处的童年经验。
生活的经验没有限度,生活的感受也无法完全,只有好奇心和想象力才是小说家最为宝贵的“生活”。人是文化的产物,作为一个小说家,他所敏感的总是他所置身的文化氛围,只有在属于他自己的氛围里,发现的契机才会随处可见。普鲁斯特不会去写《老人与海》,福克纳也不会去写《局外人》。这跟他们没有吹过古巴的海风没有晒过阿尔及尔的太阳关系不大,有关系的,或许只是海明威身上那数不胜数的炸弹碎片和加缪与生俱来的异邦感受。在更多的时候,小说家生活在“生活”的边缘,他介入“生活”的触角不是四肢不是汗水甚至不是眼睛,只有心灵的感觉至高无上。艺术不是为了堕入苍白的写实中去画地为牢,不是为了实现复印机才引为自豪的科学迷信效果。艺术的逻辑是打碎有序遗忘表象,由片面和孤立获得形而上的解放,组合成一个属于心灵的世界。在小说中,小说家所说的话,只是他想说的和能说的话;而小说家所觉悟到的,也只能是生活那隐约的暗示,那种无边无际的神秘感受性。小说家的小说,最终会大于生活。
C.小说家与生活(2)
小说家要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生存方式大体合意呢?我想,即使是男小说家,也应该像弗吉尼亚·伍尔夫那样,先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和可以维持温饱的收入;然后是有相对长一些的独处的时间;有差不多的体力;有几架书……达到这样的标准似乎不难。是的,的确不难。哪怕是生活在一个最糟糕的社会里,除了得到一间自己的屋子有时会麻烦一点,其他几项对一个身心正常的人来说,应该不成问题。
事情的关键是小说家本人。没有人不想过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之后那种富如巨贾的生活。
尽管现实的功利性无孔不入,在庞大的物质实际面前,基本上是非功利的小说艺术总是遭受排挤和冷落,从而使得大部分小说家与这个世俗世界格格不入。但毕竟小说家是一些智慧的生命,他完全可以迎来财富滚滚(我不说权势滔滔。在我看来,权势比财富具有更大的腐蚀性)的时刻,他没有必要拒绝人间烟火。问题的核心是,在灵欲相搏的血雨腥风里,物质对于精神的鲸吞蚕食与涂毒戕害虽然如同法西斯或者文化大革命,但小说家绝不拱手出让他坚守的阵地。小说家以他的小说构筑心灵的堡垒,为人类的良知树起最后一道保护屏障。小说家可以贫穷也可以富有(在现时贫穷似乎更标志正常),但他对待一己的贫穷和富有能够一样的心安理得,甚至麻木不仁。小说家手里的硬通货只是他的小说。我想,即使是在腰缠万贯的时候,“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又不改其乐的生活选择,也会是当今小说家最不坏的一种存在方式。我的意思,并不是要宣传禁欲主义或者越穷越革命的观点,我也不是要自欺欺人和自我安慰。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贫与富没有质的差异,只有量的区别。
在一个人类苦难高度专门化的领域里,小说家唯一重要的只是心灵,“让生命的烛芯被故事轻柔的火焰燃尽”(瓦尔特·本雅明语)是他的骄傲与光荣。然而,小说写作毕竟是一项漫长艰辛的劳动,尽管它给小说家带来的快乐无以比拟,但漫长艰辛还是巨大沉重,它往往需要小说家赌进一生的时间和其他方面的所有快乐,而能否赌赢依然未知。甚至无赢可言。事实上,这是一场神鬼之战。魔鬼阻止小说家的成功,而神性却附着于小说之上。神和鬼都是不会绝灭的,因此,在你进我退或者我进你退的僵持中搏斗便是常态。前面说过,小说家是小说这个上帝的选民,信和诚是小说家对小说最重要的态度,小说家毫不分心旁骛的写作便是对小说的祈祷。那么,有谁认为祈祷可以不需要心身双重的孤独宁静淡泊安详吗?
不是迷信榜样,我们反复默念下面的名字,只是为了进入祈祷的状态:居斯塔夫·福楼拜、纳撒尼尔·霍桑、弗兰兹·卡夫卡、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D.小说家与灵感
用一个不讲道理的道理来回答上面这个问题,大约最合乎道理。
前提是要承认灵感(因为我承认灵感才有了这个问题),然后,或许可以这样做结:当小说家能写出小说时,就说明他产生了灵感,当他苦思冥想却不知如何下笔时,就说明他没有灵感。以此类推,还可以说,成熟的灵感滋养成熟的小说,幼稚的灵感催生幼稚的小说,新异的灵感成就新异的小说,蹩脚的灵感分娩蹩脚的小说,等等,这种推导可以如同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那样循环证明。
灵感不是故事不是情节也不是细节,靠出国考察下乡采风进厂体验收集灵感殊为可疑。灵感有点像自杀之外的人的死亡,它什么时候出现你可以大体有数却绝对无法具体把握,因此每个小说家获得灵感和培植灵感的方式方法都不相同。但有个要件倾向一致或许不谬,对于文字排列组合后所产生的那种隐秘意义的迷恋与热爱,似可确定为小说家灵感最根本的源泉。灵感的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性比较强大,多少接近胡适所论: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就我个人而言,我愿意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等待灵感的不期而至,就像等待一个未来的情人。当然,我等待的姿态得让我快乐,它应该是一种由阅读思考与写作组合而成的优美姿态。因为我差不多能够肯定,这种姿态,即是我生命的基本姿态。
E.小说家与理想
在琳琅满目的小说博物馆里,不靠错觉人们也该看到,筋疲力尽的前辈小说家正眨动着讥诮的眼睛,疑惑而又同情地注视着后辈同行,似乎在询问:你往何处去?
小说家往何处去?这还的确是个问题。小说艺术发展到今天,一面开辟出一条条崭新的超越极限之路,一面又堵塞了一条条供后人选择的可能性之路,使得后世的一代代小说家,总得置身于前辈的阴影笼罩之中。
当然小说家需要的不是同情。尽管小说家在喜新厌旧这一点上与俗世认同,但小说家通过标新立异来确定自己的位置,并不是为了廉价的彩声,而是源于对生命本能的珍重。打破庙宇重筑殿堂,这种繁重的劳动被小说家看成是最神圣的使命。因为小说家知道,机械的效仿与乏味的重复,一成不变的风格和轻车熟路的模式,都是导致小说衰弱与停滞的不治之症。而这个不断运动着的、对于我们来说既熟稔又陌生的、时时在向我们提供新鲜经验与独特感受的广袤世界,只有在小说家那里通过视角的变换、手法的更新、形式的选择,才有可能被更为真实和准确地发掘出来。所以,否定传统和创造传统,就成了历代小说家是否杰出的重要佐证。不论罗伯-格里耶的“完全的主观”还是彼得·汉德克的“神秘的形式”,不论唐纳德·巴塞尔姆的“碎片”风格还是伊塔洛·卡尔维诺的“时间零”理论……它们不仅丰富了小说写作的艺术手段,它们更深化了人与世界的内在关系。
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放弃模仿另辟蹊径,这是小说家在他创新活动中的主要追求,但这并非就是全部。在我们强调花样翻新的技术革命时,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这样的困惑,每一种以挣脱模仿为目的的独特性选择,最终总是沦为模仿者最方便的草图蓝本,从而使身陷重围的小说在下一次的突围中变得异常艰难。这自然怪不得小说家的顾此失彼,但却是给小说家敲响的一记警钟。小说不是物质主义的抗争与反叛,也不是哲学命题的阐释与图解。小说的触须伸入人类心灵最敏感的区域,它是对情感与愿望的隐秘揭示,是对前途与命运的终极关怀。如果我们承认是形式赋予了小说生命,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这种形式所分泌出来的思想滋养了小说的灵魂。这个灵魂只有站在超越世俗的高度之上,才会反过来又使它所寓居的小说获得高度:既凌驾于世界之上,又融化于人类之中。而只有真正精神高远的小说,才永远是不能模仿、无法复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家的打破庙宇重筑殿堂,不是因为上帝死了,而是为了更靠近上帝。
F.小说家与责任
没有责任感的小说家我不知道有没有。但责任肯定是小说最重要的派生物,它是小说写作时所呈现出来的精神光芒的发散与折射。责任不对善恶美丑真假好坏负责,责任只对存在负责。
小说家在写作小说时的出发点可以各不相同:自娱、讽喻、训诫,没什么高下之分;小说家对小说后天功用的评断也可以各不相同:消遣、警世、教化,都可以成立。但有一点却殊途同归,所有的小说,都是借用一个个受苦的、牺牲的、快乐的、希望的和反抗的例子,来研究发现和认识人的存在及可能。所以,小说家在他的小说写作中,是没有道理去耽于通行的思想准绳和先定的形式常规来完成自己的,他只能听从发自自己内心的声音。小说家既不文过饰非也不敷衍塞责更不弄虚作假,他在小说自身虚构原则的规定下,以诚实的态度和道德的情感支持文本的美学价值,从而使真理的光辉在小说的字里行间熠熠闪烁。
小说家的责任,即一部小说的诚实和道德,集中体现在小说家的技巧运用上。
技巧既不是规范条款,也不是故弄玄虚,技巧只意味着小说的发言如果不好便等于缄默。技巧不是装扮小说的花裙子,技巧是小说本身,是小说家的本能暗示给小说家的激动和热情。小说家的每一次写作,都是以一种最有利于释放心灵和精力的形式来轻易地、自然地、丰富地表达自己,以具体的、个人的方法来解释人类本质上的复杂特性。如果这种表达和解释不需要使用技巧去完成,那么这种表达的价值就值得怀疑,这种解释的意义就难免羸弱,它也就无需成为小说或者小说的一个部分。在这时候,技巧充当的是诚实和道德的试金石。保尔·瓦雷里说过:一个诗人的职责--不要对这种说法感到惊异--并非是体验诗的意境:那是他个人的事情。诗人的职责是在其他人身上创造出诗的意境。瓦雷里又说:富有天才的人就是赋予我天才的人。
G.小说家与真实
安德烈·纪德在《伪币制造者》中说,真实使我感到窘惑。
纳丁·戈迪默站在诺贝尔领奖台上说,我所写或我说的任何事实都不会比我的虚构小说真实。
关于小说的真实和对于真实的抵达,余华有过精妙的论述,那篇文章叫《虚伪的作品》。
而我想说的只是,真实永远停留在语言的绝境里,它是想象的儿子。真实作为一个影子,一个梦幻,一个虚拟,它传递出山穷水尽柳暗花明这样一些简洁而又迷离的眼波,引诱小说家永不气馁。
埃兹拉·庞德曾经讲过一个这样的故事:
“你在画什么,强尼?”
“画上帝。”
“可是,没人知道上帝长得什么样子啊。”
“等我画好之后,你就知道了。”
这里的“画好”,我不想简单地理解为“画完了”,我认为它的主要含义是“画得好”。
H.小说家与政治
米兰·昆德拉一向标榜他的小说与政治无关,以前我不信。在他所有的长篇小说(甚至包括《为了告别的聚会》)中,政治总像鬼火一样,不怀好意地跳动在我们这些已经荒凉成政治坟场的大脑里。可是后来,当我不再作为坟场上的一丘瘦冢而以掘墓人的姿态来看待这个世界和与这个世界有关的小说时,我相信了,昆德拉说的不是假话。
政治是渴望进步的人类在自己的肢体上捆绑的翅膀,在这一点上政治与科学技术颇多共同之处:其明晰的功利因素,常常会使那翅膀蜡炬成灰。政治与现代社会的一切个人都息息相关,任何放弃政治倾向摆脱政治影响的企图都必成徒劳。小说家完全可以是为某种政治理想而战的勇士,当然前提是他在勾心斗角党同伐异的时候忘记小说。
但是小说从来也不是政治的工具,小说家更不是政治意识的仆从。在小说写作中,语言、结构、文体等属于艺术范畴的方式手段,要比作品的思想性和主题意义更为重要。艺术是质疑性的、假定性的,而政治则是非此即彼的、强辞夺理的。艺术对于政治的本能排斥,恰似女人之于无赖的纠缠。小说家的声音的确多种多样,私语也好抗议也好,其意义只在揭示存在的境况,它渴望的,是增加和强化这世界上每个人身上都可以发现的自由和责任的总量。小说家的思考是超意识形态的思考,政治则只能使小说狭隘和肤浅。在政治场景中,人是一些没有血肉的工具,事件是一些丧失深层因果关系的偶然性,一旦小说的美学品格面临人与事件的双重退化,红颜尽逝是它的必然结果。林语堂为文人确立的为文准则之一是“不反革命”,这“不反革命”无疑是艺术与政治的标准距离。“利用小说反党”肯定是小说家的自不量力,把小说变成政治武器的小说家其实是初出茅庐的政治打手。用两分法来过滤小说家的声音,除了无知还很危险。昆德拉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借萨宾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人物)之口提醒读者:我的敌人是媚俗,不是共产主义。事实上,总是被别人确定为斗士角色的鲁迅,也非常反感强加于他身上的政治釉彩,他曾说:我所抨击的是社会上的种种黑暗,不是专对国民党。这黑暗的根源,有远在一二千年前的,也有在几百年前的、几十年前的,不过国民党执政以来,还没有把它根绝罢了。现在他们不许我开口,好像他们决计要包庇上下几千年一切黑暗了!
说到底,在人生的舞台上无法换掉政治的背景,这只是政治的无所不在性出给小说的一个难题。
I.小说家与读者
谁也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读者喜欢什么样的小说家及小说?因为一千个演员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但小说家对读者的要求则相对简单,他认为写作和阅读属于智能博弈游戏,他希望读者是他势均力敌的对手。
小说读者的减少对小说家来讲不一定就是要命的事情,就好像小说作家的减少对小说来讲不能要命一样。淘尽黄沙始到金吗。爬罗剔抉,这不是靠百分比来选先进,这凭的是货真价实的爱与需要。可小说的事情毕竟是小说家、小说和读者这三方面的事情,关于三角形的物理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还是不好置若罔闻。小说通神但首先通人,小说家不能不渴望倾听。尽管读者的缺席有许多客观原因,小说家们有理由羡慕巴尔扎克特罗洛普年代的没有电影电视却有许多识文断字的家庭妇女。但是有一个要紧的事实却没法回避,在我们这个有了电影电视少了识文断字的家庭妇女的时代里,无需抽样调查也可以做出肯定,小说家真正的对手并不是少了而是多了。我们对文明的积累应该正视。问题只是,这些狡黠的对手变得更加谨慎挑剔和严苛,他们所需要的是与他们智力相当的新一轮角斗。
小说家必须接受挑战。每一部小说,都是小说家创设的一个完整世界。是否进入这个世界是读者的权利,但在这个世界里边能否玩好则在于小说家的导引。可能有盲人游客看不见曲径通幽,也可能有聋哑游客听不着莺啼鹂啭,但真正的妙景胜境终究只能是妙景胜境。连徐霞客都视而不见的山水,就至少得允许游客存疑了。在小说这个独特的世界里,如果小说家提供虚假的经验,受骗的读者必然拒绝买单。而对手的冷落,那将是小说家由衷的悲哀。自然,诚实的小说家也不会把意气用事的子弹射向读者,他不动辄宣称自己在为后世写作。小说家在他的写作中,并不需要吃得准自己的哪些文字可以流芳千石,他的笔首先对准的只能是“今天”:他自己的“今天”和读者的“今天”。如果“明天”他那聪慧的读者继续踊跃,那只能说是他的福分。
当然了,小说家对读者的期待是纳博科夫式的期待--不只是用心灵,也不全是脑筋,而是用脊椎骨去阅读接受。通过降格以求和曲意逢迎取悦读者的,那不是小说家,而是没有廉耻的婊子与翻云覆雨的政客。小说家企盼读者的接纳就像企盼爱人的垂青,但前提是这种接纳要以小说家自己的原则与方式为依据和准绳。
J.小说家与未来
K、L、M、N……如果就这么一直数下去,还有十六个字母。但是我不敢数了,我已经看到了危险。小说家的小说与嘴皮子无关,尽管坐而论道(好在论的是只对我自己有意义的小说之道)也能使我快乐,可犯规太甚、越位太过还是不大对头。
我这人有时目光短浅,不愿为将来费心劳神。可在有一点上我很固执,那就是,人类情欲的本能不会退化,小说家和小说就不会灭绝。我的意思不是要说某种主题的永恒与否,我也不是弗洛伊德的嫡嗣亲传。我的意思只是,小说和小说家永远都有快乐的理由,因为未来总在我们未知的前方而不在我们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