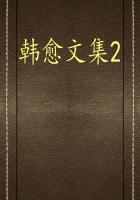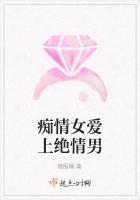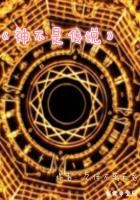这里是川西平原的西北边缘,是都江堰自流灌溉区的末梢,它有一个不为许多人知道的名字,叫柳沙堰。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柳沙堰潺潺之水,流淌千年,自流灌溉,滋养着这儿的人们休养生息,代代繁衍,直至今天。
很不公平的是,它竟不被许多的人知道,所以就有必要记录下以这儿为起点,为当地引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的一些人和一些事。
知道柳沙堰的人很少,但知道被它养育了千年之久的八角井这个地方的人却很多。
其实八角井镇也很小,小得在中国的地图上找不到她的名字。
但八角井镇的名声很大,不但声震全国,而且名扬海外。因为在这里有一个“四川省德钢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它的产品不但畅销国内各省,而且走出了国门,远销俄罗斯、新加坡、马来西亚、巴西等国。
德阳市内,只要你是八角井镇的人,你是“德钢”的职工,哪怕你身无分文,也能带走你相中的商品。因为在德阳市内,八角井镇人的殷实富裕,“德钢”人的诚实守信,妇孺皆知。
八角井镇人的生存环境着实让人羡慕:脚踏两只船,有了工厂还有责任田。
“衣食足,礼仪兴”。不管是商家,还是店主,他们都深信,生活富足的“德钢”人,不可能为区区几个小钱丢“德钢”的脸。
距德阳城南七公里处,有一座占地六十余亩,集古今建筑于一体,富丽堂皇的“南春园”,雕栏玉砌,假山亭榭碧绿色的瓦,在阳光下闪动着翡翠色的光。乳白色的地面,莹白如玉,穿行于古色古香的亭楼,如置身在琼楼玉宇的蟾宫。
园中有树,林内有鸟,树上有花。几名游客,静悄悄地踏着树下柔软的草地,消失在花林深处,消失在这七彩缤纷的庭园里。
园中有水,水在池中,水里有鱼,水上有艇,艇内有人。有的垂钓,有的划桨,好一副悠游的模样。
风中带着勾起食欲的香味,是园中酒楼的厨师在为游客准备美味。
楼阁内,有人在轻歌曼唱。天地间充满了祥和宁静。
需要提醒的是,这花了近两千万元构建的人间仙境,仅是“四川省德钢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固定资产的一小部分。还要提醒的是,当您走进“南春园”,可别忘了到“南春园”的后门去看看,那里有副楹联:
巍峨皇庄千古一井名扬蜀中谢花蕊;
沸腾钢厂当今百强福利桑梓酬邓林。
从这副楹联开始,说一说往昔,谈一谈今朝。
没有机会遇上此副楹联的作者,原八角井镇文化站的站长李本超老先生,也就没有机会向他请教上联“谢花蕊”的本意,不知是说应该感谢那个“花蕊夫人”呢,还是应该把那朵“花蕊”给“谢”了,让她“滚蛋”呢?以今天八角井的情势,是应该让她“滚蛋”的成分多一些。
花蕊夫人,这个前蜀王孟昶的宠妃,在绵远河双平渡(今八角井)修建的“孟蜀皇庄”,对她而言,其意义和杨贵妃之于“华清池”没有什么两样:游玩享乐。也许正是因为她的奢侈,才会使她的老公成为古蜀国“最后的君王”。在君王的前面冠以“最后”,就标志着一代王朝的毁灭,其下场,不但可耻,更是可悲。杨贵妃有了“华清池”,李隆基经营的“开元盛世”就算到头了,大唐帝国就由盛极开始滑向衰落。
对于今天的八角井镇人来说,创业多于享乐才是为他们普遍接受的。
花蕊夫人,虽贵为王妃,但她偏爱武功,善骑射。
公元960年,一个深秋,一匹枣红色的逍遥马,一个戎装如练的女人,一张让雁落、让鱼沉的俏脸,红马疾驰,驮着她冲进了这片人迹未至的原始森林。
她有一张让人销魂的脸,更有一副让人蚀骨的腰。
她的腰就像蛇一样,甚至比蛇更灵动柔软,更善于转折扭曲,随随便便地就可以从任何人都想不到的角度扭转过来,忽然间从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地方扭转出去。扭转的姿势诡秘而优美,无论从哪种角度去看,都似乎是一种超乎完美的舞蹈,尽管她骑在马上,看似随便扭动,却可以让好多专业舞蹈演员失去颜色。
她在马上的扭动,不是因为舞蹈,而是因为打猎。
她盘马弯弓,俊目流盼,玉臂轻舒,将一支支宫廷御造的箭,无情地射向林莽深处的獾犀羚麋、潜鳞飞羽,紧接着,就有了走兽临死前撕心的惨号,有了飞禽绝望的哀鸣,伴随着银铃般的娇笑,划破了这沉寂万载的土地用“面若桃花,心如蛇蝎”来形容这个叫“花蕊夫人”的女人,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古蜀国的臣民,遇上了这么一个“内当家”,便有苦受了。
名花倾国两相欢,
常得君王带笑看。
这是李白在《清平调》中讽刺杨玉环和李隆基的,但用在蜀王孟昶和花蕊夫人的身上也同样合适。
云想衣裳花想容,
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琼玉山头见,
会向瑶台月下逢。
花蕊夫人的绝色丰姿,只能用“天仙”来形容。所谓“仙”者,就应脱离凡俗。
蜀王后宫,深宫紫苑,铜雀深锁着一群纸醉金迷的俗人,他们糜烂,他们纵欲,满足着、宣泄着他们低级卑贱的欲望,他们是花蕊夫人不屑一顾的凡夫俗子。
“仙”就应有“仙”的去处,“仙”的去处应是蓬莱仙境,月上蟾宫,九天之上的琼楼玉宇,但这些地方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辽阔的蜀中大地,难道就没有如“仙”般的花蕊夫人可去的地方?
蜀王孟昶就不信那个邪!
以好色名播九州,以爱美人不爱江山而彪炳史册的孟昶,看着蛾黛深锁,一脸戚然的花蕊,真是看在眼里,痛在心中,她是那样孤独与失落,娇艳欲滴,却又楚楚可怜。没有一个男人能拒绝如此这般女人的请求,那种极具哀怨而凄美的诱惑,足以让任何男人为她付出一切。
孟昶答应她的请求,也就注定他将为此付出一切。
名花真的可以倾国,当他成为蜀王中的可耻“最后”时,他似乎明白了。
但当时他还不明白蛾眉惑主的道理,他只是埋怨自己,若非“爱妃”提醒,自己怎么没想到,完全可以在权力范围内造一座人间仙境。
在那远离凡尘的地方,他与花蕊夫人,幽会于月下,相见于琼山。
选址,绵远河东山双平渡(八角井),花蕊夫人常去打猎的地方--一座行宫拔地而起。若把秦王朝诸君比作“兔子”,孟昶就只能算作缸中的“泥鳅”。兔子是不吃窝边草的,秦王诸君,为建“阿房宫”,也许是出于本地区“环保”考虑吧?不惜涉千里,越秦岭,让蜀山秃。
“泥鳅”就只知道耍“团转”(近邻)了,比起秦王朝诸君来,他至少知道节俭,知道就地取材,但他不知道“竭泽而渔”的害处。
于是,兽走了,禽飞了,碧树千里变作一片贫瘠荒凉,一幢人造的仙境起来了--孟蜀皇庄。
孟蜀皇庄有多大的规模,花蕊夫人有诗为证:
龙池九曲远相通,
杨柳丝牵两岸风。
常似江南好风景,
画船来往碧波中。
孟蜀皇庄建起来了,却留下了千年的罪孽,它让在这儿休养生息的人们,饱尝了生态遭破坏后带来的千般苦果:
八角井,河坝多,
捧着石头望馍馍。
春天无雨难下种,
夏天洪水冲掉窝。
日子本比黄莲苦,
还要加上大肚(血吸虫病)多。
孟蜀皇庄最终成为一代王朝没落的象征、古蜀国耻辱的印记,所以就没有人再来关心它今后的命运。
谁能想象,这座在这里有史以来最辉煌的建筑,该是一个怎样的结局,或毁于战火,或在无声无息中消失至少生活在现代的人们是无法回答的。站在这座宏伟建筑的遗址前,除了徒增吊古的惆怅,什么也留不下。
斗转星移,多少王图霸业均成空,多少富贵荣华皆云散。孟蜀皇庄内,只留下了一口深数丈,形八方,为砖所砌,玲珑剔透,色如黄金的琉璃井了。后遂以八角为名,称八角井。
井中水常年不枯不满,味苦涩,如一个久经沧桑的老人,又像一个年老色衰的怨妇,在不急不缓地诉说人世的苍凉,命运的无常所以,我们有一百种理由,让花蕊夫人这朵花永远地“谢”去,却找不到一种让我们感谢她的理由。
这块土地,自从她跑马圈地似地从大自然中掠夺过去后,就饱尝千年之久的贫穷的折磨。历史的车轮,碾过了无数次“春种”希望,也碾碎了无数次“秋收”梦想。
深挖啦,细铲呀,这片土地,经过一次又一次杀鸡取卵似的索取后,已经变得贫瘠了,吝啬了,就是掘地三尺深耕细种,也无法让生活在这儿的人们腹内不饥身上暖。一汪苦涩的井水,留下千年痛楚的咀嚼,也留下了千年深邃的思索。
贫瘠的土地,厚种薄收,禁锢着在这儿生活的人们所有美好欲望,他们把所有“穷则思变”的幻想,寄托在“张铁嘴”、“王半仙”的摊前,几文血汗钱换来几句大吉大利、玄之又玄、自我陶醉的精神安慰。
只要你做到忠恕,能隐忍,驯如牛马,这样的好人定有好报,今生不行,报在儿孙,儿孙还是不行,就报在儿孙的儿孙一辈又一辈的希望,一世又一世的落空,幸福就诠释在那根滋味辛辣、知足常乐的旱烟管里,在懒散、百无聊赖中打发组成生命的时光:“一个月过年,三个月种田,八个月赌钱。”“钱少,我少用;粮少,我少吃;衣少,我少穿。但我耍了玩了算享受了。”这是原来八角井人常自我安慰的一句话。
如果命运是由神定,那么神无疑也具有和人一样的劣根性,它不但嫌贫爱富,而且还落井下石。
生在八角井的人们,除了忍受缺衣少食,前程黯淡,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乏外,他们本就不算强壮的身体,还要经受另一种致命的威胁:血吸虫。
血吸虫,以其残忍的嗜好着称于世,它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一个又一个地忍受着如万蚁蚀骨般的痛楚,在万分恐惧中,感到自己的肉体在一点一点地失去功能,自己的生命在一寸一寸地消失,自己的魂魄在一步一步地离他而去。
在中国的民间,有句最恶毒的诅咒,就是“千刀万剐”,明朝的皇帝把这民间的诅咒,还真地改作了刑法,冠名“凌迟”。
“凌迟”处死,大忠大勇的袁崇焕挨过,大奸大佞的刘瑾也挨过--那是一种惨绝人寰的漫长的死亡过程。
比起凌迟的惨烈,血吸虫戕害人的生命不需要任何设计,就能制造出比千刀万剐还要森然的图景--几根如衰草般的头发,双目深凹于眼眶,扑闪着油尽灯枯时幽蓝的光,大大的脑袋,没有一丝肌肉的脸,一张蜡黄色的皱皮,包裹着几根如柴的枯骨,腆着一个大肚,如鬼魅在人间行走。
血吸虫把人体当成是最为残酷的游戏场,如同玩牌一样掂量着,如何才能把人的血液吸得一滴不剩,把人体的所有器官包括肤发,破坏得最干净彻底,它们要让人把死这件事变成一个可供细细品味,慢慢咀嚼的漫长过程。
凌迟的时间,至多不过两天,而这一个死亡过程,不知道要拖多久。
几个月前,一月前,半月前,还是那样的强壮、健美的躯体,短短的时间里,就被血吸虫吸光了体内所有的一切,成为一具如同风干千年的木乃伊,一具如春蚕丝尽的空壳。
整个村子失去了往日的生气。
这便是昔日的八角井。
这是一片多灾多难的土地,这是一片苍天不怜的土地。
几乎一无所有的八角井人,依然抛不下被称之为故乡的地方,没有去寻找适彼之乐土,坚守在他们祖先漂泊旅程中落脚的最后一站。
一年一度,拖着沉重的身躯,在大地上,撒些微薄的希望,收割着一茬又一茬的辛酸。
又打米,又磨面。
劳动才投三角半。
曾任生产队会计,现在是“德钢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王周龙,经常忆苦思甜,向集团公司年轻的干部职工讲述这些往事,每讲一次,都会引来一阵阵感喟,感喟声中,听得出有不怎么相信的成分。但在“文革”期间这是事实。
希望的火光,就像摇钱树、聚宝盆之类的故事,忽远忽近,时隐时现,一个,又一个传说八角井中,有一深居蛰龙,只要它一出现,自然风调雨顺,民殷物阜。
仅就这一点渺茫的希望,不知有多少八角井人,为此付出如宗教徒般的虔诚,为这传说中的神灵叩尽响头,焚香点蜡,献上祭牲,然后开始等待它的垂怜。
一年又一年,年年失望年年望,等老了人,等老了山,可是这个受尽人们顶礼膜拜,大吃冷猪肉的神龙,连一片甲都不现一下。
失望之极的八角井人终于明白了,吉祥和幸福,是拜不出来的,而死守这片田地也是干不出来的,得另寻门路。
不知起于何时,也不知最先缘于何人之口,说八角井下有座盐山,只要钻孔取出,就像售水取利那么便当。
被贫困折磨久了的八角井人,将对幸福的渴望化作热血,他们寻津问故,求师访术,以前所未有的热情与速度,翻遍井下最深处的每一个角落,结果呢?地也窘迫,人也惭愧。发财梦再次破灭。
还是冒出一个敢吃螃蟹的人。
此人曾任“德钢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党委书记,当年担任过公社副书记,他叫李化旭。这个看似孱弱的人,不知哪来那么大勇气,竟率先办起了几家孵化房,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一年下来盈利逾千。一时群情激奋,竞相效仿。
但在那个荒诞的岁月,致富都会被烙上耻辱的印记,贫穷倒成了一件十分光彩的事。这点微若寒星的希望之光,很快被视作洪水猛兽,当成资本主义尾巴,被无情地割去了。“书中自有黄金屋”。千百年来,读书成为中国人追求富贵的捷径,“几多白屋出公卿”的故事,谁都耳熟能详,谁都能随口说出几个来。
唯贤是求,何贱之有拣金于沙砾,岂为类贱而不败?度木于涧松,宁以地卑而见弃?但恐所举失德,不可以贱废人。
读书这条路,该是有多么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啊,但就当地而言,除了知道罗江有李氏一门三进士之外,好像没有听说有几个人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
但不要忘记了,李调元他们是生在罗江,而不是在八角井。
要想能“一举成名天下知”,就得有供养“十年寒窗”的银子。朝不保夕的八角井人,哪来供养他们的子弟苦读十年的余钱。
当兵吧,当兵也不失为条出路。
一顶绿军帽,一曲“向前”歌,或许真的可以成为年轻人的希望。但是,这块土地几经血吸虫肆无忌惮大施淫威,整个八角井,竟找不出几个体检合格之人,有一年还得从邻乡借三人才能完成规定的五人招兵指标。
从大炼钢铁到大寨田,从撮土造肥到双季稻,八角井人几乎将这块弹丸之地抄了个底朝天,也没能出几枚让他们丰衣足食的小钱。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人们在自己倒霉的时候,常这样自我安慰,但八角井人心中的“又一村”在哪儿呢?
不远,就在离八角井不到二百米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寺庙,叫朝阳寺。
朝阳寺,那是孕育着八角井人希望的地方!
朝阳寺,是一座寺庙,但它供奉的神灵,不是菩萨,而是一名武将,相传是三国名将汉州太守邓芝。
据传,邓芝晚年因痛恨阿斗刘禅降魏,故隐居于此,削发为僧,在今八角井柳沙村修建禅院一座。又因古代神话里把大树称为邓林,加之邓芝姓邓,来个二邓合一,取名“邓林禅院”。
邓芝故后,历经风雨沧桑,寺院经维修后,更名“朝阳寺”。
但不知为什么,名更了,供奉的神灵也变了。
任何人都想象得到,当时邓芝在此削发为僧,供奉的决不是他自己。
难道邓芝真的成了佛?值得后人把他当作神来敬奉?
凡上了年纪的八角井人,都还对朝阳寺有残存的记忆。
历经千年的风雨,朝阳寺已经荒芜,荒芜的庭院中,凄冷败落的庭台间,凋零的草林深处有几间雕梁画栋的砖木建筑,尽管破败,也能显示出往日香火鼎盛时的残迹。自从那些上了年纪的八角井人有记忆开始,庙中香火就冷落下来了,至于原因,可能是八角井人对邓芝已经彻底失望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