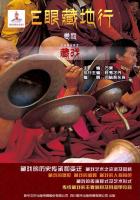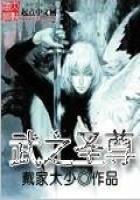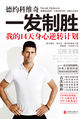……于是终于有一批学生脱颖而出,冲破文明的制约,挖掘出自己心底某种已经留存不多的顽童泼劲,快速培植、张扬,装扮成金刚怒目。硬说他们是具有政治含意的‘造反派’其实是很过分。昨天还和我们坐在一个课堂里,知道什么上层政治斗争呢?无非是念叨几句报纸上的社论,再加上一点道听途说的政治传闻罢了,乍一看吆五喝六,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主动性。
张育仁先生写到这里,特别强调,以上是余秋雨关于红卫兵中“造反派”一方的开脱性描述。当谈到自己时(即余秋雨),就更是开脱加原谅了:
反过来,处于他们对立面的“保守派”学生也未必有太多的政治意识,多数只是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颠荡中不太愿意或不太习惯改变自己原先的生命状态而已。我当时也忝列‘保守派’行列,回想起来,一方面是对‘造反派’同学的种种强硬行动看着不顺眼,一方面又暗暗觉得自己太窝囊,优柔寡断,赶不上潮流……
张育仁还强调,这些年,他还不止一次听到身边的一些知识分子朋友,在读“秋雨散文”时记忆犹新地提到当年他的那篇曾一度影响很大的《走出“彼得堡”》。
余秋雨在《千年庭院》一文里的这两段话,其实确实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当时连饱经沧桑的人很多都弄不清谁是谁非,何况当时的余秋雨涉世未深。那个时候,人人都热爱毛主席,拥护共产党,但谁是真正的革命者,谁也证明不了谁,谁也说不清楚。每个人都处在历史的进程当中,都是局内人,在政治问题上,局内人永远看不清自己的对与错。
张育仁先生所指的余秋雨《走出“彼得堡”》一文究竟写的什么,大部分读者还不知道。胡锡涛先生介绍了这篇文章的内容:“《走出‘彼得堡’》写得很俏皮,恰是应景之作。此文强调文化人走出文化的小圈子,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与工农相结合,这是与‘文革’的极左路线相符合的。余秋雨这篇文章,是尊命而写还是自愿而写,我不知道;但它的客观效果,肯定不好,完全和广大文化工作者的心愿相反,‘文革’时期文化人都被赶到乡下或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已经活得够累、够辛苦了,都想回到原来的岗位上重操旧业。1973年,有的人刚刚回到城里恢复工作,有的人则还在乡下做‘回城梦’,正在这做梦、圆梦的时候,余秋雨发表此文,给了当时文化界人士当头一棒,使他们非常恼火:你余秋雨高高在上,写文章唱高调,还要叫我们‘走出彼得堡’,永远在下面吃苦头,岂不可恨?这种心态上的不平衡、不服气,应该说,是正常现象,人们至今回忆起当时的这篇文章,仍然耿耿于怀,怒气未消,也属情有可原。余秋雨应该在反思‘文革’的同时反思自己,反思当年为什么写《走出‘彼得堡’》。”
这篇文章是与极左思潮相吻合的,但这种文章在当时来说像每家每户都要吃的青菜一样的平常,坐在那个位置,如果不这样写就根本不可能发表,甚至会被认为是立场问题,轻者批判,重者可能蹲大狱。下面跟着上面走,群众跟着路线走,人人都这样,要说错,也错在当时的极左路线。如果把这种特定历史时期时的作为当作揪住不放的由头,确实有些可笑。
除上面列举的批评外,余秋雨当年在写作组的“同事”孙光萱也写了一篇《正视历史,轻装前进》的长文,在2000年4月6日的《文学报》上发表。孙光萱这样写道:“石一歌”写作小组不是学术团体,而是“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之一,余秋雨是这个写作小组的重要成员,他于1973年离开后上调到更核心的写作班文艺组,担负着帮“石一歌”改稿的重任,同时还帮助姚文元修改其旧著《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做资料准备,余秋雨在粉碎“四人帮”后代表“石一歌”出访日本,其任务并不是他吹嘘的监督朱永嘉,等等。
介绍余秋雨进入写作班子的胡锡涛先生,分析和纠正了孙光萱以上观点,并将余秋雨入围写作组的事迹,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外围,即在复旦大学宿舍那幢楼。“石一歌”的笔名产生在外围,也在那幢楼。“石一歌”确是“十一个”的谐音,但余秋雨不是十一个中的一个,外界把余秋雨当做“石一歌”,或看做“石一歌”的主力,纯属误会,瞎猜。“石一歌”产生时,余秋雨尚未报到。他入围后,曾参与讨论或修改“石一歌”写的文章,也没啥了不得。“石一歌”与“丁学雷”、“罗思鼎”是两个档次的笔名,外界不明真相,把三个笔名捆在一起,也多少有点误会。虽然“石一歌”后来也成了名牌,但究竟不是正宗老字号。
第二阶段是在内围,即当时上海写作组所在地康平路89号。进入内围的人,除了余秋雨,还有十来个从工厂抽上来的青年笔杆子,他们都是写作组作为‘苗子’来培养而使用的;余秋雨怎么会从外围被选入内围?就在于他才华出众,文笔漂亮,写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文章而深得头头们的欣赏。其中,有两篇文章尤为重要,一篇是用笔名“任犊”写的《走出“彼得堡”》,在上海《朝霞》发表。另一篇是《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由上海王知常寄给北京《红旗》采用。
又是上天的恩赐,爱读书的余秋雨在蒋经国先生山间的这所读书室里,寻找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读不到的书,他感受到的是久违了的快乐,这种快乐是强烈而持续的,他惟恐突然被人夺去,他已习惯在这里静静地看书,连毛泽东去世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他也是从两位过路村民嘴中得知的。
对于自己文革时期的行为被人批判,余秋雨在《借我一生》中进行了回应:
我知道“文革”十年间不管是早期的写作组还是后来的写作组系统都有过比较神气的岁月,但我都没有遇到。
徐企平老师、盛钟键老师等人曾经一再试图借取宏观世界的一丝须蔓,来拔救我的陷于大难的全家,也没有做到。我遇到的,恰恰是工总司拿着尚方宝剑刺在它喉口的那几个最可怜的月份,它却很不仁义地把我的躯体塞在剑刃边上。当剑头稍稍松开,我就走了。
关于余秋雨在“文革”中的写作或者说表现,我想李美皆先生在《文学自由谈》2004年第6期的一段话说得很到位:
不必感叹人性的不完善,人性永远是丑陋的,自己也不尽完美。也不必怨恨上天的不公平,这恰恰是公平的,这很符合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使人看到了某种类似于天道的东西。所谓天道,也许本来就是摆平人心的那种神秘的制衡力量吧?余秋雨现在稍微有点不舒服,那就对了,你已经舒服了那么久,让别人舒服一下也是应该的……《论语》中有一句话:君子不以一言举人,不以人废言。余秋雨并非大恶,围绕余秋雨的纷扰应该结束了。虽然人和文都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作家、学者,主要还是应该靠文章来站住脚的。而对于读者和批评者来说,重要的不是鸡,而是鸡蛋,离开他的文去谈论他的人对于大家有什么意义呢?青年批评家张闳说得好,纠缠于余秋雨在‘文革’期间的所作所为,只能抹杀“余秋雨批判”这一文化行动的真实意义。
是的,在那样一段浩劫的岁月里,人的意志几乎完全受到客观环境的箝制,其一言一行以今日之眼光审视必然有对有错,事过境迁再度挑起,并抓住紧紧不放,实在没有太大的意义。
四、感受千年庭院
那是60年代末,余秋雨正和同学们在全国进行大串连。他这样描述当时学生在列车上的情景:
学生们像蚂蚁一样攀上了一切还能开动的列车,连货车上都爬得密密麻麻,全国的铁路运输立即瘫痪。列车还能开动,但开了一会儿就会长时间地停下,往往一停七八个小时。车内的景象更是惊人,我不相信自从火车发明以来会有哪个地方曾经如此密集地装载过活生生的人。没有人坐着,也没有人站着,好像是站,但至多只有一只脚能够立地,大伙拥塞成密不透风的一团,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则横塞着几个被特殊照顾的病人。当然不再有过道、厕所,原先的厕所里也挤满了人。谁要大小便只能眼巴巴地等待半路停车,一停车就在大家的帮助下跳窗而下。但是,很难说列车不会正巧在这一刻突然开动,因此跳窗而下的学生总是把自己小小的行李包托付给挤在窗口的几位,说如果不巧突然开车了,请把行李包扔下去,车下的学生边追边呼叫,隆隆的车轮终于把他们抛下了。多少年来我一直在想这件事:他们最终找到下一站了吗?那可是山险林密、虎狼出没的地方啊。
余秋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到达了湖南的岳麓山,这里到处是人,他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只知道尽快往前走,想摆脱这熙熙攘攘的人群。突然,他看到了一条偏僻的小路,几个弯一转便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天渐渐暗了下来,四处显得神秘而空静,他停下脚步,环顾四周。他看到前面不远处有一堵长长的旧墙,围住了很多灰褐色的老式房舍。他感到好奇,也有些兴奋。他沿着墙走了几步,就看到一个门,轻轻一推,门开了,他将脚跨进去的时候,心里有点慌乱,还假装咳嗽了几声,以引起里面人的注意。他觉得这地方似曾相识。他的脚步在这里磨蹭着,一种无形的力量钳制着他,他要搞清这是什么地方,终于他看到了一个石碑,上面写着四个字: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创建于公元976年,是世界上最老的高等学府之一,也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岳麓书院是著名的文化学术中心,在海内外有着很高的威望。一千多年来,这里聚集过很多一流的学者、教育家,其中包括文化哲学大师朱熹、王阳明、张栻,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哲学大师王夫之、理财大师陶澍、启蒙思想家魏源、军事家左宗棠,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岳麓书院的气势也应验着它的魂魄,“道南正脉”的牌匾,高悬在岳麓书院讲堂的正梁上,匾中的“道”指理学。北宋时期理学在洛阳传播,南传之后,逐渐形成了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派和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道南正脉”的意思就是这里是理学向南传播的嫡传正统。
公元1167年,朱熹和张栻在这里持续讲学两个多月,前来听讲的学者达千余人。据说有一次他们三天三夜没睡觉,辩论得十分激烈,这被看作是岳麓书院历史上最经典的一次学术盛会。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岳麓书院闻名遐迩,湖湘学派在中国学术界的历史地位就此确立。
在《山居笔记》中,余秋雨这样阐释了岳麓书院这座千年庭院的深远意义:
书院的出现实在是一批高智商的文化构想者反复思考、精心设计的成果,它既保持了一种清风朗朗的文化理想,又大体符合中国国情,上可摩天,下可接地,与历史上大量不切实际的文化空想和终于流于世俗的短期行为都不一样,实在可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让人赞叹不已的创举。中国名山间出现过的书院很多,延续状态最好,因此也最有名望的是岳麓书院和庐山的白鹿洞书院。
这个庭院的力量,在于以千年韧劲弘扬了教育对于一个民族的极端重要性。我一直在想,历史上一切比较明智的统治者都会重视教育,他们办起教育来既有行政权力又有经验实力,当然会像模像样,但为什么没有一种官学能像岳麓书院那样天长地久呢?汉代的太学,唐代的宏文馆、崇文馆、国子学等等都是官学,但政府对这些官学投注了太多政治功利要求,控制又严,而政府控制一严又必然导致繁琐哲学和形式主义成风,教育多半成了科举制度的附庸,作为一项独立事业的自身品格却失落了。说是教育,却着力于实利、着力于空名、着力于官场,这便是中国历代官学的通病,也是无数有关重视教育的慷慨表态最终都落实得不是地方的原因。
余秋雨认为,岳麓书院能够延绵千年,除了上述管理操作上的成功外,更重要的是有一种人格力量的贯注。对一个教学和研究机构来说,这种力量便是一种灵魂。一旦散了魂,即使名山再美,学田再多,也成不了大气候。他还认为,教学,说到底,是人类的精神和生命在一种文明层面上的代代递交。这一点,历代岳麓书院的主持者们都很清楚。他们所制订的常规、学则、堂训、规条等等几乎都从道德修养出发对学生的行为规范提出要求,最终着眼于如何做一个品行端庄的文化人。
自从余秋雨串连到岳麓书院的那一刻起,他便坚定了要做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决心。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怀着这样的信念,他一做就是二十多年。余秋雨认为,人的一生很短暂,既然选择了教育事业,就要将师生的情分看得高于一切,将师生的生命紧紧地维系在一起,老师对学生的投入不应谈什么回报,而只能将自己生命涌动的精髓,将自己毕生的知识传承给学生。这就是余秋雨最大的幸福。在岳麓书院,余秋雨感受着千年庭院,更继承着千年庭院的精神,那就是:不问结果,一定要将文化无私地传授下去。
在余秋雨初次邂逅岳麓书院30年后,即1999年7月11日,余秋雨重返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并登山讲坛,发表了题为《走向21世纪的中国文人》的演讲,并回答听众及网上观众提问。湖南经济电视台及其网站同时直播了这次演讲。这次演讲后被文化界称为“岳麓书院事件”。
余秋雨清楚地记得,这天天公不作美,雨一直下着。但大家听说是余秋雨教授来演讲,都不愿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听众们一个个站在雨地里,穿着雨衣,打着伞,墙壁四周也站满了人,余秋雨很是感动,也有些意外,他向大家不停地表达着谢意。
能被邀请到岳麓书院演讲,余秋雨不仅感到荣幸,也感到一种责任。他始终没有忘记这是一所千年学府,这个定位使得他既明智也谦虚。湖南电视台把他的演讲定位于“余秋雨设坛千年学府”。他感到有些惶恐,在《余秋雨寻找文化的尊严》中他这样表述:“从我的内心来讲,‘设坛千年庭院’,把它变成‘朝拜千年庭院’更合适一点。主语不是我,不是‘余秋雨设坛千年庭院’,应该是‘众学子朝拜千年庭院’。我相信在今天这个下午,这个场合,就合适了,大家坐在这儿也心安理得了。”
余秋雨在《走向21世纪的中国文人》的演讲词中,着重讲到了“四座桥”。
第一座他称之为“经典学理之桥”,即中国古代的经典之作,它们对世界文化产生了深厚的影响,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大约在17世纪,西方很多传教士来到中国,来得最多的是耶稣会的传教士,他们想在中国占领一个庞大的传教士市场。结果他们有些惊奇地发现中国先秦哲学中的一些思想非常值得研究,结果他们还把中国先秦哲学传播了回去。比如,他们翻译了孔子、孟子的一些书,还写了《孔子传》,之后,中国的哲学在西方的影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比如,一个没有来过中国的欧洲学者,如果他要写一本世界哲学史,他就会把前面很长的篇幅留给中国古代哲学,这是中国古代哲学了不起的成就,真令世界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