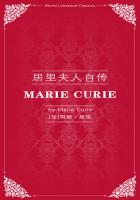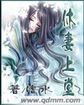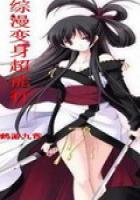柳大华称得上性情中人。每每接受采访,总是直抒胸臆,不喜矫情,因而也引发颇多争议。“老伴总是埋怨我,嘴上没个把门的。”回顾自己的棋坛生涯,他依然语出惊人。
在柳大华的象棋世界里,有1对19的盲棋壮举,有包括两次全国个人冠军在内的一系列头衔,他个人最看重的,是1980年将当时正如日中天的胡荣华推下神坛。然而在两度登顶之后,他就与全国个人赛冠军缘悭一面。
“征战棋坛这么多年,战绩也还算可以。但是只拿过两次个人赛冠军,夺冠次数在国内仅排第七,我心里一直不服这个气。”谈及棋坛生涯恨事,柳大华相当坦诚。
他表示,从技术上、记忆力上来讲,自己都不输于他人,关键是粗心、急躁的性格,导致多次在关键时刻出现低级失误,最终与冠军无缘。
“我这一辈子都争强好胜,到老也只是稍微淡了一点儿。不过正是这种不服输的性格,我才能走到今天。”柳大华淡淡地说,“现在我的身体状况不错,也许以后还会给大家带来惊喜。”(作者:邹谨)登山运动
△陈山——攀越冰峰览众山
现代登山运动在武汉出现较晚,仅在与野外勘测有关的部门,结合专业开展,铁道部第四勘测设计院和武汉地质学院是其中最著名的。铁四院出了个登上过公格尔九别峰和希夏邦马峰的陈山,地质学院先后为国家培养输送12名登山运动健将(先后多次登上海拔7 000米以上的祁连山主峰、昆仑山慕士塔格峰、青海积石山主峰、西藏纳木那尼峰等)。陈山是其中最早有影响的登山运动员。
攀越帕米尔次高峰列宁峰
陈山,1934年12月出生于黄陂祁家湾,原名陈三,后因喜爱登山运动改名陈山。陈山参加工作就进入铁路部门。1958年,国家体育总局为了准备与苏联联合登上珠穆朗玛峰,开始组建专门的登山队。当时,从铁路、林业等野外作业部门以及地质大学、石油大学和公安部、军队抽调了100多人。24岁的陈山就是这次入选的。
1958年7月,苏联以100名登山功勋运动员集体签名的形式,分别向苏联国家元首和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中苏共同攀登世界第一高峰的倡议。两国政府代表团于7月下旬在北京举行会谈,达成协议,决定1959-1960年两年内组成联合登山队攀登珠峰。按协议规定,中国于1958年8月下旬派46名登山运动员前往苏联集训;10月初,苏联派出3人前来中国,与中国队员一起前往西藏,对珠峰进行登山前的路线侦察。根据协议,中方承担修筑一条从日喀则经聂拉木、定日直到珠峰山脚登山营地的长达320公里的公路,以便运输车辆从拉萨直抵基地;根据苏联建议,中方从苏联购置两架AN-6型高空侦察机,并负担30名苏联队员和官员在中国期间的食宿和交通费用;苏方负责供应30名中国队员的高山装备、氧气设备和攀登工具以及部分高山食品(当时中国不能生产这些物品)。两国联合侦察队如期完成路线侦察,中方按照协议完成自己的义务后,中苏双方于1958年12月最后商定,1959年3月20日,苏方队员抵达北京,立即飞往拉萨进入基地营,正式着手攀登。
1958年,陈山等中国登山队员先是在新疆天山进行适应性集训,后来到苏联中亚地区,由苏联的功勋教练员进行专业训练,最终的目标是要登上位于帕米尔高原、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边界上的外阿莱Trans-Alay山脉最高峰——列宁峰(海拔7134米)。(帕米尔高原的最高峰是位于塔吉克斯塔共和国境内的加尔莫山Garmo)列宁峰陡峭的山侧有厚达数百米的冰川覆盖,路途遥远,常常有雪崩发生。经过训练,这一年9月7日,陈山等中国登山队员攀越了列宁峰。
冲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
回国后,陈山作为技术骨干,1959年有几个月在天山地区为地质部测量队进行登山训练。年底,他到了拉萨,为1960年中苏联合攀登珠峰做准备。但是这年底,由于中印关系紧张,苏联出于在中印边界地区不能表现得与中国很热火的考虑,借口“苏联队员一年内都没有进行训练”,取消了两国1960年联合攀登珠峰的合作协议。
面对这种形势,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问中国登山队:“他们不干了,我们自己能不能干好?”队员们一致表示:“我们自己一定能干好!”周总理了解到中国登山队缺乏攀登8000米以上高峰的装备和工具而国内暂时又无法生产这一情况后,与刘少奇、陈云、李富春、贺龙等商议后,批准拨款40万美元,由中国驻西欧使馆协助购买所需的各种高山装备。
1960年3月19日,陈山与全部210名登山队员全部进入珠峰脚下海拔5200米的基地;同时,上百吨从国内国外采买的装备和食品也安全运到。20多顶大型帐篷组成的基地营,形成了一个新的村落。
3月24日,陈山作为二线队员,保障物资运输,到达6400米高度,在这里建第3号营地,并担任第二大本营的营长。副队长许竟问陈山:“你还能上吗?”陈山坚定地回答:“能上!”4月6日,登山队从基地出发,越过最危险的绒布冰川、冰裂缝地区,6天后登上7007米高度的北坳。全队有40人越过北坳并将大批物资运输上去。5月2日,陈山和队员们克服被风吹倒和滑坠的危险,越过了7400米的一个大风口。陈山最高到达7600米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这一次,由于天气原因,中国登山队先是撤回基地,后来王富洲、贡布、屈银华3人于5月25日4点20分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这是人类第一次从珠峰北坡登顶成功——1921年到1938年,英国人用了17年的时间,7次到北坡侦察、攀登,有10余人遇难,均告失败。被第二台阶阻退的英国人说:这里没有攀援的支点,横亘着世界上最长的路线,它无尽无边。英国人宣布北坡“飞鸟也无法逾越”。
攀越“白色的帽子”公格尔九别峰
1961年,根据国家体委的安排,中国登山队当年的任务是以训练为主,在新疆境内海拔7595米的公格尔九别峰进行思想、技术、战术和身体的全面训练。同时,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争取再创女子登山世界纪录。
公格尔九别峰属于西昆仑山脉,海拔7595米,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布伦口乡苏巴什村,是西昆仑山脉上的第二高峰,由于山上终年积雪,犹如牧民头上所戴的帽子,所以当地牧民就称它为“公格尔九别”,语意为“白色的帽子”;因它高度略逊于公格尔山(7719米),也有人称它为“小公格尔”,但它的山势地形却丝毫不逊于公格尔山。北坡是陡峻的峭壁,南坡是复杂的冰雪地。
西藏参加这次训练、登山活动的有打破世界女子登山纪录的西绕、潘多、齐米和查姆金4名藏族女运动员,男队员有多吉甫、拉巴才仁和医生陈宏基。中国登山队由57人组成,北京登山营营长袁扬(女)任队长。
5月12日,队伍离开喀什进山,当天到达设在卡拉库里湖边的登山大本营。此前派出的侦察组已先期到达,并已上山进行路线侦察活动。5月16日,队伍开始第一次适应性行军,当天到达4320米的山上宿营。后来将攀登路线转移到公格尔九别冰川西山脊。
5月26日开始第二次行军,目的是取得高山适应能力和运送部分物资到4900米处的过渡营地,并在那里进行了两个小时的冰雪技术训练。5月28日,经过一天的行军到达了5500米处宿营。29日又上到了6200米处,并在这里宿营。当天天气很坏,时而烈日当空,时而大雪纷飞。5月30日10点半,大队人马由6200米营地下山,下午7点半回到大本营,完成第二次行军计划,为突击顶峰创造了良好条件。
突击顶峰从6月11日开始,陈山担任突击队长,当天到达4600米营地。第二天,又登到5500米处宿营。6月13日,由于天降大雪,突击队在营地停留了一天。6月14日,由5500米处顺利登达6200米处,并在此处宿营。6月15日,突击队登到了6800米处的雪坡上,并在此处宿营。这天,他们在通过称为“鼻梁”地段的时侯,由于地形复杂而积雪又很深,队伍行动很缓慢,一直到下午6点多才到达营地。6月16日,有5人由于高山反应太重被迫下撤,其余人员登到了7300米处宿营。6月17日,队伍分为3个小组向顶峰作最后冲刺。当天气候由好转坏,下午一直降雪,能见度很低,队伍要经常停下来观察,确定攀登路线。高度越来越高,积雪越来越深,气压越来越低,队员们的高山反应越来越大,不时有人在行军中倒下无力起来,致使队伍前进速度越来越慢。突击队决定重新调整人员,只留下5名突击队员,他(她)们是:邬宗岳、陈山、潘多(女)、西绕(女)、拉巴才仁。(其余大部人员下撤。下撤人员摸黑下到7300米营地时,已是午夜12点了。)突击顶峰的5名队员终于在6月17日22点30分登上公格尔九别顶峰。藏族运动员西绕和潘多再次打破世界女子登高纪录。
这次登顶成功,不应忘记的是,全队下撤途中遭遇雪崩,前后有5名运动员遇难,他们是:西藏运动员西绕(藏族,女)、拉巴才仁(藏族)、医生陈宏基,北京运动员衡虎林(坠入极深的冰裂缝)、穆柄锁。还有大批运动员被冻伤致残,这是中国现代登山运动开展以来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陈山也是在这次登顶中被冻伤了手指和脚趾,造成终身残疾。他在这次登顶中荣立一等功。
攀越“黑色处女峰”希夏邦马峰
希夏邦马峰,海拔8012米,在全世界高峰中排名第14。位于中国西藏自治区的聂拉木县境内,东距珠穆朗玛峰120公里,是喜马拉雅山脉由北西——南东走向渐变为东西向的转折处。希夏邦马来自藏语,意思是“高山缺氧,气候多变”。它也曾被称作是“高僧众赞峰”(来自梵文)。全世界共有14座8000米以上的高峰。到20世纪的60年代,地球上8000米以上的高峰只有希夏邦马峰尚未被人类所涉足过,被称为“黑色处女峰”。
1964年,中国登山队决定征服希夏邦马峰。3月中旬,登山队进驻到了希夏邦马峰的脚下。因为无先例可循,登山路线的选择是非常困难的。队员们用高倍望远镜细致地观察了山形地貌之后,选择了一条可能的路线,便开始为登顶做准备。幸运的是,路线没有出现多大问题。登山队顺利在沿途建立起了高山营地,并于5月1日突击到海拔7700米的地方。从大本营里传来的消息说,第二天的天气不错,适于登顶。
5月2日凌晨6时,冒着零下25度的严寒和6级大风,突击队员们毅然出击。在队长许竞率领下,刚上升到海拔7800米的高度,迎面遇到一个平均坡度在50度以上的冰坡。黎明时刻,坚硬的冰面反射出幽蓝色的光,冰坡下方是几十丈高的岩壁。队员们必须从这里横切过去,才能绕道攀向峰顶,每一步都十分艰难而危险,他们不得不用冰镐刨出台阶,全身斜靠在冰面上,一只脚确实踩稳了,才挪动另一只脚。
为了保证队伍安全通过,队长许竞在冰坡的一端打下一个可以穿挂尼龙绳的钢制保护冰锥。当登山运动健将王富洲最后通过这里时,他双脚一滑,全身坠落了20多米,幸亏有冰锥和尼龙绳的保护,才没有发生事故。队员们为了横切过这不到20米的冰坡,竟费了30多分钟时间。
在绕过两座巨大的冰瀑区以后,突击队员们沿着一座45度左右的雪坡向上攀登。登山队副队长、登山运动健将张俊岩走在最前面。经过长期凝聚的雪,变得异常坚硬,队员们只好采取用冰镐固定一下再先后迈动两脚的“三拍法”前进。这时他们的呼吸变得更加急促,感到两腿有些酸软而沉重,上升的速度更缓慢了。他们靠在雪坡上休息了一会,又继续攀登了50米左右,然后拐向左上方,踏上一条平缓的雪脊。
这时,距离希夏邦马顶峰不过10米左右。可是由于体力的巨大消耗,大家又休息了一次。当10名队员们走完最后一段距离,陆续踏上三角形的峰顶时,眼前豁然开朗,狂风迎面扑来。当时,正是北京时间10点20分。抬头望去,太阳斜挂在东南方的晴空里;鸟瞰峰底,彩霞正从脚下飘过。登山运动健将、藏族队员索南多吉从背包里拿出一幅五星红旗和一座毛主席塑像,安置在冰雪里。张俊岩和邬宗岳用16毫米电影摄影机,把这些活动一一拍摄下来。队员陈山、成天亮和云登用照相机分别为大家合影留念。陈山在这次登顶中荣立特等功,获得体育荣誉奖章一枚。
1965年5月25日,中国邮政发行了特70《中国登山运动》邮票1套5枚,分别为中国登山队登上贡嘎山、慕士塔格山、珠穆朗玛峰、公格尔九别峰、希夏邦马峰。其中后3座冰雪高峰,都留下了陈山的足印。
考察冰川做贡献
1964年底,陈山不再从事一线登山,被国家体委派到四川省体委工作,曾在北碚准备筹建中国登山队基地。因客观条件不理想,该基地未能建立起来。1972年陈山回到武汉,担任铁四院体协秘书长。
1974年4月至1975年12月,陈山在对中国科学院冰川科学考察队队员进行了有关训练后,随队前往巴基斯坦,对巴托拉冰川进行科学考察。
巴托拉冰川位于喀喇昆仑山系北部,是世界中纬度地带内、长度超过50公里的八大冰川之一。1973年春夏之交,该冰川突然爆发洪水,将连接中巴两国的交通要道喀喇昆仑公路严重毁坏。为了解决该公路是否改线、原地修复能否保证长治久安的疑难问题,中巴两国政府决定由中国方面进行科考。
经过近一年的大量观测和复杂计算,科考队得出结论:巴托拉冰川近年来在继续前进,但它的极限前进值只有180米,最终将在距中巴公路300米左右处停止前进。巴托拉冰川前进的年限从1975年算起为16年,16年以后将转入退缩,而且这个退缩将会延续到2030年以后。有关部门根据这个结论,制定了经济合理的修复方案。后来,科考队撰写了《喀喇昆仑山巴托拉冰川考察与研究》的报告,1980年出版,其中主要部分在《中国科学》杂志上用中英文发表,并在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进行交流,受到了中外冰川学者的重视和好评。1982年,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经过评选,授予这部著作自然科学奖三等奖。这是中国冰川学建立以来所获得的最高荣誉,也是中国冰川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攀越新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