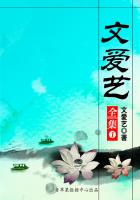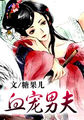每逢寒暑假,我都要到姐姐家里去看看。姐姐被家务、农活和一群孩子缠累,老得很快。从她身上,已经很难看出和左邻右舍的大嫂的区别了,她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妇,在重复着我不识字的母亲做过的一切。姐夫常在假期里开各种各样的会,我去了不一定能见到他,而姐姐则忙着为我做饭,我坐在堂屋里和她的公公说话,耳朵里却在听着从厨房里传来的“哐当哐当”的风箱声。我轻易不来,姐姐定要做点好饭菜,拉着风箱,往锅底下塞着柴火,“哐当”好几个钟头才算完事。而吃饭的时候她又不能陪我,妇女不上席。姐夫不在家的时候就临时请村上的“文化人”来作陪,说着搜肠刮肚找出来的闲话。而我是来看姐姐的啊,却一句体己话都顾不上说。在我同陌生人吃完她费了不少劲才凑齐的“四个碟子”之后,她才和孩子们坐在锅屋里享受残汤剩饭。姐姐,我的姐姐!她把自己看成一个废人,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了,巴望着我大学毕业好挣钱奉养父母,承担起做儿女的责任。
母亲没有等到这一天就在贫穷之中去世了,家里只留下父亲。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正是大学生粪土不如的年月。四十六块钱的工资要养活自己,还要结婚、生孩子、奉养父亲,一分一分地计算也难以安排。我这个农民的儿子念完了大学还穿着家乡的土布褂子,裤子上打着补丁。要在北京安一个家,哪怕置办最简陋的东西,也要四十六块的多少倍?我和妻子在一间十平方米的斗室里举行了只有我们两人参加的“婚礼”。结婚好几年连锅、案板、菜刀都没有备齐。
父亲怜惜我,没有到北京来拖累我。他仍然在贫瘠的土地上挣取连口粮都换不出的“工分”,年年决分都要“透支”,由我向生产队偿还父亲劳作一年仍然欠下的债务。进一步孝敬父亲我就没有余力了。也许家乡父老把我看成“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人了。我可怎么向他们解释呢?电影导演在前些年是挨批的角色,这几年处境不同了,但也只是“有名无利”的职业。我跑遍全国各地拍片,每部影片都花去几十万、上百万元的成本,为国家赚回成倍的利润。可我自己从去年开始每月工资才涨到七十二块五毛,并没有“富起来”啊!
父亲终于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痨病”时常发作,一个人躺在那两间茅屋里,如果半夜里一口气上不来,死了都不会有人知道。感谢我的一个当“赤脚医生”的堂弟给他打针吃药,替他挑水做饭。可是,这总不是长久之计,人们都会问:“他儿呢?不会找他儿去?”
我无法再忍受心中的愧疚,一再写信敦促父亲到北京来治病。
一九八一年秋收之后,他终于来了。
我拿着电报,去车站接他。从家乡小镇上打来的电报几经周转到我手里已经过了钟点。出站口如流的人群、无数张面孔我一个都不放过,但里边没有我的父亲。我逆着人流往里挤,在纷纷攘攘的车厢里寻找他,一直到最后一节车厢,才在已经快走空的座位中间发现了一位老人。他穿着黑布夹袄,守着几个大大的粗布包袱,在焦灼地等待着他的儿子。
“大大,你来了!”我急切地叫着从小习惯的称呼,去搀扶我的父亲。
白发苍苍的头从车窗边转了过来,那双棕黑色的眼睛朝我注视了一会儿,父亲才认出我来。在他的心目中,儿子永远是小时候的样子,自从翅膀硬了飞走之后,一年一度、数年一度的探亲已留不下十分确切的印象。而且儿子也在变老,面前的这个戴着眼镜、鬓发斑白的中年人是他的儿子?他得凭着记忆中的印象几经印证才敢确认。
“噢,我知道你一准来接我,就坐在这儿没动窝。包袱忒沉,得等你接啊!”父亲的脸上漾出笑意。刮得干干净净的脸一笑,两边的皱褶拉成好几条深深的沟纹。
“包袱?你带这么沉的包袱做啥?”我提了提他身边的包袱,埋怨地问。
“穷家难舍,我都搬来了。”
“那房子呢?”
“屋,扒了。树,刨了。连床,都卖了。你寄的盘缠没动,我还能给你添点儿过日子的钱呢,这回来了,就不走了!”
父亲一一历数着他的行李,告诉我哪件里边是什么。除了他自己的四季衣服,还有用了多年的被褥,几件舍不得丢的小玩意儿,还有一口袋绿豆,一口袋芝麻,一罐香油和一包脆枣,那是我家的枣树最后一次收获。
我只好雇了一辆三轮车,用超过这些包袱价值的车钱把父亲的家产运回了我在北京的家。父亲见了他日夜惦念的孙女、孙儿,用哆哆嗦嗦的手抓了脆枣给他们吃,眼里涌出了两行老泪:“吃吧,咱家的水土好,这枣儿甜。吃吧,就这一回了,往后就吃不着了!”
夜里,在一间半斗室里住下了老老少少五口人。床铺不够,就搭行军床吧,就是搭地铺也不回家了。
父亲住下来了。他要在生命临近终点的时候住在儿孙身边,过一过大都市的生活。天安门、故宫、颐和园、长城,都逛一逛。历史博物馆也得看一看。闲着没事到公园里打打太极拳,玩玩鸟儿,像那些退休的干部、工人们似的。儿子的书橱里有很多闲书,他可以好好地看一看,甚至还可以写写字。年轻的时候他替人家写了不知多少春联,而最得意的一副是贴在自家门上的:“读书写字真乐事,种竹栽花最怡情”。一个农户贴这样的春联?那是他的志趣,他的爱好,他的精神支柱,他一辈子没有实现的愿望。
他在北京过得很愉快,从颐和园的排云殿,他沿着山路走走停停,一直登上佛香阁。从万寿山的制高点上俯瞰整个北京,他陶醉了,随口吟出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杜甫的名句。在天坛的回音壁前,他像孩子似的把耳朵贴在那弧形的墙上,谛听我在另一端亲切的呼唤:“大大,大大!”这最悦耳的乡音,使他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在故宫,他久久地注视着“金銮殿”上的皇帝宝座,仿佛在心中丈量从农民到帝王之间的十万八千里距离,而这距离,刹那间缩得近在咫尺。他也许在回味陈胜在当农民时说的一句话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不是在用知识分子的心理溢美自己的父亲,不,父亲是博学的,他甚至在凭吊历史古迹的时候,好几次指出了写在牌子上的说明词中的谬误之处。我告诉他:等我手头的这部电影完成之后一定拍一部历史片,父亲说的这些说不定能用上。
父亲在北京的日子是美好的,却又是短暂的。西山的枫叶红了的时候,父亲的“痨病”犯了。他无力地躺在床上,半闭着眼睛,嗓子里呼着微弱的气息,带着咝咝的痰音。瘦骨嶙峋的胸腔艰难地起伏着,那里有许多话要说,却说不出。
担架!救护车!输氧!紧急抢救!我被吓蒙了,惟恐死神夺去父亲的生命。
父亲又活过来了。他在阴曹地府的门口转了一遭重回人间之后已不再留恋北京,而急于回去,回家去。也许他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了,要把遗骨埋在故乡的祖坟上。也许,是地下的母亲在冥冥之中召唤他吧?
北京的冬天天气奇冷,我的心也像冰冻的土地一样板结,没有什么可以使它融化了。带上必备的药品和须臾不敢离开的氧气袋,在万木萧疏的季节,我把苟延残喘的父亲送回了家。不,已经无家可归了,是送到姐姐家,然后,只身返京。“对望无言惟有泪,几番徘徊意踟蹰!”父亲后来在信中这样回忆我们的离别。我不能留在他身边照料他,“等”他死,我还有工作,还有事业,还得走,只有把父亲交给姐姐了。说不定哪一天,父亲会突然死在姐姐家里,连通知我回去都来不及。我的心缩成一团,有什么办法?一切都拜托姐姐吧。她,曾经将阳关大道让给我,自己跨上了独木小桥。而这一次,我却把重担都“让”给她了。心债,我的心上,欠了姐姐多少债啊!
我终于挨到了下午一点,登上了从县城往西开的长途汽车。不,路不长,只有二十多里,我过去背着胡萝卜徒步要走两个小时,现在,汽车只要三十分钟。可这三十分钟我却觉得长似一年。“父病危,速回”!每一分,一秒,我都在赶,在抢,谁知道父亲是不是还活着?也许,姐姐为了不使我过度伤心才把死讯说成病讯?也许,姐姐怕我不回去摔“老盆”才这样把我“骗”回去?哪儿能呢?我岂有不回之理!哪怕父亲还剩下最后一口气,我也要赶回去见他一面,哪怕父亲已经闭眼,我也要按传统的仪式披麻戴孝,摔“老盆”,把父亲的灵柩送进祖坟,与母亲的遗骨合葬。我要在坟前做双倍的忏悔!不,我相信父亲不会死,他已经奇迹般地在姐姐家又活了三年,前不久,还亲笔给我写来了长篇书信。不会死,他一定还活着,在等着我——他惟一的、最爱的儿子。
汽车到站,我又上了乡间土路。从这里到姐姐家还有五六里路,我踏着雨后的泥泞,沿着当年汉高祖起兵斩蛇的“白帝河”,没命地跑,奔向那个在地图上找不到、在我心中却永远抹不掉的小村庄。
走进村子,我的心咚咚地狂跳,我担心会听见哭丧声。没有,村子里静静的,大人都出去干活了,只有几个小孩在墙边路口上玩。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一步一步走近姐姐家的大门。到了门口,我几乎要窒息了,好像预感到姐姐正在里边抚着父亲的尸体痛哭。啊,生离死别,我在艺术创作中极为陶醉的生离死别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了。在电影中,我总不让任何一个角色痛痛快快地死,不让他的亲人在死前得到“大团圆”的结局,想方设法折磨观众的心,巴不得让他们的眼泪流成河。现在,在一幕话剧中我成了剧中人,才知道自己曾是那么残酷!
院子里没有哭声,一点声音也没有。大门口也没有贴那种×形的草纸,丝毫也没有出殡的迹象。父亲真的还活着吗?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像跨进鬼门关似的快步走了进去。父亲,我来了!
四
走进卧室,我竟然没有看到父亲。姐姐家的两间东屋的隔断土墙上挖了个下方上圆的小门,套间里惟一的小窗上蒙着旧塑料布,屋里一片昏黄幽暗。两张床靠墙摆成“丁”字形,占据了房间的大半。临窗的床上堆着黑乎乎的被褥和棉衣。父亲,我的父亲在哪里?
姐姐一家人跟着我走进来。
“外爷爷在这儿!”我的外甥女指着临窗的床上对我说。
啊,我这才看清了,父亲原来竟围坐在那堆起的被子、棉袄中间!他佝偻着腰坐在床上,头无力地耷拉在怀里抱着的氧气袋上,一动不动。猛然间,我竟然不敢相信那是一个活人!
我扑在床上,抓着父亲的手:“大大,大大,我回来了!”
父亲仍然一动不动,任我摸着那双干得起皱的手,对我的呼唤也毫无反应。不,他听见了,只是没有力气做出反应。一顶旧绒线帽遮住了他满头的白发和宽阔的前额。背着西窗的微弱光线,他的脸上一片昏暗,眼睛无力地半闭着,上唇和下颚都长满了杂草似的胡须。他轻轻地喘着气,夹杂着咝咝的痰音。父亲从来不是这个样子。他不喜欢留胡子,不愿意显出老相,总是把脸刮得千干净净。他在农民中长期保持着与众不同的卫生习惯,刷牙、漱口、洗澡,从不马虎。而如今,他连这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仅靠氧气袋维持生命的残躯,一动不动地佝偻在床上,像是只等我回来做永久的告别。
“这回犯病犯得怪厉害,还怕等不到你回来哩!”姐姐对我说,“吊针打了三天三夜啦!”
“三天三夜?”我看着一动不动地佝偻着的父亲,“一直就是这个姿势吗?”
“三年都是这样!他不能倒下睡,倒下就憋得慌,三年就这样坐着,腿上都磨出膙子啦!一天天地受罪!”姐姐说着,抬起衣袖擦泪。
我的心痛苦地战栗。三年,父亲竟是这样度过的?为什么每次写信都没告诉我?我自以为尽量地寄钱可以减轻姐姐的负担,可以减轻父亲的病痛,可是这三年的僵坐,我怎么代替啊?我自以为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父亲,用夜以继日的工作来压制自己的怀念之情,可我毕竟每天从半夜到凌晨还有一夕安眠啊!而父亲,却连片刻的平卧歇息也没有,就这样似醒似睡、半死不活地坐了三年!为什么父亲不让我在梦中看见他这备受煎熬的身影?他的信,那一封封写得很长、字迹又很工整的信,竟是伏在膝盖上写的,字里行间向我报着平安!
“咱把大大送医院吧?”我对姐姐说,“住院治疗,不惜一切代价,我带着钱呢,带了五百块!”
姐姐擦着泪说:“多少钱也没有用了,他不能动,几十里路送医院能把他颠打坏喽!还不抵在家,俺啥工夫都不缺,医生天天上家来打针、给药,我白天黑夜守着他,端屎端尿,医院里能行?”
姐姐说得对,我不忍心再让父亲受颠簸了,“就把钱留在家里吧,凡是能买到的东西,凡是咱大大想吃的东西,都给他办到!可惜我来得太急,啥吃的都没带!”
“不缺,啥都不缺,”姐姐说,“他的胃弱,也不能吃旁的啥,就是吃稀的,鸡蛋膏子,蜂糕茶。怕大便干,还得常喝蜜。”
父亲床前的草囤子上盖着块木板,权当桌子。上面摆着点心盒子、蜂蜜瓶子……虽然上面落满了灰尘,可在我们家乡没有人把灰尘当成什么有碍卫生的东西,吹一吹就行了。我看着这一切,揪心似的疼痛。如果父亲住在我那里,总比这里强得多啊!可是他现在已经不能经受千余里的汽车、火车了。何况我那里有天天到家里来看病的医生吗?有整日整夜在床前值班守候的人吗?没有。这里是父亲惟一的安身之处了。
“俺这给他生了个炉子,他这屋最暖和了!”姐姐说。语气里有尽孝的自慰,还有一些自豪。
的确,我们家乡在冬季从没有生炉子取暖的习惯,家家都是屋里屋外一样冷,充其量在来客人时才抓把柴火烤烤。现在父亲的床前生着一只烧蜂窝煤的铁炉,大概是全村最优越的了。那炉子还兼做炊具,无盖,无烟筒。
我又不安了:“别中了煤气。”
“不要紧,门跟窗户都不严,中不了煤气。”姐姐说。
可不是嘛,我们家乡的房子都是那种老式的双扇门,关起来也露着好大的缝。门楣上还有一块空当,是留给燕子飞来飞去的“燕路”。窗户不安玻璃,也不糊纸。只有父亲的这扇窗口蒙上块塑料布,被西风吹得呼扇呼扇的。唉,既要取暖,又要透风,这糊涂的生活哲学!
父亲醒来了。不,他根本就不是在睡,他一直在倾听我们说话,只是没有力气插嘴。此刻他蓄足了力气,终于张开了嘴要说话了。我期待地望着他,他的眼睛却照样地半闭着,并不像凝视着归来游子的样子,只是嘴唇在动:“这一崩儿(一段时间)……没见你的信,小报上说,你在拍刘邦的电影?完了没?我还……能捞着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