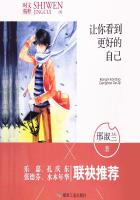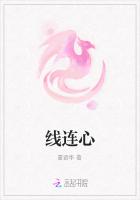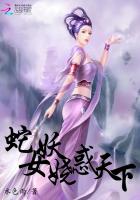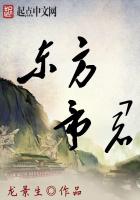说话到这里,有必要声明:我决没有发动中国的乞丐化妆上街表演“活雕塑”的意思。试想,如果北京的马路突然冒出一些横眉怒目的“八大金刚”或是泥头泥脸的“收租院”来,也够大伙儿受的!我只是想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明史,是由它的全体成员一代又一代共同写成的,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在“雕塑”着国家和民族的形象,佛罗伦萨街头的“雅丐”便是一例。
(发表于1999年2月1日《北京晚报》)
碑
离开莫斯科之前,去看了新圣女公墓。原定的访问日程中本来并没有这个项目,是受了翻译小刘的鼓动才临时增加的。在瞻仰列宁墓时,他对我说,斯大林的遗体本来也保存在这里,苏共二十大之后,被赫鲁晓夫搬出去了,埋在克里姆林宫的红墙下。
“我知道,在国内看到过这些报道。”我说。
“其实,能埋在克里姆林宫的红墙下也已经是很高的‘规格’了,只有‘领袖’级的人物才能获得这份殊荣。”他又说,“但是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也是当过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的人,但死后并没有埋在这里,你知道他埋在哪儿了?”
“他埋在哪儿,我怎么会知道?”我毫不掩饰对赫鲁晓夫的漠然。
“埋在新圣女公墓。”小刘说,“墓碑是抽象派雕塑家涅伊兹维斯内设计的。你知道吗?赫鲁晓夫当权的时候,并不喜欢这个人的作品,曾经当众羞辱过他:你画的是什么玩艺儿?驴尾巴蘸上颜料胡乱甩几下,都比你画得好!”
“那为什么还请他来为赫鲁晓夫设计墓碑?是后人恶作剧吧?”
“不,这恰恰是赫鲁晓夫本人的遗愿。”
“这更不可思议了,为什么?”
“谁知道?也许是想修补人缘儿吧?咳,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我不禁对赫鲁晓夫产生了“兴趣”。谁能想到,当年不可一世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失势之后如此凄凄惶惶,竟然向一位曾被他不屑一顾的艺术家低头服输?有意思!
“怎么样?我陪您去看看?”小刘向我建议。
我立即表示同意。第二天,趁代表团自由活动的时候,我们雇了辆出租车,冒着蒙蒙细雨,直奔新圣女公墓。
原以为公墓一定在郊外,其实不然,新圣女公墓就座落在市区的一条街道上,外表并不引人注意,里面倒很宽敞,形形色色的坟墓、墓碑和雕像参差错落,像一座露天的雕塑博物馆。小刘也是第一次来这里,他对我讲的那一大套都是听来的,正像北京的许多名胜,北京人往往是因为陪外地朋友参观才第一次领略。公墓里的游人很少,我们踏着落叶,寻寻觅觅,从一座座坟墓旁向前走去,秋风拂过头顶的树枝,瑟瑟作响,令人心头掠过一阵悲凉。
旁边走过一位老太太,六七十岁的样子,从朴素的服装看来像是一位农妇,白发苍苍,步履蹒跚,手里捧着一束鲜花。小刘连忙上前打个问讯:“大婶儿,请问,赫鲁晓夫的墓在哪儿?”
“赫鲁晓夫?”老太太站住了,吃惊地望着我们,好像是怀疑自己听错了,或许是有意装傻充愣,“哪个赫鲁晓夫?”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小刘说。
“噢,是他呀,”老太太的眼神里流露出对死者的不敬,连带着对我们也没有好脸色,“你们……是去给他上坟?”
“不,不,我们是外国游客,只是来‘看看’。”我连忙解释,生怕因为赫鲁晓夫而得罪了这位“苏联人民”。
“看看?赫鲁晓夫的墓有什么好看的?”老太太不以为然,“斯大林在世的时候,他说斯大林就像他的父亲;斯大林一死,他马上翻脸,把斯大林说得一无是处,这样翻云覆雨的小人,不值得纪念!”
老太太说到这里,转过脸去,撇下我们,径自去了。
我和小刘不禁感叹:赫鲁晓夫在他的国家竟是这样不得人心!一路闲聊着往前走,忽然发现赫鲁晓夫的墓就在近旁,那墓碑十分惹眼,而且上面还有赫鲁晓夫的头像,很容易辨认,我这个年龄的人对他那张肥脸是很熟悉的。赫鲁晓夫留给我们的印象太深了,他专横、霸道,粗暴干涉兄弟党和国家的内政,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和中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协议,使“三年自然灾害”雪上加霜;他野蛮、粗鲁、随心所欲,信口开河,在美国当众脱下皮鞋敲桌子……劣迹斑斑,不胜枚举。当年“反修”热潮中,中共中央“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战斗檄文就是针对他的,毛主席的诗句“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也是针对他的。在中国,“赫鲁晓夫”这四个字就是野心家、阴谋家、修正主义的代名词,是十恶不赦、万劫不复的魔鬼。从赫鲁晓夫时代到现在,四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反修”斗争已成为历史,连苏联都不复存在,那么,今天又该怎样来评价赫鲁晓夫呢?也许,如果没有赫鲁晓夫的折腾,极“左”、专制的斯大林时代不会那么早结束;庞大的苏联也不至于那么快衰败、消亡。
有意思的是他的墓碑:深灰色的基座上,黑白两色的大理石相互交错,相互扭结,两者的缝隙中嵌着赫鲁晓夫的头像。这就是涅伊兹维斯内极具独创性的杰作,黑白两色的墓碑,史无前例,举世无双。但他为什么要这么设计?这黑白两色是什么意思?小刘说:“可能是寓意赫鲁晓夫功过兼具、毁誉参半。”也许是吧?可我听着又觉得这种说法更像习惯于“三七开”、“四六开”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谁知道墓碑的设计者涅伊兹维斯内是不是这么想的呢?如果真是这样,我倒要佩服这位艺术家的大度,他并没有因为旧怨而报复死者,而能够以平静的心态,力求客观地认识墓主的一生,不管“半黑半白”的评价是否准确,他设计墓碑的创作态度是严肃的,墓碑上的赫鲁晓夫头像以写实手法雕成,而没有丝毫丑化。
离开赫鲁晓夫墓,我们又意外地发现了众多“熟人”的墓:作家果戈里?法捷耶夫、奥斯特洛夫斯基,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以及青年英雄卓娅和舒拉都埋葬在这里,简直是明星大聚会,新圣女公墓强大的阵容和深厚的底气着实令人惊叹!这激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一一拍照留念,并且继续寻找下去,看看还有什么人是我们熟悉的。这时,竟又碰到了那位农妇似的老太太,她正半蹲半坐在一座墓前,低头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原来捧在手里的鲜花已经放在墓碑前。这墓碑十分简朴,也没有墓主的雕像,不像那些名人墓那么醒目。
我问小刘:“这是什么人的墓?”
小刘看了看碑上的字,说:“乌兰诺娃。”
“啊?”我吃了一惊,“乌兰诺娃!”
老太太被惊动了,抬起头来,满脸泪痕。她认出了我们,好像很为墓主而骄傲,问道:“听说过这个名字吗?知道她是谁吗?”
“当然知道了,”我说,“她是苏联最优秀的舞蹈艺术家,在全世界都非常有名……”
“是的,”她点点头,“乌兰诺娃为我们的国家争了光!”
“她曾经访问过中国,只可惜我没有亲眼看过她的演出!”
“我看过,看过许多次!”老太太说,那神情极其自豪。
“您……是她的什么人?”
“我?我是她的观众,她的崇拜者!在一次演出之后,她还亲笔给我签过名呢!当然,她不一定记得我,因为崇拜她的人太多了!”
这个回答实在出乎我的意料,原来她既不是乌兰诺娃的亲戚也不是朋友,而只是一个“老追星族”!
老太太告诉我,她从小就喜欢芭蕾,梦想着能成为像乌兰诺娃那样的艺术家,可是天不遂人愿,她后来的人生道路与舞蹈完全无缘,但是她丢不下那刻骨铭心的爱好,几十年来一直崇拜着乌兰诺娃,直到她去世,仍然痴情不改。她不是本地人,家住在二百多公里以外的一个小镇,到莫斯科来一趟要坐好几个小时的火车,昨天进了城天就已经黑了,她只好在火车站坐了一夜,天一亮就赶到这儿来了。
“这是您进城的惟一目的吗?”我问,“是不是还有别的事要办?”
“没有,”老太太说,“就是特地来给她上坟。每年我都至少要来一次的,给她献一束花,对她说一说心里话,就好像又看见了她在舞台上翩翩起舞,那是一种崇高的艺术享受啊!”
啊,不知长眠地下的乌兰诺娃听到了没有?如果她九泉有知,应该为自己仍然活在观众的心里而欣慰,这也正是艺术家的生命价值所在!中国的史学泰斗司马迁说过:“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惟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是的,历史无情,生前富贵尊荣,死后未必不朽,长留天地之间的惟有“倜傥非常之人”,那碑,立在人的心中。
小刘,给我们拍张照吧!我和老太太并肩而立,身旁是乌兰诺娃那近乎简陋的墓碑。
从新圣女公墓归来,赋绝句一首:
秋风黄叶雨霏霏,哭倒坟前道是谁?
莫谓舞魂从此逝,巍然不朽在心碑。
(发表于2004年第4期《文学风》)
海空星河
天边褪去了最后一抹晚霞,夜幕笼罩了大海,一层层白浪缓缓地漫上沙滩,再缓缓地回落,是那么悠闲、从容。这是退潮的浪,奔腾了一天的大海也需要歇一歇了,像睡眠中轻柔的呼吸。有意思的是,退潮并不是海水倒流,而是随着浪涌的一起一落,水位渐渐降低,那湿漉漉的沙滩便越展越宽了。
我和两三个当地友人来到海边,他们说,若不是为了陪我这位远方来客,倒还没有机会乘夜观海,今天也是第一次。我感慨,海边的人真是太“奢侈”了,白白浪费了多少良宵美景!海边大排档的小伙计为我们在沙滩上置一张方桌,几把座椅,泡一壶铁观音,于是宾主落座,把盏临风,对海品茗,踏浪听涛,好不快哉!千里之外的都市喧嚣,余威未尽的秋后残暑,都作云烟散去,一时不知身在何处,今夕何夕!
旁边有渔民在拉夜网,听他们说,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一。我这才意识到,怪不得看不见月亮。天已经黑透,浓黑中泛着微蓝,明净澄澈,闪烁着无数星斗,与远处的点点渔火交相辉映。这般满天星斗的夜色,在北京是看不到的,大概是因为北京有太多的“明星”吧?我和友人仰望星空,竞相指点,头顶一抹轻纱纵贯苍穹,那是银河;右岸一颗大星,闪着黄钻石般耀眼的光,当是织女;而左岸并排三颗稍暗的小星,一定是牛郎和他肩挑的一双儿女了。奇怪不奇怪?我们中国人即便走到天涯海角,看到星星便会想起那个牵动了一代又一代人情感的神话故事:“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濯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此刻,天上的牛郎织女正在隔水相望,欲语不得,要等到鹊桥飞架,他们夫妻母子团聚,还有整整七天。每年的那一天,善良的中国人都要向他们表示庆祝,并且也期望借此为自己带来吉祥。《帝京岁时记胜》“七夕”条云:“街市卖巧果,人家设宴,儿女对银河拜,咸为乞巧。”在我的儿时,北京的这些风俗已经大大淡化,种种仪式都没有了,但“七夕”并没有消失,它仍然活在人们的心里。记得那时,我总要和年龄相仿的几个女孩儿一起到院子里的葡萄架下谛听牛郎织女的夜半私语。那是极为认真、极为虔诚的潜心静听,“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听他们都说些什么?一阵寂静之后,小伙伴儿们开始转述各自所听到的内容,这个说,牛郎肩挑着两个孩子,一路上又累又饿。见到织女就说:“快给我两个油饼儿吃吧!”那个说,她听到织女的女儿在诉苦:“妈呀,爸爸这个人真不怎么样,对我们一点儿都不好,你跟他离婚算啦!”现在想想,这些天真的话语都是孩子们的心声,是他们自己生活的折射,可是在当时,却都信誓旦旦地宣称这是亲耳“听”到的!我已经记不得自己曾经听到过什么,也记不得往年“七夕”是否看见过牵牛星和织女星在银河相会,倒是在事隔几十年之后,当我如此清晰地注视着海空星河之际,却更加关注那个四口之家的命运了。你看你看,现在牛郎和织女还离得这么远,七天之内真的能够走完这段路程吗?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决心要亲自看个究竟。
夜深人散。次日晚餐后,还是在那个时间,还是那几位朋友,又相约来到海边,吸引我们的已不仅是品茗听涛,更重要的一项内容则是夜观天象了。我们仔细观察,发现银河的走向与昨晚稍有不同,但牛郎和织女的位置却看不出什么变化。等到深夜,依然如故,只好再待来日。第三夜,西南天际现出一弯新月,浅浅的鹅黄,淡淡的光亮,像一只金钩,给海滩又增添了一层情趣。曹操诗云“月明星稀”,那大约是指浑圆的满月,而我们此时所见到的新月还没有足够的光辉照亮海空,天上的银河和密密麻麻的星斗仍然十分清晰。但遗憾的是,我们所关心的牛郎织女却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近,这是怎么回事呢?第四夜,第五夜,新月悄悄地丰满起来,到了第六夜,已经接近半圆,清晰的弓,模糊的弦,像一片飘浮在空中的羽毛。然而,牛郎织女的状况还是没有什么改观,仍然保持着相当的距离,“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要知道,明天就是他们鹊桥相会的日子,现在只剩下短短的二十四小时了,还来得及吗?海边休闲变成了焦急的等待,好像卫星发射进入倒计时。尽管我们这些中年人谁也不可能将神话故事信以为真,凭着有限的天文知识也知道牵牛星和织女星与地球之间的距离是不相等的,也就是说,他们永远也不可能碰面,地球人所看到的“牛女相会”只不过是个虚假的表象,犹如电影上两个镜头的叠印,但人到什么时候也不可能将童心完全泯灭,比如现在,我们都像孩子似的痴迷着星空,盼望那“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河迢迢暗渡”的动人时刻早早到来。当然,这只有等到明天了。
终于等到了第七夜,“七夕”的正日子。我们早已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提前吃过晚餐,黄昏时分便赶到海边,坐等天黑。真是不巧,今天是个多云天气,薄云至晚未散,天朦胧,月朦胧,银河也朦胧,仿佛洪水暴发,泛滥得漫无边际,织女在哪里?牛郎和他的两个孩子在哪里?“一片汪洋都不见”了。这就是我们苦苦等待七个夜晚的答案吗?这就是牛郎织女故事的结局吗?真令人太遗憾了。众人默然良久,不知该如何收场。座中一位忽然说“那云彩就是鹊桥啊,他们已经在相会了!今天喜鹊来得特别多,把银河整个都遮住了!”亏得这个聪明人,用“模糊”手段解决了这个难题。
夜空茫茫,星月朦胧。寂静之中,大海从容不迫,推过来一层层白浪,吞吐着沙滩。这是退潮的浪。等退到极限,就开始涨潮,奔腾汹涌,咆哮冲天。这便是大海,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不知明年“七夕”,我还会来海边吗?
(发表于2001年9月23日《北京晚报》)
书到用时
小时候,家里常挂一副对联:“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几十年来,深感其是。中国人讲究“经世致用”,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用。然而,读了半辈子的书,却仍然不够用,写文章遇到捉摸不定的事,还要查书,不敢贸然下笔。比如,我在写《穆斯林的葬礼》时遇到的一个问题:北京改名叫北平是哪一年?为了这个年份,我就查了几十本书,才得以落实,是一九二八年。再比如,写《补天裂》时遇到的一个问题:晚清大内总管是“李莲英”还是“李连英”?为了一个草字头,又翻遍故纸堆,一直查到了李连英的墓碑碑文,终于确信没有这个草字头。这还只是最小的例子。海底捞针,苦则苦矣,但此中欣慰,局外人也难以体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