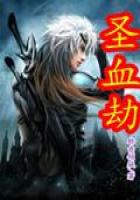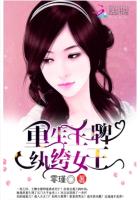问题的提出与研究设想
以往的研究者对于词汇加工的心理过程以及内在机制还存在不少争议,其问题的焦点集中在词汇认知是有语音信息的参与,还是直接由字形通路完成。汉语由于不像拼音文字那样在正字法单元(笔画)与语音单元(音素)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较早的研究采用识记(Tzengetal.,1977)或句子核证(Treimanetal.,1981)等实验任务没有发现语音在汉语阅读中的作用。然而近几年的研究采用能够即时考察词汇加工的实验范式(如掩蔽实验范式)发现汉语的词汇加工中语音信息的激活也是自动发生的,没有受到被试者意识的控制(如张武田等,1993;Tanetal.,1996;Perfetti&Zhang,1995)。
但是语音的自动激活与语义通达中语音通路作为中介通路是两个相关但又截然不同的问题,即使语音激活在词汇识别过程中发生,正字法信息也可能会在语义信息之前被激活并且可能通达了语义,语音的作用可能只是被用来在短时记忆中储存信息(Baddeley,1979;Tzengetal.,1977;Xu,1991),或者作为深层信息表征被转换成外显的发音行为。
与英文研究相比较,汉语相关探讨还不是很多,所达到的深度还远远不够。少数的研究(e.g.Lecketal.,1995;Xuetal.,1999)或者采用需要语义参与的实验任务直接考察语音编码在词义通达中的作用,或者通过研究形、音、义三要素的加工时间进程间接地考察语义加工中语音作用的问题,还有的从生理心理学的角度进行探讨。研究中得到的结果是不一致的,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研究者所采用的实验范式、材料等的不同而造成的;另一方面也表明汉语词汇形、音、义的加工是复杂的,词汇认知以及语义的激活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
对汉语词汇认知的心理过程,已有的研究基本上得出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例如,Perfetti&Tan,1998)从人类语言特点与认知加工的角度出发,提出语音加工是人类语言加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语音与书写系统的关系是后者依赖于前者,而非相反的情形,因此不论在英语还是汉语的词汇认知中,语音都应该起重要的作用,而不同文字系统的特点会对其具体的作用机制产生一些细微的影响。另一种观点(例如,周晓林,1997)则从对不同文字特点的分析出发,认为汉语与拼音文字相比正字法与语音之间关系的任意性程度更大一些,形似的字可能发音不同而形异的字可能会有相同的发音。另一方面,字形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完全任意的,形旁可以指示整字所表达意义的语义类别(例如“打”的形旁表示与“手”有关),因此在汉字的加工中字形比语音似乎发挥更大的作用。
如果语音是汉语词汇加工中重要的中介通路,语义主要是由语音激活的,那么应该在各种实验中发现稳定的“语音效应”,然而从前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对语音在语义加工中作用的研究从上世纪70年代起至今并没有得出一个较为一致的结论,研究结果比较混乱甚至相互矛盾,这说明汉语词汇的识别不一定只依赖于语音通路,用单一的语音加工机制无法说明汉语词汇加工的实际情况。
总体来说,在词汇加工中是否存在语音编码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在于它的加工速度(Patterson&Coltheart,1987)。大量对拼音文字的研究发现语音在语义激活中起重要的作用(Frost1998;Lukatelaetal.,1980;Turveyetal.,1984;VanOrdenetal.,1987),研究者们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拼音文字中正字法与语音之间有规则的对应关系而正字法与语义之间的关系是任意性的,由于不同领域之间的转换受制于它们之间匹配的规律性(Patterson&Coltheart,1987;VanOrdenetal.,1990;Plautetal.,1996),语音的激活速度就比较快,因而会对语义的通达产生重要作用。一个极端的例子如在塞语(Serbo—Croatian)中形与音的匹配基本一致(one—letter—for—one—phoneme),研究发现塞语的词汇通达以语音为“中介”,并且这种“中介效应”非常稳定(Lukatelaetal.,1980;Katz&Feldman,1981;Feldman&Turvey,1983;Frost,1994)。
在汉语中,形与音以及形与义的关系似乎都具有较大的任意性。正字法单元(笔画)与语音单元(音素)之间没有非常规律的对应关系,并且形似的字可能发音不同(如请—倩),形异的字可能会有相同的发音(如流—留)。另外虽然形旁可以指示整字意义的语义类属,但是却不能明确地表明整字的含义,再加上随着文字的演变有些形旁所指的意义已经与整字的意义发生较大的偏离(例如肤)。因此总体而言,汉字的形、音、义之间的联系是任意性的,各信息层面之间的转换似乎没有太大的规律可循。既然形、音、义之间的联结任意性较大,那么可以认为这三要素之间的联结强度主要依赖于在学习和使用中的强化程度,熟悉性高的词的三个要素之间的联结要强于熟悉性较低的词。并且从认知经济的角度来看,从形—义比形—音—义的通路效率更高,因此熟悉性较高的词词义的激活主要依赖于字形到语义的直接通路;在熟悉性较低的词的词汇通达中由于由形到义的联结强度变弱,单纯依赖正字法信息无法激活语义表征,并且由于形与音的关系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较之形与义的对应(一对多,一个字形可能对应几个意思)更为稳固(Perfetti&Zhang,1995),这样语音的激活应该快于语义的激活,因此词义的通达应该由音与形的共同作用来完成,语音在词义的加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在汉语中,有一部分汉字的字形与语音之间的对应并不是完全任意的,根据统计(陈原,1990),形声字中大约三分之一的字,其声旁的读音与整字的读音一致。已有的研究(舒华、张厚粲,1987;Seidenberg,1985;Zhou&MarslenWilson,1999b)发现在汉字的加工过程中,声旁被从整字中分离出来并且它的语音信息得到了激活,被激活的语音信息会对整字的加工产生影响:如果声旁的读音与整字的读音一致,就会对整字语音的提取产生促进作用。因此结合以往的研究,本研究认为当声旁读音与整字读音一致的时候,整字的语音激活速度快,会对语义的激活产生较大的影响,不论是在熟悉性较高的词的加工中还是在熟悉性较低的词汇加工中,可能都会有语音信息的参与。
另外由于汉语与拼音文字不同,在拼音文字中用韵律信息(重音)来区分词义的很少,因此在拼音文字的加工中忽略重音信息给词汇的识别带来的影响不会很严重,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可以简化整个的认知加工过程;而汉语中声调与声母、韵母一样都是汉字语音表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声调也有着区分意义的功能。例如如果想要经由语音表征通达到“鲜”的语义表征,仅仅激活了它的音段信息是不够的,因为共享此音段的共有四个字(鲜、咸、显、线),必须要先激活它的声调信息才能够通达到确切的词义。因此结合以往的研究,本研究认为声调在汉语词汇的加工中起了作用,但由于声调属于超音段信息,它的存在依赖于音段信息(韵母元音),再加上声调本身的特性(例如汉语中的四个声调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因此声调的充分加工一般落后于音段信息,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完成。
同时根据平行分布加工理论模型(McClellandetal.,1986),形、音、义三种编码的激活是交互式的,在一种水平上建构一种表征会受到其他两个水平的表征结构的影响,同时也会影响其他两个水平的建构,也就是说在语音表征与字形、语义表征之间应该存在着交互作用。而在汉语的研究中,已有一些研究发现了这种不同信息层面之间加工的交互作用(Lecketal.,1995;Sakumaetal.,1998;Tanetal.,1995,1996;Zhou&MarslenWilson,1998)。Lecketal.(1995)在采用语义分类任务的实验研究中发现当同音词与语义类别词在正字法上相似程度较高的时候,得到了显著的同音干扰效应,而当两者在字形上不相似时,同音干扰效应就小得多,甚至不显著。Tanetal.(1995,1996)发现语义精确程度会影响音、义的加工时间进程。Zhou&MarslenWilson(1998)发现把双字词中的一个字用其同音字替代而形成的同音假词与控制词相比,被试者在词汇判断任务中做出“拒绝”反应的潜伏期更长一些,即同音假词效应,并且同音假词效应与成分字的频率有交互作用,这说明同音假词对原词的语音表征的激活是整词的语音加工与成分字加工的交互作用的结果。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语音在语义加工中的作用可能会受到其他两个表征层面的影响。
对词汇认知的实验研究设计
一实验目的
实际研究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实验假设,语音在汉语熟悉性较低的词汇加工中有一定的作用,在熟悉性较高的词汇加工中没有作用;当形声字中声旁读音与整字读音一致时,整字的语音加工速度快,因此会在语义通达中产生较大的作用;声调信息也参与了词汇的加工过程。
第二部分考察了语音在词义通达中的作用是否受到其他两个要素的影响。实验五采用语音中介语义启动任务,语音中介启动词不仅与语义相关词同音,而且与语义相关词形似。实验假设如果汉语词汇识别中语音加工与字形加工存在交互作用,那么同音并且形似的语音中介词得到的启动效应应该与仅仅同音的语音中介启动效应不同,前者应大于后者。实验六考察了语义类型(语义精确词、语义模糊词)与语音中介启动效应的交互作用。实验假设,由于语义精确词的加工速度快于语义模糊的词,语音在语义精确词通达中所起的作用应小于在语义模糊词通达中所起的作用。第二部分考察了语音在词义通达中的作用是否受到其他两个要素的影响。试验五采用语音中介语义启动任务,语音中介启动词不仅与语义相关词同音,而且与语义相关词形似。试验假设如果汉语词汇识别中语音加工与字形加工存在交互作用,那么同音并且形似的语音中介词得到的启动效应应该与仅仅同音的语音中介启动效应不同,前者应大于后者。试验六考察了语义类型(语义精确词、语义模糊词)与语音中介启动效应的交互作用。试验假设,由于语义精确词的加工速度快于语义模糊的词,语音在语义精确词通达中所起的作用应小于在语义模糊词通达中所起的作用。
二关于SOA的时间设定
实验采用需要语义信息参与的语音中介语义启动实验范式。根据已有的研究(周晓林,1997;Perfetti&Tan,1998;Tan&Perfetti,1997),本研究中将实验中的SOA一般设定为120毫秒。研究假设,如果语音对语义通达产生作用,那么在这个时间点上应该可以发现语音中介语义启动效应。同时为了考察语音中介启动效应随着加工时间的延长所发生的变化,在实验中将SOA延长至400毫秒(Tan&Perfetti,1997在启动词呈现时间为500毫秒时只发现了语义启动效应,而没有语音中介启动效应,本研究所采用时间约与之一致),实验的假设是,随着加工时间的延长,被语音激活的不恰当的词被抑制住了,因此语音中介语义启动效应就会消失,只有语义相关启动效应。
三对汉语声调的实验研究设计
实验还考察了在词汇加工中声调的作用。实验范式为语音中介语义启动任务,语音中介词为与语义相关词音段相同、声调不同的词,SOA分别为120毫秒、400毫秒。实验假设,当语音中介词被呈现时,它的语音表征被激活了并且扩散到其他同音表征上,由于在较短的时间(SOA为120毫秒)上声调信息虽然被激活但是还没有被加工完全,因此它无法对不同声调的语音表征进行抑制,这样语义相关词的语音表征也被激活了,并且影射到其语义表征上面,因而会对目标词的加工产生促进效应。而随着加工时间的延长,不同声调的语音表征也被抑制住了,因此也就无法产生语音中介启动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