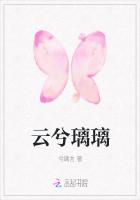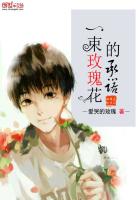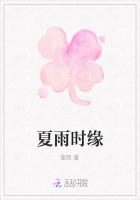按照年代测定,马厂类型文化约相当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也就是传说中的夏代,即自新石器时代向文明国家演化的过程当中,与农耕起源的时代已有相当的距离了。如果说在人们熟悉已久的“男耕女织”模式存在之前还曾有过一个更为古老的“女耕女织”的模式,也许乍听起来有些耸人听闻之嫌。然而,人类学研究表明,施密特、汤姆森等人坚持的女性发明农业说是有足够依据的。最初,妇女发现了育种原理并开始种植的尝试,随着农业收成的优越性和稳定性逐渐被狩猎社会完全认可,这才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男性放弃狩猎而转向农耕。即使在男女共同参加农业生产的社会里,对于妇女发明育种技术从而使耕种成为现实的功绩依然是记忆犹新的。神话与仪式在这里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珞巴族中流行的农耕祭礼便可作为一个实例:
庄稼收完后,举行称为“昂德林”的丰收节。丰收节的时间约二天,全村男女共饮丰收酒,晚上喝酒对歌至通宵。
男女对唱的内容是关于农业的起源及男女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如名叫“虾依·亚李波”的歌中唱道:“我们男子不帮忙开天辟地,你们女子到哪里去找地种庄稼!”“我们女子不育成种子,学会种庄稼,你们男子怎么能喝上这样甜蜜的美酒?没有花蜜蜂蜜自然不会甜,没有我们女子育成种子,人类也不会有像今天这样多的粮食吃!”
在这首词义分明的农耕仪式歌中,女性尚能以充分的自信和自豪向男人们夸耀她们发明育种技术,开创农业新纪元的伟大业绩。
发现于古埃及,属于公元前四千年代。双臂上扬的女性,有人说表现了繁殖崇拜仪式中的祭祀舞蹈,也有人说是表示“伟大”的身姿符号,可以跟中国内蒙古、云南沧源、广西左江等地发现的表现祭祀性乐舞的岩画相参照。耕女织时代的遥遥反响。如人类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农业的发明是妇女的功绩,不仅因为妇女是主要的采集者,其后又成为初期农业的发明者;还因为初期农业主要是由妇女们承担和领导的。北美印第安人如易洛魁人、祖尼人、亥达沙人,非洲东南部的许多部落,以及新几内亚的巴拿罗人等,在农业活动上就是以妇女为中心的。由妇女们选出一个年长而精力充沛的管理人领导农耕工作,而这个管理人还可以选择一两个人做自己的助手。随着锄耕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发展到犁耕农业阶段,男子就成为农业方面的主要劳动者了。”从以上材料中可以推测出,在妇女发明农耕技术之后,男子取代妇女成为农业的主要劳力之前,一定存在过一个主要由女性从事农耕生产的历史阶段。当时意识形态的核心观念在于将女性的生育能力同大地的生产能力相互认同,使大母神信仰向地母信仰方向演进。
大母神在农耕文化中同土地的生养能力相认同的另一结果是,农作物乃至整个植物世界的周期性荣与枯的循环被看做是地母特别掌握的死亡与再生功能的体现。于是,原来只作为生育之象征的母神神格现在发展为兼管死亡、复活的命运之神、月神和阴间主宰神。这样一来,从单一的生命赋予者,到“生——死——再生”这样一种生命循环过程的主宰者,大母神观念的发展同源于日、月循环运行的神秘的“道”的观念也就相距不远、日趋融合了。杜而未先生坚持认为老子所说之“道”本为月神,虽不免以偏盖全之嫌,但毕竟还是包含着某些真实的信息的。
由儒家礼法制度所代表的典型的父权制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性别偏见,在其统治下,中国远古的母系社会的宗教与神话必不可免地受到空前的毁灭性打击而难以完整地留传后世。只有在作为儒家的男性中心文化之对立面的道家传统中,特别是在道家思想的早期代表老子的文本中,还多少保留着一些使我们可以窥视被父权文化所吞没的远古女神宗教的蛛丝马迹的原型与象征。若能结合近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关于女神宗教的某些新发现,对于这个问题的宏观理解似可更深一步,获得某些实证性的证据。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东北红山文化遗存不断传来关于女性裸像发现的消息,这足以使西方1.所谓“岛屿母神”像,石制,发现于斯巴达附近,约公元前15世纪。2.发现于巴基斯坦俾路支史前文化遗址。
可能在祭祀和巫术仪式里使用。这一类女性陶像往往都表现丰殖与多产。岛屿女神像更特别突出腹部,表现孕育,祈求蓄庶,可与中国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妇女造像比较。考古学界对史前维纳斯分布的有限理论大为改观。也给中国史前女神宗教的考索提供了有利的依据。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祭祀遗址出土的女神像和辽宁省牛河梁“女神庙”与积石家群的发现,都以五千年前的实物证据无可辩驳地证实了我国史前新石器时代曾盛行过对女性神灵的崇拜和祭祀礼仪。这就为了解《老子》书中有关母神原型的种种表述提供了现实基础。看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类在石器时代信奉过以女神为崇拜对象的宗教,这一点是不约而同的。只是由于父权制文明的确立才最终导致了最高神性别的由女变男。
红山文化中首次发现的中国史前维纳斯已经引起各方面学者的注意。考古学界倾向于把女性陶像认定为农神和地母神。俞伟超先生认为:“在母权制的农业部落中,把妇女像作为崇拜的神像,还可能具有另一种意义,即作为农神的象征。美洲的一些印第安人,当年曾把对生活有重要关系的三种农作物——玉米、豆子和南瓜,作为农神,祭祀时则以妇女代表之。从东山嘴陶塑像的形态看,能够直接表现出的含义是生育神,但联系到红山文化的生产状况看,也许是农神,还可能兼有两种意义。……长方形的祭坛,应是祭祀地母的场所。在原始的农业部落中,人们依靠农业来维持生活,因为见到农作物是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便以为农业收成的好坏,在于土地神的赐予,于是,普遍信仰土地神。”
20世纪90年代,一个更为惊人的发现来自黄河流域的腹地陕西扶风县,考古工作者在那里的新石器遗址中发掘出一尊高7厘米的裸体女像,其造型特征竟与西欧史前维纳斯像如出一辙。由此可知,史前女神宗教的存在绝不限于一时一地,而是具有跨文化、跨种族的普遍性的。可以确信在中国其他地区的史前文化遗存中将还会有更多的史前母神像陆续问世。
通过上述背景分析,本节开篇时所提出的问题似乎可以有一个合理的解答了。老庄生于父权制文明之世,但是却顽强地坚持为父权制文明的正统意识形态所不容的远古女神宗教的思想遗产。他们让“可以为天下母”的混沌充任宇宙发生神话的主角,这样便有效地排斥了男性中心文化所推崇的男性创世主的观念。他们还竭力地表达这样一种思想:宇宙万物是原始母神“生”的结果,而不是男神凭借其至高无上的意志和权威“造”的结果,这样就把道家理想中的黄金时代落实到“生”之前的孕育状态,而不是“造”以后的伊甸乐园了。从象征意义上看,宇宙创生以前的混沌状态同婴儿诞生以前的母胎状态是可以相互指涉的,所以老子所标榜的“贵食母”与“复归于婴儿”同重返混沌一样,其价值指向是完全一致、互为表里的。诚如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家西蒙娜·德·波伏瓦所说:
母亲即是混沌(chaos)……因为混沌既是一切生命所由出之源,又是一切生命所当归之处;她乃是无(Nothing-ness)。
老子不是也把混沌状态视为“无极”和一切生命之源吗?看来他的婴儿说与混沌说都是以母神为本源的。艾利亚德指出,与复归混沌的神话主题相对应,在原始部落中流行一种叫做“复归子宫”(regressus ad uterum)的启蒙仪式,使成年者通过象征性地回返母体(地母)——即神话意义上的“回归初始”(re-turn to the origin),获得新生的准备条件。不过,这种“回归子宫”所获得的新生同第一次的肉体诞生不同,它侧重于精神、人格方面的“生”,即获得一种为社会群体所认可的新的存在方式,更确切地说,是神话式的再生。
无疑的是,这样一种以回返母腹而获再生条件的原始观念正是史前大母神信仰的重要遗产,它以不同的方式残存下来,曲折地保留在东西方文明传统之中,转化为集体无意识和某些礼仪性的象征行为。瑞士心理学家容格所说的双重母亲的原型在基督教的再生信仰中的表现便是显而易见的例子。
圣子基督本人便是“重生的”,通过在约旦河的洗礼他从水中再生,从精神上复活了。所以,在罗马天主教礼拜仪式上,圣水盆被称为“子宫堂”,而且,正如你们可以在天主教祈祷书中读到的,在复活节前的圣星期六举行的圣水盆祝祷中,它甚至今天仍被这样称呼。
除了基督教的洗礼观念和老子的回归哲学之外,归返母体的原型还突出表现为世俗文学的常见主题。尼采写道:“无生物就是母亲的胸怀。从生活中解脱意味着再度变得真实,意味着臻于完美。谁都应懂得:复归于无情感的尘土是件乐事。”乔叟通过一个不能死去的老人之口说:“日日夜夜,我拿着拐杖,敲着母亲的门说:‘噢,亲爱的母亲,让我进来吧!’”
与西方宗教和文学中的回归母体主题不同的是,中国道家和道教经由老庄对“抱一”理想的阐发,将回归母体的理念发展为闭目塞听式的东方修道实践:谁说那无知无欲无为的混沌状态不是对母腹中胎儿“食母”形态的无意识模仿呢?“玄牝”这一隐喻词汇的运用本身已经足以说明老子对于混沌与子宫之间的象征性认同关系是了然于心的。“玄牝之门”作为“天地之根”,自然隐喻着世界万物的总根源,这同作为创世之前混沌状态的万物总根源在象征的意义上是一致的。
我愚人之心,纯纯。俗人昭昭,我独若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第二十章)
只有基于对混沌天堂信仰的理解,方可洞悉老子倡导的眙儿战略(以母腹之中的“纯”“昏”“闷”状态为特征)同原始启蒙仪式的回归子宫训练之间的一致性。而庄子那种以生为丧、以死为归的超然态度,也只有同母腹即再生之源的信念相联系,才能获得溯本求源的透彻观照。
三、大母神与混沌:老子的性别政治
大母神信仰的衰落是父权制文化确立统治地位以后的必然结果。关于父权制文化如何最终战胜并取代了远古的母系社会,由于没有文字记载,也许人们只能依靠猜测或推论去了解其大概了。在这方面只有神话保留下来一些珍贵的线索。自19世纪瑞士学者巴霍芬首先借助于神话传说的启示创立“母权论”以来,在这个方向上继续进行探索的神话学家代不乏人,借鉴他们的方法和观点,对于理清古代思想史上的一些难解之结是大有益处的。
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所作《神谱》是父权制文化的典型作品,其中全面描述了男神的胜利与确立统治的过程。以宙斯为首的新辈神经过多次较量而战胜了与母系文化相联系的提坦旧神。尽管如此,代表失势的母系文化的地母神及其后继者赫拉依然拥有强大的实力。甚至男性文化的大英雄巨人安泰也只有在同大地母亲相联系时才具有力量,一旦离开地面,他马上就丧失了全部体力。
在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中,男性英雄早已取代大母神成为神话叙述的第一主人公,但大母神并未完全退出神话舞台,她以多少被丑化的方式表现为专横任性的“生物之母”伊什塔尔。在她同男性英雄吉尔伽美什的较量中,虽然表面上看女神屡遭失败,但从最后结局上判断,男性英雄所获不死之草被蛇所窃,实际是被女神所剥夺。这一结局表明已失势的母系文化以收回不死性的方式惩罚与父权文化相认同的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