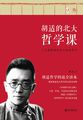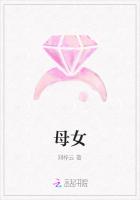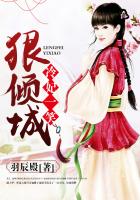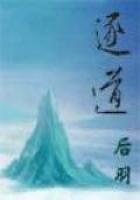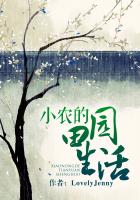哲学史家们早已注意到,中国哲学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关注道德人伦和国家治理问题,具有浓厚的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色彩,不同于西方哲学关注自然世界,突出宇宙论的倾向。老子在先秦哲学家之中的独特风貌首先就在于他表现出对宇宙论问题的极大兴趣,以及把人生哲学建立在自然哲学基础之上的立论倾向。陈鼓应先生在《老子哲学系统的形成》一文中指出:
老子的整个哲学系统的发展,可以说是由宇宙论伸展到人生论,再由人生论延伸到政治论。然而,如果我们了解老子思想形成的真正动机,我们当可知道他的形上学只是为了应合人生与政治的要求而建立的。
在这段引文中我们看到了一明显的矛盾:说老子哲学系统的展开是由宇宙论到人生论和政治论,又说宇宙论是为应合人生与政治的要求而建立。那么,究竟是先有了宇宙论,后有人生论呢,还是先有了人生论,后有宇宙论呢?看来陈鼓应倾向于后一种看法,作为根据,他还引述了徐复观先生的如下见解:“老学的动机与目的,并不在于宇宙论的建立,而依然是由人生的要求,逐步向上推求,推求到作为宇宙根源的处所,以作为人生安顿之地。因此,道家的宇宙论,可以说是他的人生哲学的副产物。他不仅是要在宇宙根源的地方发现人的根源;并且是要在宇宙根源的地方来决定人生与自己根源相应的生活态度,以取得人生的安全立足点。”从这些话来判断,陈、徐二先生均认为老子的人生哲学派生出了他的宇宙论,后者是为适应人生要求而编造出的副产品。
我们认为,老子哲学中的这两大层面的对应是老子的类比思维方式所决定的。按照老子的逻辑取向,自然是先有宇宙论,之后再类推出人生论方面的行为准则。而老子的宇宙论本身直接导源于神话宇宙观,作为他类比推理的基础和出发点,比他所表达的人生要求和政治主张有着更深远的渊源和背景。关于老子的宇宙发生论与创世神话之间的承袭关系将在后文加以讨论,这里仅就老子的类比逻辑取向做一些具体说明。
纵观《老子》全书,对“道”的论述构成全部思路的核心和基础。第一章开宗明义便提出“道”的问题,并区分出“道”的两种体现方式:“有名”与“无名”。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始;有名,万物母。
常无,欲观其妙;常有,欲观其徼。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道作为宇宙创生的总根源(天地始),是一种无名状态,即先于创造的时间和空间而存在的原初混沌状态;道作为宇宙万物发生和运动的总规律(万物母),却又体现在万物获得语言命名的规则秩序中。世界的开辟,宇宙时空的开始,即是从“无”到“有”,从“无名”到“有名”的转化过程。从永恒的“无”中,可以观照宇宙本源的无穷奥妙;从永恒的“有”中,可以观照宇宙运动规律遍及万物的情形(参见卷首彩色图版)。这种作为宇宙本源和作为宇宙规律的道虽然在“有”和“无”的名称上有异,但实际上是同一的道,可统称为“神秘”(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神秘而又神秘的道,是解答世上一切奥妙现象的不二法门(详见第五章)。
就这样,《老子》在开篇一章就从宇宙发生论角度确立了观照、分析和判断宇宙间一切事物的总标准和总原则。作为“众妙之门”的玄奥之道的确定,构成老子自然哲学的基础,也成为老子逻辑推理展开的根本出发点。
从思维方式看,作为老子进行类比论证总依据和总根源的道,其实质乃是作为神话思维时代意识形态基础的创世神话的主题的抽象和引申。如果认识到创世神话在原始思维和原始世界观中的核心地位和主导作用,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是宇宙之道在老子哲学中占据着类比依据和推理基石的重要地位。
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综合分析了世界各地的神话体系后发现,关于世界被某一创世主(a creative being)所创造的神话具有相当大的——如果不是绝对的——普遍性。几乎任何一种稍具规模的神话体系中都自然包括这种创世神话的内容。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考察儿童智力发生过程时也发现,儿童也会自发地提出关于自己和事物由来的问题,要求对此做出某种肯定的解答。无论是文化群体中发生的宗教性的创世解释,还是个体儿童内心发生的小规模的“创世记”故事,均有一个共同之处:世界的创造者(常幻化为父神或母神——所谓“世界父母”)同时也应是世界和人类的主宰者和管理人。坎贝尔认为,也许民族性的、宗教性的创世记只是儿童式的创世问题的一种翻版,它们之间的相似性说明人类认识世界与自身的要求必然随着智力的发育或进化而出现。由此可知,创世者作为创造行为之源和宇宙万物的总监理者在自发的原始思维中本来就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世界的创造为主题的创世神话实际上所要解答的问题正相当于后世哲学中的宇宙本体论课题。正像创世神话为整个神话世界的时空展开奠定基础,本体论问题的解答也为一切其他哲学问题的提出和解答奠定基础。
据我们所见,对创世神话的本体论价值做出精辟描述的是《新大英百科全书》中的《创世的神话与教义》一文。该文把创世神话定义为“特定的文化共同体解释世界由来的象征性叙述”。认为神话能够表达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创世神话在这种表达中的作用首先在于给人类在世界之中定位。这种定位可以显现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以及他所必不可少的,同其他人、自然和整个非人世界的关系。创世神话为“文化”定下一种基调和坐标,它将决定该文化共同体中所有其他方面的价值、态度和意识结构。创世神话与哲学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它是以象征叙述的形式解答哲学基本问题的。创世神话一经产生,就在原始意识形态中发挥着价值范型的作用,不仅其他神话要以它为基准,就连非神话的表达也无意识地遵循着这一范型标准。例如在《圣经·旧约》中,希伯来人的每一次民族复兴都借用范本所提供的主题和相关意象,被描绘为一次次的新的“创世记”。
与北极星干连的北斗星也曾被认为宇宙中心,与“世界大山”的昆仑相应,后来还曾与“太一”叠合起来;但是“太一”更原始、更重要的意象却是“太阳”。
基于上述认识,重读《老子》第一章的内容,显然可以看出那是用抽象语汇重申创世神话的本体论主题,其作用正是为全书展开的哲学系统确立基准和坐标。在以后的许多篇章里,同一主题又以各种方式加以重现,使类比推理的神圣依据得到反复强调。
如第十四章说:
迎不见其首,随不见其后。
执古之道,以语今之有。
以知古始,是谓道已。
第二十五章说: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漠!
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
第四十二章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第六十二章说:
道者,万物之奥。
第七十三章说: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坦然而善谋。
所有这些对道的创生功能的回顾与描绘,除了强调本体论的范型作用之外,还起到了为类比推理强调神圣的逻辑根据的作用。在《老子》一书中,宇宙之道的存在使类比推理显得十分自如。其一贯的价值取向总是同样的,即在自然与人生之间,无机物与有机社会之间建立某种体现因果关系的类比公式:因为天地自然如何如何,所以人也应当如何如何。
天地自然的现象是宇宙之道的直接体现,所以取法自然所昭示的规则范型也就是效法宇宙之道。第二十三章说:
希言自然。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天地。
天地上(尚)不能久,而况于人?故从事而道者,道德之;
同于德者,德德之;同于失者,道失之。信不足,有不信。在此,老子把飘风骤雨这种自然现象当做类比的出发点,从飘风骤雨不能持久去推论人治方面的道理:人为暴政是失道行为,不可久长,只有同于“希言”的自然之道,无为而治,才是合乎理想的治理之术。从思维方面看,把疾风暴雨类比为暴虐统治,这正是神话思维本有的在不同质的现象之中确认相似性的逻辑使然。
《老子》第四十三章再次运用此种类比逻辑: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于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
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
老子认为世人很少能够做到不言和无为,这是因为人们不明白无为的益处。为了论证无为胜于有为、至柔胜于至坚的抽象道理,他又搬出了那种体现自然与人事之间因素联系的类比等式,把“无有入于无间”这样一种人们司空见惯的自然现象作为依据,说明无形的力量(无有)足以穿透没有间隙的东西(如水之渗透力,便是老子喜用的至柔克至刚的例证),人们应当由此得到类比性的启发——“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
在自然现象“无有”与人的行为准则“无为”之间,本来并不存在任何实质性的关联,老子利用类比逻辑使二者成为同类事物,这表明他的思维方式尚未完全脱离具有自我中心倾向的神话思维。
现代心理学表明,这样的自我中心性的类比认同现象普遍发生在精神异常的患者身上。对于精神患者来说,世界变得无秩序了,不可理解了。由此导致的惊恐和痛苦必然要求为世界重新赋予意义的解释。于是患者常常在“顿悟”中“把两件事拉到一起并且合为一体”,靠建立在相似性上的同一重新给失去秩序的世界带来秩序。下面列举一些实例:
一位患产后精神分裂症的红头发的年轻妇女,她的一个手指感染了,末关节红肿。有一段时间她认为那指头就是她本人。她曾指着那个红肿的指头告诉医生:“这是我的红色的烂脑袋。”
一位患者有两个情人,一个住在墨西哥,一位住在美国纽约。她却认为这两个男人其实是同一个人,因为他俩都弹吉他并且都爱她。
还有一位患者自认为是圣母玛利亚。问她为什么这样认为,她回答说:“我是个处女,圣母玛利亚是个处女,所以我就是圣母玛利亚。”
美国心理学家阿瑞提将这类患者表现出的思维特征概括为“旧逻辑思维”。他指出:“一个用旧逻辑思维来解释的世界在许多方面都与古代人的神话世界以及当今各种土著社会的文化是相一致的。18世纪的哲学家维柯和20世纪的哲学家卡西尔最为出色地给我们描述了古代神话世界,那是个形状发生改变的、局部等于整体的、事物可以互相交换的世界。而且人类学家在各个时期都报道说,在某些土著文化中,旧逻辑思维比其他类型的思维占有优势。”在儿童思维、精神患者思维和神话思维之间存在着类同特征,这一点已为心理学家多方证实。因而三者之间可以互相阐发。阿瑞提针对上引三例患者的情况做出了总结性的分析:采用旧逻辑思维的患者们把不相干的事物视为同类。第一位患者把自己认同为手指;第二位患者将两个情人认同为一个;第三位则自认是圣母玛利亚。“患者在两个或更多的事物或人物之间发现了至少一种共同的因素,这就足可以把它们视为同一。显然这种思维在正常人看来是荒谬的。病人注意到共同具有的因素,忽略其余的因素而不考虑在内。”这种对于相似性的高度敏感也常常发生在创造过程中。老子将无形的力量同无为的原则类比认同时大概也只着眼于二者名称上的共同因素“无”;将暴风骤雨同暴政相类比时则只着眼于二者共同的抽象特征“暴烈”吧?果真如此,老子的类比思维就其逻辑特性而言显然还未彻底脱离神话思维阶段达到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科学思维。
最先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公式对精神患者的异常思维进行研究的心理学家是艾·冯·多马鲁斯(Eilhard Von Domarus)。他所提出的原则是:在正常思维中,同一性只能建立在对象完全相同的基础上;而在旧逻辑思维中,同一性可以建立在对象相同属性的基础上。像老子将中空的车轴、中空的器皿、中空的门窗与房室这三种不同事物比附在一起,用来说明“无”的作用时,正是着眼于这三种不同对象所共有的中空属性的。心理学家把这种导致认同的属性叫做同一环节或同一属性。
显然这种思维并不是遵循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这种逻辑认为只有相同的事物才能同一。这类事物是确定的,因此只能进行有限的推演。比如一个苹果可以和另一个苹果同一(二者都被看做属于“苹果”这一等级)。但是在旧逻辑思维里,苹果可以和一位母亲的乳房视为同一,因为乳房和苹果形状相似。乳房和苹果等同了。换句话说,在旧逻辑思维中,A也能够成为非A——也就是B——如果A和B具有一种相同属性(或要素)的话。
显而易见,心理学家所称的这种旧逻辑思维并非完全不合逻辑,也非无逻辑,而是遵循着自发的简单类比逻辑,它同我们从神话思维中归纳出的基本逻辑是完全相通的。在把老子的类比同这种神话的和精神病患者的类比相对照时,不难看到二者虽有相通之处,但毕竟还有程度上的微妙差异。差异之一,老子的类比总是朝向同一种价值指向的,即总是为了说明人事方面的道理而在自然方面求得类比根据。换言之,总是以天道为基础去类推人道,如第八十一章所云:“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差异之二,老子的类比范围已不局限于具体的事物,而是延展到抽象概念的层次上了。这就是说,就思维的抽象化程度而言,老子比一般的神话思维又高出一筹了。第二十六章云: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
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
轻则失根,躁则失君。
这里,老子用自然现象的抽象特征“轻与重”为类比起点,推论出国君应不轻易离开有严密保护、并便于卧息的辎重之车。
1.山东福山出土汉画像石。2.潘祖荫田藏汉画像石(榜题:辎车)。
“辎车”,汉刘熙《释名》说“载辎重卧息其中之车”。《老了》说:
“君子终日行,不离其辎重。”皆在采其安宁静重。“辎重”作为军语,则指后勤供应,重军设备等,往往有保护,处事必须稳重,“燕处超然”的行为准则。从自然事物的抽象特征“重”到人的行为准则“稳重”之间,类比转换遵循的是语词概念的本义与引申义之间的发展模式。同理,从“轻重”之“轻”到“轻率”之“轻”,类比推理遵循的是同样的语义转换模式。语言学家索绪尔早已指出,类比也是语言使用中创新的原则。
从以上两种差别特征来看,老子的类比思维虽然脱胎于神话思维,但已经充分显示出向新的更为抽象的逻辑思维转化的迹象,只是尚未达到亚里士多德第一次系统阐明的那种普通形式逻辑的规则水准,因而最能代表中国式的神话哲学的思维特征。
神话思维的类比是自我中心性的,因此它也并不遵守亚里士多德规定的矛盾律。这种矛盾律认为:A不能同时既是A又不是A。在老子的类比推理中,我们看到违反矛盾律的现象虽然不如神话中那样普遍,但也还是不乏实例的。比如在第七章中,老子为了说明圣人无私心而能保全生命,用了“天长地久”作为类比依据:天地所以能够长久,是因为天地的运动不是为自己的。到了第二十三章,却又说:“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这是为了形容天地所产生的疾风暴雨不能持久。前后对照,自相矛盾处甚为明显。老子主要出于论证的需要而随意取用自然现象作为类比根据,并不考虑矛盾律的规则。天地既可以是长久的样板,又可以是不能长久的样板,正所谓A既是A又不是A。老子哲学中这种违反普通逻辑规则之处的存在,暗示研究者不能完全用严格意义上的逻辑思维去分析和推导,而只能从神话思维的角度去做灵活的把握。如威尔赖特所言:
……进入诗里的普遍概念是具体的,并且是根本含蓄在诗里的。这就是说,普遍概念和表现它的文字分不开,也不能用逻辑来解释,否则就会歪曲它的意义。因为它的普遍性只通过具体的比拟而存在,不是通过界说和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