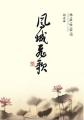作者:豪·博尔赫斯
在人类浩繁的工具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无疑是书,其余的皆为人体的延伸,诸如显微镜、望远镜是视力的延伸;电话则是语言的延续;犁耙和刀剑则是手臂的延长。而书则完全不同,它是记忆和想象的延伸。
在《恺撒大帝和克雷奥帕特拉》一剧中,萧伯纳曾说亚力山大图书馆是人类记忆的中心。书便是记忆,此外,还是想象力。
什么是对往事的追忆?还不是一系列梦幻的总和么?追忆梦幻和回忆往事之间究竟有些什么差异呢?这便是书的职能。
我曾试图撰写一部书的历史,但不是就书论书,因为我对书(特别是对收藏家的那些冗长不堪的书)的本身并无兴趣。我是想写人们对书进行的各种不同的评价。施本恪勒比我先走了一步。他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有许多关于书的精彩论述。除了同意施本格勒的看法外,我也谈谈自已的一孔之见。
古人并不像我们这样推崇书——这令我十分吃惊。他们只把书看成是口头语言的替代物。“说出的话会飞掉,写下的东西留下来。”这句人们经常引用的话,并不是说口头语言会转瞬即逝,而是说书面语言是持久的、然而是僵死的东西,口头语言则像是长了翅膀一样,十分轻盈,正如柏拉图所说,口头语言是“轻快的、神圣的”。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人类的许多伟大的导师的学说均是口授的。
我们先来看看毕达哥拉斯的情况。我们知道,毕达哥拉斯故意不留下书面的东西,那是因为他不愿被任何书写的词语束缚住。毫无疑问,他肯定已经感受到“文字能致人死命,精神使人新生”这句而后在《圣经》中出现的话的含义。他感受到了这一点,不愿受制予书面语言。因此,亚里士多德从未提到过毕达哥拉斯,而只是谈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弟子们。譬如,他对我们说过,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传人们重视信仰、法规;主张永恒的复归。这些思想过了很久以后被尼采又发掘了出来。这就是受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一书批驳过的时间是循环的看法。圣奥古斯丁运用了一个绝妙的比喻,说基督的十字架把我们从禁欲主义者的圆形迷宫中解救出来。时间是周而复始的看法,休漠、布朗基,以及别的许多哲学家都谈到过。
毕达哥拉斯有意不写下任何东西,他是想在他逝世后,他的思想还能继续留在他的弟子们的脑海中。这就是“Magister dinit”(我不懂希腊文,只能用拉丁文来表示,其意为“吾师曰”)
的来源,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弟子们会被导师说过的话束缚住手脚。恰恰相反,这正好强调了他们可以完全自由地发挥导师指出的思想。
我们并不清楚是不是他开创了时间是周而复始的理论,但我们知道,他的弟子们却很推崇这个理论。毕达哥拉斯虽已作古,但他的弟子们却通过某种轮回的方式(这正是毕达哥拉斯所喜欢的)继承了他的思想,当有人指责他们,说他们提出了某种新的说法时,他们就会这样说,我们的导师曾经这样说过。
此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些例子,最引人注目的要算柏拉图了。他说书就像是肖像(可能他这时想到了雕塑或绘画),人们会把它们看作是有生命的,但向它们提问时,它们却不会作答。
为了改变书不会说话的缺陷,他搞了个柏拉图式的对话。这样,柏拉图便以许多人的身份出现了。有苏格拉底、高尔吉亚和别的人物。对此我们还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即柏拉图想象着苏格拉底仍然活在世上,以此来告慰自己。每当他遇到什么问题时,他总扪心自问:要是苏格拉底还活着,对此会说些什么呢?以此表明苏格拉底虽死犹存。他死后也没有留下任何书面的东西,是一位靠口授的宗师。
对于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只写过几句话,却早已被泥沙给抹去了。之后,他没有再写过我们知道的东西。菩萨也是一位口授的大师,他的说教至今仍萦回于人们的耳际。下面我们看一下安瑟伦的名言:把一本书置于一个无知者的手中,就像把一柄剑放在一个顽童的手中那样危险。古代的人们就是这样看待书的。在整个东方还有这样的观念:书不应该用来揭示事物,它仅仅是用来帮助我们去发现事物。尽管我对希伯来文一无所知,我多少还学了点“神秘哲学”,看了《启明书》和《关系论》的英文和德文版。我知道这些书写出来不是为了让人们去理解他们,而是为了让人们去解释它们,它们激励读者去继续思索。在古代,人们没有像我们这样崇敬书,尽管我们知道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在枕头下总放着两件武器:《伊利亚特》和剑。那时候人们都非常尊敬荷马,但是,并不像我们现在这样把他看作是一位圣贤。那时候人们并不认为《伊利哑特》和《奥德赛》是神圣的书,那只是两部受到尊敬的书,人们可以对它们进行批评。
柏拉图将诗人们从他的共和国里驱逐出去,却又未被人们指责为排斥异己。我们还可以举一个古代人反对书的例子,那就是塞涅卡,在他致卢西里奥的令人赞叹的书信中有一封信是指责一位虚荣心很强的人,说他的图书室里收藏了一百册书,塞涅卡因此问道,谁有时间看完这一百册书呢?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为数众多的图书馆已受到人们的珍视。
对于古代的一些事我们是很难理解的,那时的人不像我们这样崇敬书,他们总把书看成是口头语言的替代物。后来,从东方传来了一个新的观念——关于天书的观念。我们来举两个例子,先从后来的例子说起,即谈谈穆斯林教徒对书的看法。他们认为《古兰经》产生于世界诞生之前,也产生于阿拉伯语形成之前。他们认为它是真主固有的一个属性,却不是上帝的作品,就像是怜悯、公道一样。《古兰经》里曾经神秘地谈到过该书的原型,它乃是一部在天上写成的《古兰经》,它便是《古兰经》的柏拉图式的原型。《古兰经》里说,正因为这本书在天上写成,因而它是真主的一个属性,它产生于天地形成之前。穆斯林的学者或阿訇都是这么认为的。
我们还有一个近在咫尺的例子:《圣经》,或说得更具体一点,《犹太教典》和《摩西五书》。据认为,这些书都是圣灵口授的,把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时代写成的书都说成是出自同一圣灵之手,这的确是件颇为有趣的事情。《圣经》说:“神是无处不在的。”希伯来人想把不同时代的各种文学作品综合起来,合成一本书,其书名就是“Tora”,(意即希惜文的《圣经》)所有这些书都被归于一个共同的作者:神灵。
一次,人们问萧伯纳是否相信《圣经》系圣灵之作,他回答说,所有值得反复阅读的书都是神灵的作品,也就是说,一本书的含义必定会超越作者的意图。作者的意图往往是浅薄的,有时甚至是错误的,然而,书里总包含有更多的含义。拿《堂吉诃德》为例,它就不仅仅是一部嘲讽骑士小说的书,它是一部纯净的书,书中绝没有任何信手拈来之物。
我们来设想一下这样一首诗的含意。譬如我说:
潺潺流水晶莹透亮
岸边绿树映在水中
绿色草原密布浓荫
显而易见,这三行诗每行都是11个音节,它为作者所喜爱,是他意志的体现,是人为的。但是,同神灵写出来的作品相比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同写出书的神的观念相比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神灵写出的这本书中没有信手拈来的东西,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每个字母都是事先想好的。譬如,《圣经》是以Bereshit baraelohim开头的,其第一个字母为“B”,因为这一字母与Ben-decir(赐福)一词相应。这是一部没有任何信手拈来之物的书。
这一情况使我们想到《神秘哲学》,它会促使我们去研究文学,去研究由神灵书写的书,这与古人的想法相反,他们对灵感的看法比较模糊。
歌唱吧,诗神,阿喀琉斯暴怒了。荷马在《伊利亚特》这一史诗开篇时是这样说的。他说的诗神即为灵感。倘若人们想到神灵,那一定会想到某个更具体更有力量的东西,这个东西便是下凡到文学上来的上帝。上帝已写了一本书,在这本书中,绝无任何信口开河之词,连这本书的字数,每句诗的音节的多寡都有一定之规。正因为这样,我们能用字母来做文字游戏,也能衡量每个字母的价值,原因便是这一切都是经过事先斟酌的。
这便是对书的第二种看法,即节是神灵之作。或许这种看法比古人的想法更接近于我们现在的看法。古人认为书是口头语言的代替物,以后又认为书是神圣的,之后,又被其他一些看法所取代。譬如,有人认为一本书代表一个国家。我们还记得穆斯林们把以色列人称为书之人,也还记得海涅的那句话,他说那个民族的祖国就是一本书。那个民族指的是犹太人,那本书是《圣经》。如此说来,我们对书又有了个新的看法,即每个国家都由一本书来代表,或由著有许多书的作者来代表。
令人诧异的是(我并不认为这点迄今已被人们所发现),各国推选的代表其形象并不十分像这些国家。譬如,有人会想,英国应推约翰逊博士为代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英国选了莎士比亚,而莎士比亚(我们权且这么说)正是最不富有英国特色的英国作家。英国作家的特点是寓意含蓄,也就是意在不言中。
而莎士比亚恰恰相反,他善于在比喻中运用夸张手法。倘若有人说莎士比亚是意大利人或犹太人,丝毫也不会令我们吃惊。
德国的情况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值得尊敬、但极易狂热的国家,它恰恰选了一个宽宏大度、并不狂热、国家观念极其淡薄的人为其代表,他就是歌德。德国是由歌德来代表的。
法国尚未选出能代表自己的作者,人们倾向于雨果。毫无疑义,我十分敬佩雨果,但雨果并不是典型的法国人,他可以说是个在法国的外国人。雨果那层出不穷的比喻和华丽的词藻表明他并不是典型的法国人。
更令人惊奇的例子要算西班牙了。西班牙本应由维加,卡尔德隆或克维多来代表,但并非如此。它却由塞万提斯来代表。
塞万提斯是宗教迫害时期的人,然而他的态度是温和的、宽容的。可以说,他既无西班牙人的美德,也无西班牙人的恶习。
仿佛每个国家都想由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来代表,以补救自己的不足,弥补自己的缺陷。我们本应选择萨米恩托的《法昆多》当作国书,但我们没有这样做。由于我们有战争的历史,刀光剑影的历史,我们便把叙述一个逃兵的史诗《马丁·菲耶罗》作为代表。尽管这本书被选中是有理由的,但怎么能设想我们的历史会让这么一个征服荒原的逃兵来代表?然而,事实就是这样,似乎每个国家都感到有这个必要。
关于书的问题,许多作家都有光辉的论述,我只想谈谈其中的几位作家。首先我要说的是蒙田,他在一篇谈书的论文中有这么一句至理名言:我若无兴便不命笔。蒙田认为强制性的阅读是虚假的观念,他说过,倘若他看书时看到一段费解的章节,便把书放下,因为他把看书当作一种享受。
我还记得许多年以前有人曾作过一次关于什么是绘画的民意测验。当人们问到我的姐姐诺拉的时候,她说:绘画是以形式和色彩给人以愉悦的艺术。我可以说,文字也是一种给人以愉悦的形式。如果我们看的书很费解,那么,书的作者就是失败的了。因此,我认为像乔伊斯这样的作家从根本上说是失败的,因为读他的书异常费力。
看一本书不应花费很大的气力,费力便令人感到不舒服。
我想蒙田说的颇有道理。他还列举了几位他喜欢的作者,他谈到维吉尔,说对于《农事诗集》和《伊尼特》他更喜欢前者,而我却喜欢后者,但这是无关紧要的。蒙田谈起书来总是充满了激情,他说尽管看书是一种享受,却带有忧郁之情。
爱默生的看法与蒙田大相径庭。他对书也作了重要的论述。在一次讲座上,他称图书馆是一座神奇的陈列大厅,在大厅里人类的精灵都像着了魔一样沉睡着,等待我们用咒语把它从沉睡中解脱出来。我们必须打开书,那时它们便会醒来。他还说,看了书我们便能与人类的优秀分子在一起,但我们不能光听他们的话,最好是同时看看书评。
我曾在布宦诺斯艾利斯大学哲学系当了20余年的英国文学教授。我总是告诫我的学生们要少看参考书,不要光看评论,要多看原著。看原著可能他们并不全懂,但他们听到了某个作家的声音,并感到欣慰。我认为,一个作者最重要的东西是他的音调,一本书最重要的东西是作者的声音,这个声音通过书本到达我们的耳中。
我一生中有一部分时间是在阅读中度过的。我以为读书是一种享受,另一种较小的享受乃是写诗,我们或将它称为创作,这是对我们读过的东西的一种回忆和遗忘相结合的过程。
爱默生和蒙田都主张我们应该只看能使我们欢愉的东西,他们都认为看书是一种幸福。我们对书都寄予厚望。我一贯主张要反复阅读,我以为反复阅读比只看一遍更重要,当然,反复阅读必须以初读为前提。我对书就是这样迷恋,这样说未免有点动情,当然我们不想太激动,我只是对你们说说自己的心里话,我不是对所有的人说话,因为“所有的人”是个抽象的概念,而每一个人才是具体的。
我仍然没有把自己当成盲人。我继续买书,继续让书堆满我的家。前些日子有人送我一套布罗克出版社1966年出版的百科全书,我感觉到这本书在我家里,觉得这是一种幸福。这一套字体潇洒、共有20余卷的百科全书在我家里,只是我不能阅读,里面有许多我看不见的地图和插画。尽管如此,这套书总在我家里,我感觉到书对我具有亲切的吸引力,我想,书是我们人类能够得到幸福的一种手段之一。
有人在谈论书的消失,我以为这是不可能的,可以谈谈书和报纸或唱片的不同。它们的区别就在于,一张报读后便会弃之脑后,一张唱片听后也会被人遗忘,因为那是比较机械的东西,没有严肃的内容,而读一本书能使人永志不忘。
关于书是神圣的概念——如关于《古兰经》、《圣经》、《吠陀经》里面叙述了吠陀如何创造了世界的看法——可能已经过时了,然而书仍然具有我们试图不让它失去的某种神圣的东西,人们取来一本书,打开它,这本身就有美学的含义。让词语躺卧在书中,让那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僵卧着又有什么意义呢?毫无意义。倘若我们不打开它,书又有什么用呢?它仅仅是一卷纸或是一卷皮而已。但是,如果我们去读它,就会出现新奇的东西,我以为每读一次都会有新的内容。
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我已引用过多次),任何人也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这是因为河水足在不断地变换着,而我们并不比河水的变化更小。我们每读一次书,书也在变化,词语的含义在变化。此外,每本书都满载着已逝去的时光的含义。
我刚才说过我不同意看书评,现在我想跟自己唱一唱反调(说几句自相矛盾的话也了无妨么)。哈姆莱特已经不完全是莎士比亚在17世纪初塑造的哈姆莱特了,哈姆莱特已成了柯勒律治、歌德和布拉德莱笔下的哈姆莱特了,这个人物已被重新进行了塑造。堂吉诃德的情况是如此,卢戈内斯和马丁内斯·埃斯特拉达的命运也是这样。《马丁·菲耶罗》也已经不是以前的《马丁·菲耶罗》了,因为读者在不断地丰富着书的内容。
当我们看一本古书的时候,仿佛看到了从成书之日起经过的全部岁月,也看到了我们自己。因而,有必要对书表示崇敬,尽管有的书有许多错误,我们也可能对作者的观点不能表示苟同,但是它总含有某种神圣的令人尊敬的东西。对书我们虽不能迷信,但我们确实愿意从中找到幸福,获得智慧。
“简评”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一1986),阿根廷著名诗人、小说家。主要作品有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热情》、《面前的月亮》等,小说集《世界性丑事》、《交叉小径的花园》等。
博尔赫斯博览群书、学贯中西,其作品风格独特,自成一派,人称“宇宙主义”或“卡夫卡式的幻想主义”。博尔赫斯的一生几乎都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这篇作品以和悦的笔调写出了书的历史以及对书的礼敬态度。论者认为博尔赫斯的创作素材不是来自生活,而是来自书本,正是在古今各国书本中钩沉索隐的功夫使他触发了无数令人击节惊叹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