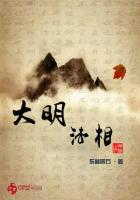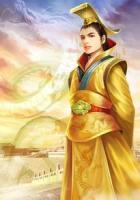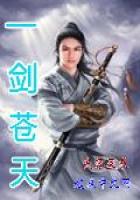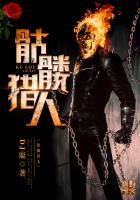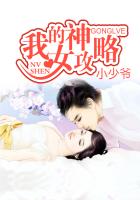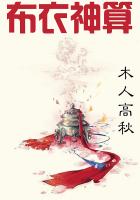一
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是抗战前期我国文艺界关于文艺理论的一次最大规模的论争,它既是之前“文艺大众化”论争的承继,又与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发展方向和道路相联系。关于它的起因,一般以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为标志,认为它是引起民族形式论争的导火线。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到:“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这里提到的“民族形式”、“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等术语,虽然最初提出是针对政治思想而谈,但其基本精神也同样适用于文艺界。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再次谈到“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7页。毛泽东关于建立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民族形式的论述,在文艺工作者中引起极大反响,促进了广大文艺工作者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于是,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开始进行。
当然,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得以真正开展与深入还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发起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的生死存亡之中,民族意识空前高涨。在当时一切为了抗战的语境下,抗战救亡文学运动蓬勃发展,“文章下乡,文人入伍”的口号得到了广泛地响应。但是文艺工作者们逐渐认识到,只有通俗化大众化的作品才能为广大民众所接受,才能激起他们的抗日救国热情。因此,必须深刻地认识统一战线的、民族战争的、大众本位的、活的民族现实,文艺运动应该在方法上内容上提出和现实情势相应的口号,但为了方法上的内容上的要求得到补充的说明,也就需要从形式方面明确地指出内容所要求的方向,这就是“民族形式”这一口号的提出。
另外,苏联文艺思潮对民族形式问题的提出影响也很大。郭沫若曾指出“‘民族形式’的提起,断然是由苏联方面得到的示唆。苏联有过‘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的号召”。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兑》,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437页。“民族形式”概念并不是毛泽东最初发明,它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了斯大林“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论断的启发。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主客观条件的作用下,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得以展开。这场争论最初是在延安解放区展开。当时在延安的一些文艺工作者围绕毛泽东的讲话,围绕“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等问题展开讨论。但是真正将这场文艺论争推向高潮,则是随后在国统区尤其是重庆掀起的围绕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的讨论。
二
在国统区展开的有关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主要围绕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展开讨论,以向林冰和葛一虹为代表的争论的双方围绕这一问题展开针锋相对的论争。1940年下半年,论争进入第二阶段,《新华日报》社召开座谈会,使论争从仅仅围绕中心源泉问题深入到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以及如何对待中外文化遗产等问题上,讨论更加全面深入。
(一)第一阶段的论争
一是以向林冰为代表的观点。
1940年3月24日,向林冰在重庆《大公报》发表《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一文,针对之前一直进行的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问题提出他自己的看法。向林冰认为“民间形式的批判的运用,是创造民族形式的起点;而民族形式的完成,则是运用民间形式的归宿。换言之,现实主义者应该在民间形式中发现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向林冰:《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427页。即“民间形式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这一观点曲解了民族形式所应该包含的内容,否定了五四以来新文艺形式的发展和所取得的成果,将“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简单地等同起来,实质上是抗战初期“旧瓶装新酒”观点的再次提及,抹煞了五四以来一切新的文学,引起了各方激烈的争论。
向林冰以“新质发生于旧质胎内,通过了旧质的自己否定过程而成为独立的存在”向林冰:《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425页。作为其理论基础,并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详细论证:
首先,他认为民间文艺形式是大众“习闻常见的自己作风与自己气派,是其存在形态在文艺的质的规定上的反映”。向林冰:《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426页。由于“存在决定意识”,所以“喜闻乐见”应以“习闻常见”为基础,民族形式应以民间形式为基础。他更进一步指出,这是争取文艺大众化――通俗化的根本前提。其次,他认为“内容决定形式”,民间形式在一方面是“民族形式的对立面”,另一方面“又是民族形式的同一物”,它在“本性上具备着可能转到民族形式的胚胎”。因此,完全可以对旧有的民间形式加以批判地运用,使之成为创造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除此以外,向林冰还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加以完全的否定。他认为“五四以来的新兴文艺形式,由于是缺乏口头告白性质的‘畸形发展的都市的产物’,是大学教授,银行经理,舞女,政客以及其它小‘布尔’的适切的形式”。向林冰:《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427―428页。完全抹煞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对其加以彻底的否定,认为它不可能成为民族形式创造的中心源泉,而“只应置于副次的地位”。
向林冰的观点一经发表,就遭到了葛一虹、胡风、郭沫若等人的强烈反对。他简单地肯定并完全要利用民间形式,认为在当时抗战时期所提倡的新的民族形式的创造不过是过去旧的形式,再添加进新的抗战的内容就足够了。将“喜闻乐见”解释为“习闻常见”,这不免有偷换概念的嫌疑。“如以‘中国老百姓所习闻常见’为标准,那末一切形式都应该回复到鸦片战争以前。小脚应该恢复,豚尾也应该恢复,就连鸦片烟和吸烟的各种形式都早已成为‘中国老百姓所习闻常见’,而且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所独有的‘民族形式’,也有其合理的存在,那中国岂不糟糕!”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兑》,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438―439页。葛一虹、胡风等人不但反驳向林冰的观点,并相应提出了各自对“民族形式”的理解。
二是以葛一虹为代表的观点。
向林冰提出“中心源泉论”之后,遭到各方面的强烈反对,其中以葛一虹最为典型。与向林冰以民间形式作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观点相反,葛一虹在1940年4月《新蜀报》上发表《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谓“民间形式”吗?》,对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大加肯定,认为它“本身是完美的”,在“普及性上之所以不及旧形式,其原因在于一般劳动人民知识低。”所以,提出“目前我们迫切的课题是怎样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准,而不是怎样放弃了已经获得的比旧形式‘进步与完善’的新形式”。葛一虹:《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谓“民间形式”吗?》,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435页。葛一虹反对将民间形式作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取而代之以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他指责向林冰抹杀五四新文艺的成绩,指责他的观点是“新的国粹主义”。
在葛一虹看来,在当时新的形势即全民族抗战的社会背景下,为了表现人民大众高涨的抗战热情,就应该创造出适合于抗战的民族形式,这样的民族形式应该是“继续了五四以来新文艺艰苦斗争的道路,更坚决地站在已经获得的劳绩上,来完成表现我们新思想新感情的新形式――民族形式”。葛一虹:《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谓“民间形式”吗?》,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435页。他认为只有这样的形式才是真正为老百姓喜见乐闻的,才是新鲜活泼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葛一虹这一系列的观点有其合理性和先进性,然而其中有些也显得简单片面而有失偏颇。例如,他认为民间形式是“没落文化”,是“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品,是已陷入没落文化的垂死时的回光返照”等全面否定民间形式的看法就遭到了部分论争者的质疑。由于他和向林冰的观点各自都有其合理与片面的地方,所以引起了接下来的更为激烈的争辩。
(二)第二阶段的论争
一是关于民族形式问题论争的座谈会。
为了对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国统区于1940年4月21日和6月9日分别召开了两次座谈会,将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继续深入。
1940年4月21日,由《文学月报》在中苏文化协会主办了讨论会。会议在罗荪的主持下进行,王芝冈、叶以群、光未然、向林冰、葛一虹、臧云远、潘梓年、胡绳、戈茅等21人出席。与会人员积极发言,各抒己见。叶以群认为:“新文学是中国文学底正常的发展,是与‘五四’以前的旧文学脉络相承,决非从天而降的怪物”。《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456页。要创造新的民族形式,就应该“承继中国历代文学底优秀遗产,接受他们的形式的精粹”、“接受民间文艺底优良成分”,同时还要“吸收西洋文学底精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457页。戈茅也认为:“民族形式不等于旧形式,不只是利用一下旧形式就成功,而是如何创作新形式的问题”。《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458页。抗日的内容与民族的形式不能分开,只有与现实生活大众生活相联系的作品才能有民族形式的产生。潘梓年说:“民族形式不是利用旧形式,旧形式是简单的,不够适应于表现目前这新的复杂的社会生活,改造旧形式并不能解决新形式(民族形式)的创造,只能来救济,应当吸收它的优点接过来运用,把它粉碎了消化了创造新的民族形式”。《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458页。总的来说,大部分参会人员都不赞成单独以某一方面作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而应将旧的民间形式与五四以来的新文艺相结合,各取所长,同时吸收国外文学的精华,立足于抗战的现实,创作出新的民族形式。
1940年6月9日,《新华日报》社再次召集文艺界人士在一心花园召开座谈会,继续探讨民族形式问题。会议由《新华日报》社总编潘梓年主持,叶以群、胡绳、戈茅、艾青等18人参加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问题,讨论扩展到更广的范围。与会者除了讨论“中心源泉”这一基本问题之外,还涉及到文学的大众化通俗化、文学的深与广甚至戏剧音乐等问题。叶以群就指出:“自从民族形式提出,到现在为止,一直停留在民间形式是不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问题上了,现在应该把这一问题向前拉一步,更深入更广泛地展开讨论,我觉得民族形式,是中国所发生的现实应该用怎样活泼的形式表达出来的问题”。《民族形式座谈笔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475页。臧云远认为:“文艺本身,尤其是民族形式的文艺的本身,也包含着深与广的统一起来的可能性”。《民族形式座谈笔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476页。会议结束后,潘梓年作了总结性的发言,他将大家的发言总的归纳为六点:第一,民族形式问题的提出;第二,形式不能离开内容来讲,不管什么样的民族形式都不能与内容分开来谈;第三,五四后新文艺运动的发展阶段;第四,对民间形式进行讨论;第五,新文艺运动与通俗化,大众化运动;第六,历史题材问题。在总结其他人发言的基础上,潘梓年同时还讲述了自己的看法,主要倾向于对向林冰观点的批驳。
在这两次座谈会之后,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就不再只是局限于“中心源泉”之上了,之后的讨论范围更加广泛深刻,更接近民族形式的实质。
二是郭沫若和《“民族形式”商兑》。
继向林冰和葛一虹相继提出自己的观点,并争论不休之后,1940年6月9日、10日,郭沫若连续两天在重庆《大公报》发表名为《“民族形式”商兑》的文章,阐明他在这场论争中的看法。郭沫若在文章中明确提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毫无可议的,是现实生活。今天的民族现实的反映,便自然成为今天的民族文艺的形式。它并不是民间形式的延长,也并不是士大夫形式的转变,从这两种的遗产中它是尽可以摄取些营养的”。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兑》,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450页
首先,他否定向林冰“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中心源泉的说法,认为“‘喜闻乐见’被解释为‘习闻常见’,于是中国的文艺便须得由通俗文艺再出发,民间形式便成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这个见解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兑》,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438页不能以老百姓“习闻常见”作为标准,否则一切诸如“小脚”、“鸦片烟”的旧有形式都可以算做中国所独有的民族形式。在否定将民间形式作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同时,郭沫若也强调对旧形式利用的重要性。在当时抗战形势严峻,民众教育水平不高的历史条件下,对与人民大众有着密切关系的民间形式的合理利用显得尤为重要。“在目前我们要动员大众,教育大众,为方便计,我们当然是任何旧有的形式都可以利用之”。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兑》,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441页。他强调,用旧诗词的形式来写抗战的内容未尝不可;旧小说中的个性描写也可以用来增添文章的表现。同时,他还分析了音乐、戏剧、绘画等民间形式的利用价值。在谈到如何利用旧形式的问题上,他认为“我们现在是在尽力扬弃我们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命运的,把这些和时代精神盛在民间形式里面去教育民众,宣传民众,民众获得了这种精神,结局是要抛弃那种形式的”。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兑》,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444页。这种结局是要抛弃旧形式,因此它自然不可能成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
其次,在谈到新文艺这个问题上,郭沫若也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他对新文艺并不是持完美无缺或已经有绝好成绩的态度,而是指出了两个他认为不满意的地方:首先,“最大的令人不能满意之处,是应时代要求而生的新文艺未能切实的把握时代的精神,反映现实生活”。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兑》,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448页。原因还是在于新文艺是个新生事物,它的历史尚短,从事新文艺工作的年轻人大多没对本国现实有切身的经历感受。其次,“新文艺的来源地是中国几个受近代化的程度较深的都市,尤其象上海,那差不多等于外国的延长”。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兑》,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448页。这样的作品显得过分欧化,将中国人塑造成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为了克服新文艺的各种弊病,就需要“作家投入大众的当中,亲历大众的生活,学习大众的言语,体验大众的要求,表扬大众的使命”。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兑》,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449页。文艺工作者如果能够做到上面提到这些,那么他的作品一定能符合大众的欣赏水平,达到教育大众的目的。
最后,郭沫若在文中提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毫无可议的,是现实生活”。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兑》,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450页。
民族形式的创造是历史的必然,是现实生活的必要,我们既然要求要有民族的形式,就必须要有现实的内容。“民族形式”在抗战的新现实下,就必须要赋予新的内容。它不是民间形式或士大夫形式的转变,也不是国外新形式的照搬,而是经过消化与吸收,和中国现实相结合,体现民族特点的中国自己的民族形式。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在创作中,不断深入现实,从中吸取创作源泉,采用民众自己的语言写民众的生活。
这篇文章的发表,较好地解决了在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中一直存在的“中心源泉”问题,明确了在民族形式创造过程中如何看待和利用民间形式,如何对外国文艺的消化与吸收问题等问题。在此之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就不再如第一阶段时简单围绕源泉问题来谈,而是继续向着更深更广的范围展开,涉及到更多实质性的问题。
三是胡风在论争中的观点。
1940年10月,胡风在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后期在重庆撰写并出版了《论民族形式问题》一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在民族形式问题上的一些看法和主张。该书不仅延续了之前文艺大众化通俗化的探讨,而且涉及到文学的形式与内容,文学的形式与现实生活等问题,突破了前期讨论的局限性。在此书出版后,关于这场论争的各种观点便逐渐销声匿迹了。
在《论民族形式问题》中,胡风立论的出发点在于对向林冰“新质发生于旧质的胎内”的否定上。同时,他还指出,在反对向林冰的人当中“不但没有谁从原则上提出过反对,有的(胡绳、潘梓年、黄芝冈、葛一虹、以群、罗荪等)甚至还明确地表示了同意,说‘这些理论根据都是没有问题的’(胡绳)”。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胡风全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0页。为此,胡风引用了卢卡契《叙述与描写》中“表现现实的新的风格、新的方法,虽然总是和以前的诸形式相联系着,但是它决不是由于艺术形式本身固有的辩证法而发生的。每一种新的风格的发生都有着社会的历史的必然性,是从生活里面出来的,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这段话对“新质发生于旧质胎内”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驳。此外,他还引用了大量的证据来说明文艺的发展不是靠内在的辩证发展而来的。他说明,历史上每一次新的文艺思潮、新的文艺形式的产生以及繁荣都是和先前的思潮形式作过激烈的斗争。“文艺创作是为了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并不能抛掉这原则有意识地去发展某一固有形式,那么,文艺的发展就不是用‘形式本身固有的’内在的辩证法平行地去对应存在的发展”。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胡风全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6页。
新的文艺在发展的进程中,必须要和旧形式作坚决的斗争,尤其是当旧形式愿意装着好像只反对新的形式而不反对新的内容,形成其好像和内容无关的本身的优点的时候,尤其是当旧形式愿意接受“批判”,让出一点地位给“新内容”的时候,这种斗争就显得尤为必要和更加艰难。这样的论述,给予“旧瓶装新酒”、“新质发生于旧质的胎内”的观点以坚决的打击。
尽管胡风对向林冰的观点进行批驳,但是在对民间文艺的理解上,他和葛一虹的观点又不完全相同,不是为了维护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而走向另一个极端。他对民间文艺并不是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认为:“现实主义的作家虽然应该深彻的研究民间文艺,但并不是为了要‘运用’它的形式,而是为了要从它得到帮助,好理解大众的生活样相,解剖大众的观念形态,汲受大众的文艺词汇”。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胡风全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55页。将大众的生活样相,大众的观念形态融化到现实生活里面,经过作家观点的组织,成为新的内容融化到大众的口头语言里面,经过作家创作方法的组织,成为新内容相应的新形式的材料。由此可以看出,胡风对民间形式的理解在于不是为了运用形式,也不是为了接受内容,而是为了得到帮助,在此基础上能够更好地理解大众的思维方式、表现感情的方式以及认识生活的方式,即所谓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可见,胡风对待民间形式的态度,既不同于向林冰的观点,又认为周扬、艾思奇等对民间文艺的理解缺乏说服力。归根到底,他强调的是文艺与现实生活的结合,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对民间形式加以分析和利用。
另一方面,在对待五四新文艺上,他持的是一种肯定的态度。在引用了向林冰、郭沫若、何其芳、罗荪等人对这一问题的观点,并且回顾了五四新文艺的发展道路之后,胡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要理解五四的‘文艺史观’,不能仅仅看它说出了什么,重要地还应该要看它反映了什么”。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胡风全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1页。对于新的文艺思潮的理解,不能只从它的立论表现上去评价,还应该在创作的过程中加以理解。为此,他列举鲁迅、郭沫若、康白情和湖畔诗人等为例,说明五四新文艺为了内容上的突进,为了革命精神的要求,形式上也采取了一种崭新的前无古人的姿态。尤其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为例,说明五四以来产生的这种新的形式是在国际文学的影响之下,在中国社会的基础之上生根发展起来的东西。所以,“以市民为盟主的中国人民大众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正是市民社会突起了以后的、累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的一个新拓的支流。那不是笼统的‘西欧文艺’,而是:在民主要求的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以及浪漫主义)文艺;在民族解放的观点上,争求独立解放的弱小民族文艺;在肯定劳动人民的观点上,想挣脱工钱奴隶的命运的、自然生长的新兴文艺”。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胡风全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4页。胡风认为,五四新文艺正是从上面提到的这些接受了思想、方法、形式,在民主革命的实践的要求里面将这些思想、方法、形式化为斗争的立场、创作上认识中国现实的路向、组织形象的能力。由此,五四新文艺才可以“获得了和封建文艺截然异质的、崭新的姿态,内容上的‘表现的深切’和形式上的‘格式的特别’”,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胡风全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4页。成为一场伟大的文学革命运动。这样,胡风赋予了新文学以崇高的历史地位,它不仅建立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联系,而且又与传统的中国文学有质的区别,它具有了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要求,是世界进步文艺传统的一个新拓的支流。
总之,胡风在民族形式论争中一直坚持的是文艺运动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观点。希望通过“民族的形式”反映“新民主主义的内容”、“‘民族形式’,不能是独立发展的形式,而是反映了民族现实的新民主主义的内容所要求的、所包含的形式”。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胡风全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7页。他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现实主义的发展必须以五四革命文艺传统作为基础,它一方面是“接受世界革命文艺的经验来认识(表现)民族现实而形成的”,一方面也是“通过民族现实的认识(表现)去融化世界革命文学的经验而形成的”。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胡风全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8页。这就是说,民族形式的创造是国际的东西和民族的东西矛盾统一的结果,是对现实主义的合理的艺术表现。而所谓的“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论以及“旧瓶装新酒”的理论在本质上是违反现实主义的,因而是不可取的。所以,民族形式的创造应该以现实主义的五四传统为基础,“一方面在对象上更深刻地通过活的面貌把握民族的现实(包括对于民间文艺和传统文艺的汲取),一方面在方法上加强地接受国际革命文艺的经验(包括对于新文艺缺点的克服)”,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胡风全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4页。只有按照这样的方法,才能创造出能够反映新民主主义内容的新的民族形式。
胡风在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观点鲜明,坚持己见,较之前讨论的一些见解更具理论性,但其中一些也不免有偏激狭隘之处。
三
这场在解放区最先兴起,并在国统区得以深入开展的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组织地进行的。正如李泽厚在《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中提到,这场论战具有科学(学术)和意识形态(政治)交错的鲜明特点,论争双方处于势不两立的状态,取得意识形态优势的一方还常常“以不公平或主观情感来抹杀和忽视论敌中的合理成分和因素”。李泽厚:《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74页。从最初由毛泽东的讲话引起论争,到后来在各地特别是在重庆的报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召开的座谈会,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在整个讨论中,尽管有的观点不够全面,有的讨论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但总的说来都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次大的学习,扩大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国统区的影响。
如今我们重新认识和研究民族形式论争的相关问题时,就应该客观地站在全面的、历史的角度对这次讨论进行评价。向林冰、葛一虹、胡风等人的看法确实有不妥之处,但他们各自的观点仍都有其可取的地方,都是属于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学术讨论,不能大加指责甚至全盘否定,对一些认识上的偏差也应该历史地对待。
总的说来,这次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次大学习,在国统区文艺界中加强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影响。它对抗战时期的文艺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使文艺沿着“抗战的内容与民族的形式”的道路前进。同时,也为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起到了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