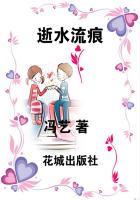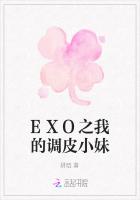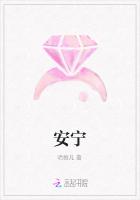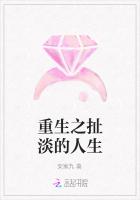1
在从莫斯科去图拉的路上,我在想,一个乡村的老头,一个地主,它蛰居在图拉的森林深处——往莫斯科三、四百里的路上,也到处是荒凉的田野和森林,他为何有如此视野,写下《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
车在陈旧的高速公路上颠簸着,窗外却是安静、平坦的森林与原野,池塘青草挺立,野钓的人如幻影,没有村庄,只有那些常见的度假小木屋,蓝天、白云、鹰,和若有若无的风。
这是一个可以思想的国度,因为她安静;这是一个具有农民情怀的国度,因为她接近农耕时代的景色。有人说托尔斯泰晚年要立志“务农”,可能是对沙皇和整个旧制度的唾弃和蔑视,却不知道他也说过这样的话:我的愿望是全世界的人都脱光衣裳,在田野上耕种。俄罗斯这块地旷人稀的土地很适合人产生这种浪漫的、童贞般的奇想。
图拉,并没有因为有托尔斯泰而声张,没有托尔斯泰的雕像,没有“欢迎”的广告牌与条幅,没有以托尔斯泰命名的饭店与商场,就连庄园门前,依然还是安静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小摊,所卖的纪念品也十分有限。一个朴素的庄园最能隐藏下托尔斯泰和他的历史。
庄园称为“亚斯纳亚·波良纳”,是“明亮的草地”的意思,也有人称“朽木林中的空地”。地主托尔斯泰在十九岁时就继承了这片土地,约四百多公顷,六千多亩;而他的家族在这儿共有二千二百公顷,即三万多亩。可以想见一个十九岁的年轻地主(而且是父母双亡)拥有了这么多土地和土地上五个村庄的欣喜若狂,美好的日子就要来到了,荣华富贵,妻妾成群,声色犬马那不是顺理成章的吗?可是,十九岁的地主托尔斯泰做的第一件事却是给农民送去茅草,让他们修房子。
这个写小说的地主从一开始就与众不同。他喜欢劳动,特别喜欢种树。进大门经过托尔斯泰称为“静穆而华丽的池塘”的大野塘,就像来到了森林一般,一股带着潮湿和树木清香的气味笼罩了我们——庄园里据传大部分树都是他手植的,那些越过百年的古树,挺拔的白桦,高大的橡树与大叶枫,还有枞树、菩提树,基本呈原始状态生长着,树干上爬满了青苔,间杂有灌木丛和茂盛的蕨类,松鼠跳跃其间,黄嘴寒鸦飞临阵阵,还可以听见啄木鸟的“笃笃”声。
托尔斯泰的故居是一个有着两层的、经过修整后比较漂亮的小楼,不过左右两边是一溜的平房。托尔斯泰的故居有我们常在他小说中见到的器物和生活场景,英式的老钢琴、贝壳盘、猎人钟、铜烛台,还有那些典型的旧时俄国农民的服装、马靴,给人的感觉也不过就是个乡村地主的奢华,而他的书桌、木椅、窄床,看起来则更像个苦行僧使用的行头,简朴得令人不敢相信,他在这儿生活?他在这儿写作?是什么样的冲动使他写下了三十卷之多的作品,并且思索着人类的道路,被他的同时代人称为“我们共同的导师”,“人类的指路明星”?
在他故居正对面的坡下和左面,都曾是他喂马的马厩——如今这儿仍在喂着马。他不仅喂马,还亲手盖房,耕种庄稼。马厩的门口,两个可爱的小孩估计是姐弟,在给一匹良种矮马刷毛,我走进马厩,有妇女搂着新鲜草料在给马们喂草,一股农村的马粪和草料混杂的气味充盈在马厩里。我在阴暗的马厩深处寻找着,似乎想看到那个喂马的写小说的老地主托尔斯泰伯爵。
往一个漫长的斜坡走上去,有一大块开阔的草地,从那儿传来了天堂般的乐声,原来是一群少女在练习演奏多少带点儿乡村教堂的音乐,这些一袭白色衣裙的少女,衣裙上有紫色的镶边,白色的帽子上有金黄色的流苏,少女们像天使一样美丽。她们的乐器挂在一个长方形的金属架上,有钟,有钢磬,一个中年妇女正在讲解,许多人在恭听。同行的告诉我们,她们是庄园组织的乐队,专门为国家级的贵宾演奏的。就在她们不远的地方,是一间茅草为顶的小木屋——那正是托尔斯泰出走的地方。
2
一个八十二岁的老人,他昏聩了吗?他患了老年痴呆症?这个倔老头子,他可以享受最优渥的生活,可是他什么都放弃了,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也许,他以一百年前的高寿(在俄国这个短寿的国度)再好好活下去,更加研究点养生之道,使生活更有规律,在大自然中散步,写作,以至最后老死在书房或者鲜花盛开的苹果树下,像一片落叶一样安详地告别这个世界,成为人们颐养天年的楷模,他不同样显得伟大吗?
可是,在一个风雪弥漫的、俄罗斯无比寒冷的冬日,他收拾起简单的行装,放弃了一切,像一个一无所有的流浪汉,踏上了凶险的孤途。可以想见在那旅客稀少、哐啷作响的老式火车车厢里,老托尔斯泰的目光是多么坚毅,又是多么凄伤迷茫。有人说他是负气出走的,我曾在一个法国人写的书中找到了这种说法,甚至那个浅薄的法国人这么议论道:“我们希望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解决夫妻间的冲突,千万别像列夫·托尔斯泰那样……”
这是1910年10月28日深夜。据记载,托尔斯泰在这天夜里听到了他书房里有人翻动的声音,他一看,是他的夫人索妮娅,他知道,她趁他不在时,在执著地寻找他的遗嘱。这使托尔斯泰大为光火,因此他痛下决心,离开这个家庭,他希望逃得远远的,他的想法是远去1067公里外的新切尔卡斯克。
这并非一时的冲动,以为是一个老人返老还童之举或是对婚姻不满的臆测是庸常人的想法。在他死后,人们发现了一封于出走之前他写给他夫人索妮娅的信,信中说:
“很久以来,我一直忍受着生命与信仰不尽一致所带给我的痛苦和煎熬……如今,我终于在做我长期以来一直想做的事情了:我要去了……人一旦进入到六十岁,就应该到森林中去……当我步入六十岁后,我就希望能够全身心地获得安宁和清静。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的生命、信仰和我的良心之间,就会出现明显的不一致。”
他还说:“请你理解和相信我,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我在家中的地位已经忍无可忍,我不能再在这种奢华的环境中生活……”
在出走的前夜,他在日记中写道:“不能再睡,我突然做出了出走的最后决定……夜,一片漆黑……终于出发了……”
与索妮娅的龃龉只是一个导火线,一个很大的导火线,但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原因。
就在这年的7月,托尔斯泰就秘密地拟好了他最后的遗嘱(他一共有五份遗嘱)。他在最早的两份遗嘱中都写明了“放弃作者权”。在另三份遗嘱中不知道他是否重提要放弃他的所有家产包括这个庄园,把它们全部分给农民,但是我所见到的这两份遗嘱都声称他无法接受他的家人因为他的思想而致富这种情况。让他的作品“没有阻碍地进入公共领域。”
他在距出走的前八日即10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
“一种至高无上的想法让我产生了巨大的痛苦。我想逃避,想就此消失。”
十三年前,即托尔斯泰六十九岁时,他就有一封写给妻子的信:“我的生活跟我的信仰不再协调,这早就使我感到痛苦,我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因此我已经决定现在要去做我早就想做的事情——出走。”这封信似乎与他出走前夜的信语调一样。
一切都是蓄谋已久的。
“巨大的痛苦”一定是信仰的痛苦,信仰由此带来的不能实现的痛苦——这便是家人阻止他放弃财产的企图。
可是,在他晚年的杰作《复活》中,他借主人公聂赫留朵夫之口已经再次阐明了他伟大的观点:
“土地是不可以成为财产对象的,它不可以成为买卖的对象,如同水,空气,阳光一样。一切人,对于土地,对于土地给与人们的种种好处,都有同等的权利。”
他甚至在这部作品中直言疾呼:我们这个社会“真理让猪吃掉了”!
他的信仰无比鲜明:阳光、空气、水、土地,属于社会的所有人,属于所有农民。
托尔斯泰曾说过这么一段话:“当人们有了恶劣行为的时候,他们总是为自己杜撰出这样一种世界观,根据这种世界观,他们的恶劣行为已不再是恶劣行为,而是不受他们支配的永恒法则的结果……它为一些人注定了低贱的地位和劳动,为另一些人注定了高贵的地位和享受生活幸福的权利。”
伟大的托尔斯泰在他的一生中,由一个曾经沉溺于酒池肉林中的阔少成为了一个道德圣人;由同情农民到完全将立场转向农民,使自己成为一个农民。他看穿了那个社会,除了沙皇的残暴外,还有资本主义的疯狂给农民造成的伤害。他认为先进的科学技术都是上层社会享受的,与农民生活没有关系。他说:“上层阶级的人们应当明白,他们称之为文明、文化的东西只不过是少数不劳动的人奴役绝大多数劳动者的手段和结果。”与其说他在《复活》中“气势磅礴地描写了人民的苦难”(草婴语),不如说他借那个拯救了自己的聂赫留朵夫之口,道出了他最后的信仰——这是终其一生和思想总结,是他探索了八十余年的真理,是普世原则。
当一个人回归了农民,他的想法必然会十分简单和天真。
可他的“回归”又只是一个梦想,一个与现实抵牾的冒险念头。虽然他一直以来就开始了成为农民的铺垫,比如减租息租,比如在庄园办了一所农民子弟学校,自编教材,亲自授课,比如与农民呆在一起,干所有农活。大画家列宾曾画过这位“农民”:短袍,腰扎宽皮带,手扶木犁,如果说不是那双鹰似的深邃的双眼和哲学家似的长髯,你一定会相信这是一个农民,一个老农,一个俄罗斯土地上平凡的老农。他总是在生活中和作品中叨念着农民的贫困和可怜,发誓把拯救农民视为自己的天职。可是现在他不得不只身出走,应该说,这是一次失败的出走,他最后没有看到那些喜气洋洋因为分到了他土地的农民的表情,似乎是某种宿命的象征,让他看到的只是无尽的风雪和铁轨尽头的迷茫的暗夜。
他因为年老体衰,受不了这样的风寒,发起了高烧,浑身发抖,只好在下一站——阿斯塔波沃车站下车,这场夭折的出走似乎从一开始就预示了它的命运。
好在,他当时已是大名人,车站站长认出了这个生病的老头子,于是托尔斯泰就歇息在车站的木屋里。当时,《俄罗斯言论报》恰巧有个记者经过此站,在站台上也认出了托尔斯泰,便很快向报社发回一份电报——是一则简短的消息:“列夫·托尔斯泰在阿斯塔波沃车站站长家,高烧40℃。”
他就要死了。就在此时,接到消息的托尔斯泰的家里乱作一团,夫人索妮娅因愧疚自己的(寻找遗嘱的)行为,又找到了丈夫留下的信,一下子跳进冰冷的湖里自尽,后被人救起,但索妮娅似乎不想活了,又使用了许多自杀方法,终不能成。
11月7日凌晨,决计不再回去的倔老头儿托尔斯泰,就死在了那个将千古留名的小火车站阿斯塔波沃。
3
在通往托尔斯泰墓地的左侧,是这位道德圣人亲手栽种的约四十公顷苹果林,走过苹果林,往左拐向一条更荒寂的路,走了约二百米,就见到在路边一块草坪中间,一个长方形的隆起的“土坝”,长满了柔软的青草,当地人告诉我们,这就是托尔斯泰的坟墓。
高大的树阴遮盖着这座坟墓,它的旁边是森林的景色。一个小小的峡谷可以看到溪水的走向,遗憾的是,它现在干涸了。但是苍苔和潮气依然缱绻在这里,阳光透过林隙小心地筛下来,野草在微风中摇曳,好像在轻声歌唱。
没有一丝托尔斯泰的痕迹,没有一丝人为的痕迹,墓碑、雕像、甚至一行字。没有,什么都没有。托尔斯泰在1895年3月27日的第一份遗嘱中写道:“我死在哪儿就安葬在哪儿,墓地要最便宜的。如果死在城里,那就用最便宜的棺材,像埋穷人那样。不要送花、花圈,不要发表演说。如果可能的话,甚至不要请牧师、不要做安魂祈祷……要尽可能地节俭和简单。”在他的1908年8月11日的第二份遗嘱中,他写道:“让人们绝不要在埋我入土时举行仪式。只要一口木制的棺材,由愿意抬棺的人抬到或运到峡谷对面的‘指定地点’……至少我选择葬身之地还是有理由的。”
1928年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拜谒此墓后,写过一篇美文:《世间最美的坟墓》。他写道:
“我在俄国所见到的景物再没有比托尔斯泰墓更宏伟,更感人了……这块将被后代永远怀着敬畏之情朝拜的尊严圣地,远离尘嚣,孤零零地躲在林阴里。”
小时候,托尔斯泰听他的哥哥说过,在你亲手种树的地方,你会找到上帝的魔杖,找到它,将会使全世界的人幸福。如今,他就躲在他亲手种植的枞树和橡树下,他找到了那根上帝的魔杖吗?
一个未能实现自己愿望的奇怪老头儿,一个地主,一个作家,一个高山仰止的圣者,他“得以安息的没有任何的东西,惟有人们的敬意。”(茨威格)
谁都不理解他,包括心怀叵测的东正教教会,在他去世的那年,开除了他的教籍。而瑞典的那几个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在肯定他的文学天才之后,却对他晚年的思想和行动感到匪夷所思,不可理解,就因为这个原因,剥夺了他当之无愧的获奖资格。还有他的亲人……
他如今还在地下抱怨吗?他会抱怨吗?不,他说,那些人应当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有罪,而他,“既不能惩罚别人,也不能纠正别人。”他说:“要永远宽恕一切人。”
托尔斯泰的墓就这样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了,他真的宽恕了所有的人,宽恕了这个不想宽恕他的世界。还有什么样的纪念碑能与这个小土堆媲美的呢?没有了。天空有多高,他的纪念碑就有多高,大地有多宽,他的纪念碑就有多宽。从过去,到永远,这块墓都将是世界最美的墓。当你走近,不由自主地让心提紧,经受一次难以名状的冲击——那就是托尔斯泰在简朴中凝聚出来的绝世的力量,让人们的心承受它的打击。
走出庄园,在对面朴素的小木屋餐厅吃了一顿俄式午餐——午餐的食谱全按托尔斯泰生前的喜好制订,也就是托尔斯泰喜欢吃的日常饮食。
两个面包,其中一片是黑面包;一小碗沙拉,内有洋白菜丝、洋葱、樱桃果和苹果片;一盘土豆烧牛肉;一碗罗宋汤,内有几片番茄、牛肉、鸡蛋花。然后是一杯浓酽清香的红茶。
吃过午餐,我在小摊上相中了一尊陶瓷的托氏半身像。我决定把他“请”回我的中国书房。我要小心翼翼地把它用衣裳包裹好,经受万里之遥的颠簸与摔打。
如今,这尊雕像安然无恙地摆放在我的书桌上,托尔斯泰那鹰似的、忧郁的眼神,蓬乱的大葫子,突出的前额和高耸的眉骨,似乎在注视着我,或者对我不屑一顾。他在想着什么呢?
我却想起了在那个风雪交加的阿斯塔波沃小火车站,在那儿踯躅的孤苦老头子,像一个乞丐的老头子,正是此人,正是他,农民托尔斯泰。在他的意识已经进入微茫和谵妄之后,他给他的儿子塞尔日喃喃地说着话。塞尔日俯下身去,把耳朵贴在父亲的嘴边,他听清了,他终于听清了,听到他的父亲在说:“我爱真理……我更爱真理……”
这就是托尔斯泰最后说的话。
托尔斯泰,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托尔斯泰,我知道了你为什么要像一个农民那么生活,我知道了你为什么想成为一个农民。我总有一天会理解这其中的全部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