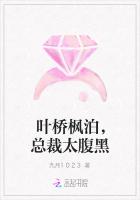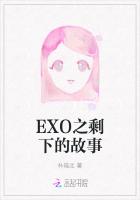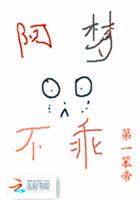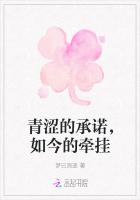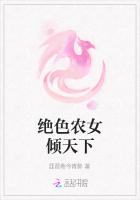作为70年代人中的一员,一个曾经的理想主义者,不敢说自己一直在坚持,甚至可以说是愧不敢言,但我不想放弃,在这个让我困惑、迷茫的世界里我不想放弃这最后一根稻草,不管它是不是能够救我。
走进书店,“新浪”出版的一本书吸引了我的目光,封面上的一行字赫然入目:70年代人,你们的理想还在吗?
打开书,目录上一篇文章的题目《拒绝和70年代人交朋友》更是刺人,翻到这篇文章粗粗一看,竟然把70年代人写成什么扮酷装炫,没心没肺所谓的“新新人类”了,对比我很不以为然,感觉那都是“八十年代新一辈”的事,与我们何干?倒是书中有段话我觉得比较中肯:70年代人可分上下两段,上半段的人大多恪守传统,责任感强,后半段特别是70年代末出生的人则大多接近我行我素的“新新人类”。(大意)我就属于这其中的上半段,一个曾经的理想主义者,但现在“你们的理想还在吗?”这句话却直撞我的心。
70年代出生的我是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和《社会主义好》等歌曲长大的,还有家里阁楼子弹箱中父母那些毛泽东时代的书,至今还记得那些英雄模范的名字:雷锋、欧阳海、麦贤得、王杰、蔡忠祥等,共产主义理想在我心中无比神圣,“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我最崇尚的道德。我偷偷地做些为老人送柴、为班上搭垃圾池之类的好事,虽然极不起眼却还生怕别人知道,并以此为快乐,甚至被一个同学欺负也决不还手,还要热情帮助她。
12岁加入共青团对于我是件铭刻在心的事件,当我小小年纪戴着团微走在学校,甚至走上街都能听到别人的赞叹时,心中那份自豪和激动的心情真的难以言表,共产主义理想在我心中愈加变得神圣,更加信仰“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奉献”。因着这份信念,我为自己选择了“人民教师”的职业理想,因为教师“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总之因为教师是最具奉献精神的职业。
15岁以后,在学习上一直很顺利的我开始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成功与失败的体验都刻骨铭心,“奋斗流汗血、得失笑傲然”成了我的人生信条之一,我开始懂得结果并不是最重要的。道德在我心中变得更加重要,以前是对作为学生的各个方面都力求完美,现在学习上似已不能,道德的完善自然在心中变得更重。“给永远比拿愉快”依然是我的人生信条,崇高仍然是我的向往。我关心集体,热爱劳动,这在现在高中生的意识中已经很淡漠,这还都没什么,当艰苦朴素,极其节俭的我给希望工程,给本校重病的同学大方地捐款时,却引起了小小的“风波”,周围同学议论纷纷,我不理会就是了,学校却让我接受采访并让我上台发言,还评我当优秀共青团员,在林校时甚至暗示我写入党申请书,我感到惊愕,继而一一放弃。要我说话时我说了,但不是他们期望的“爱心”之类的话,我觉得“爱”应该是个动词,而不是一个可以随时从口袋里掏出的名词,我只说了几句平常的话,因为我觉得这本身就很平常,如果再有什么夸耀那仅有的一点崇高感和快乐都会消失,所以我选择放弃,躲在老师的办公室里用写自己先进事迹的稿纸写了一封放弃的信。入党可以说是我从小就有的神圣向往,刚进林校未满18岁的我就曾偷偷地写过投进了学校的邮箱,学校也许没看到,但现在要我写倒让我决定在学校不再写申请书,并使我决心让这种神圣的向往成为激励我前进的动力。15岁以后的学校有了图书馆,从小酷爱读书的我像看到大海一样欣喜、激励,《便衣警察》、《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北方的河》、《蹉跎岁月》等小说则使我的理想主义情怀更加强烈,也许是受这些文学作品的影响,17岁的我开始梦想着一个人走向大西北,并且充满激情。
但到最后我所有的梦想都未能实现,虽然我还写了信给青基会给省林业厅,也到本市教育局去要求了,但还是大西北去不成,教师也未当成。当所有的梦想都破灭之后,我只争取到了最后一点选择的自由:不顾父亲的责骂、母亲的哭泣,没有想方设法留在县城,而是分配去了一个偏远的山乡,乡村是我最后的底线。
但工作单位是我不喜欢的行政机关,不过既来之则安之,其实我适应环境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很快我就习惯了那里的一切,只是因着理想的缘故无法忍受无所事事,心中常有种想在大山与乡政府之间搭起一座桥又不知如何搭的焦趵感。独自一人身处异乡,且身边也没有同学朋友,这在我是第一次,漏雨的小屋让我有一种深刻的无助感,同时也为此产生了一种成长的自豪感,但后来慢慢地焦灼感和自豪感都淡了。终于入了党,却没有了多少激动之情,在林校时不写入党申请书也因为想把这当作永远的追求激励自己,但朋友和老师都劝我入了党仍然而且甚至还能更好地严格要求自己,于是便写了,也按照程序加入了。
理想的激情在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中逐渐被淡忘,就像当初“被淡忘的团徽”一样,入党的誓言也常常被淡忘,而且我渐渐发现了乡村的天空也并不那么纯净,甚至我一直梦想的教师的世界也并不那么圣洁“光辉”,周围有太多我不理解的东西,我感到困惑、彷徨,从小形成的理想信念受到了强烈冲击,我甚至分不清谁是谁非,也许是我的思想观念太落后?但这依然无法排除我内心的不安与痛苦。于是,我学会了逃避,学会了随波逐流,想不清就不去想,“以回避现实来平息愧疚,以放弃立场来减轻痛苦”。
有人说这是一个远离英雄的时代,因此也远离崇高,我当然不敢苟同,但的确自己已很少感动,更很少去做让自己感动的事,有的事曾经觉得崇高,现在却觉得如此平淡甚至庸俗,成了一种形式,成了一种负担。媒体中的感人事迹似乎也很少打动人了,人们有的不相信,有的认为一定有什么目的,有的干脆就说“笨”,是真的“笨”的意思,而不是儿时学雷锋说的那种可爱的“傻”,老实真的成了“无用”的代名词,一切崇高似乎都被化解为虚无,至少被怀疑,曾经坚信的一切理想信念似乎都开始被怀疑,这个世界和我自己都变得“面目全非”。真有一种如临深渊,整个人被抽空的感觉。相对于职业理想的破灭,道德理想的破灭是更令人痛苦的,其中尤以价值观为核心的信仰理想经受剥蚀最令人痛苦,它对人精神的冲击是全方位的,其实这三者原本就是密不可分的。
原以为自己的根在乡村,离开乡村之后,我才发现自己虽然生在乡村长在乡村,在乡村工作了十年,但对乡村其实也是处于一种游离状态:一方面对于农民,尽管我对乡村泥土的气息和农民都感到很亲切,但我毕竟不是农民,无法与他们达到真正深切地认同;另一方面对于乡村干部,虽然我曾是他们中的一员,但我却无法融入其中。我实际上是在乡村的背景中游离于自我的世界里。当然对于城市我更加游离,但我发现城市中的人们原本就是游离的。
在这个自我的世界里理想被淡化,甚至是非都淡化,只有逃避的“宁静”。但是这种宁静真的是一种宁静吗?这种宁静又能持续多久?游离于城市,游离于乡村,游离于整个世界,我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这种“宁静”的世界又能给我一个怎样的家园?
十八岁那年,生与死的问题突然来到心中,从此无法摆脱对死亡的恐惧,便常常以此作为背景来思考生命的意义,特别是当理想淡化以后,自以为拥有了终极的视角,可是现在我发现这其实也是一种逃避。因为并不存在抽象的生命意义,而且这也无法代替理想,无法代替价值观的问题。现在的图书市场充满太多的人生感悟及所谓的成功指导书,大多宣扬一种“心态决定一切”的观念,的确给人鼓舞,但看看现实这其实是多么苍白无力,心态真的能决定一切吗?“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无动于衷”。“白手起家”的神话在倡导个人意志的同时,遮盖了多少社会问题?还有曾经盛行的“禅学”,生命的意义真的就在于此吗?其实不论生命的意义应该如何,价值观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只要你在生活中,你就必须面对。理想和信念也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当然它并不一定需要理论形态或者语言的表述,但它存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支撑着每个人的生命。记得有位同学给我的毕业留言中说我像北方人一样早熟、果断、有主见,对此一直心存疑惑,特别是参加工作以后,更觉得奇怪:我是那样的人吗?现在忽然有些明白了,年少时的我虽然幼稚莽撞,但因为有理想信念的支撑所以坚定、果断,不在乎别人怎么说,而如今的我虽然有人说“成熟”了,但因为内心的彷徨、逃避,所以就很少再有那份坚定、自信和果断了。
其实生与死的问题我虽然依然无法摆脱,但现在已很少想起,想起来也与从前的感觉不同,感觉对现实的生活并无多大影响,没了那种切肤的痛苦感,没了那种紧迫感、焦灼感,也许面对死亡的阴影,淡然也是一种摆脱?但如果这成了一种生命状态,又该是怎样一种悲哀?
高中毕业时有位同学(当然也是70年代人)在赠言本上写的人生信条是辩证唯物主义,理想是为了全人类的进步而努力,在所有同学中是很独特很醒目的,给我很深印象,但不知他现在是否还依然在坚持这个理想。
70年代人,你们的理想还在吗?作为70年代人中的一员,一个曾经的理想主义者,不敢说自己一直在坚持,甚至可以说是愧不敢言,但我不想放弃,在这个让我困惑、迷茫的世界里我不想放弃这最后一根稻草,不管它是不是能够救我。
对于不屈不挠的人来说,没有失败这回事。
——俾斯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