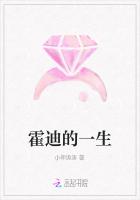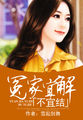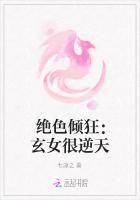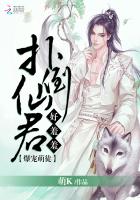编这本书的缘起,是要给刚入行的青年编辑们找一些可以借鉴的案例。我一直认为,编辑是一份和经验密切相关的职业,在技术革新覆盖绝大多数产品的时代,这份职业是需要手把手的传授及心甘情愿的自我揣摩的。
在一大堆出版人的回忆录或文集中,选出了书中这些文章。选完确定好这些篇目后,再来写这篇前言,那感觉就好比是一个已在路上的行者,面对刚开始出发的人,突然觉得光凭几句话几番注视,是说不清为什么上路,路上有哪些风景或陷阱的,只能默默地留下一本索引。在这本索引的背后,有诸多的故事以供挖掘。
本来,阅读一份尚未出版的作品,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然而,现在很难说会有多少人对编辑的工作发生多大兴趣了吧。就算身处出版业的人们,关注得更多的,也是卖点、市场、盈亏。我并非认为这些不重要,但那些影响图书出版的核心因素,渐渐变成了次要的、可有可无的东西。毕竟,在商业规则的考验下,那种手拿红笔、仔细审读手稿的对文字痴迷的编辑,早已让位给纵横市场、只会出版畅销书的企业家形象了。
但这也许只是聚光灯下的表象。正如郑振铎在本书《编辑是什么?》一文中强调的那样:“拿笔杆的人们,实在并不曾忘却他们的力量与责任。他们相信,人类社会之需要智慧也正和他们之需要食粮一样的迫切。”
那么,出版是什么?编辑是一份怎样的职业?随着时间的流逝,答案将会有不同的走向和可能性。然而,在所有的走向和可能性之中,有一些必将是核心的、炽热的、能一直鼓舞着向往这个职业的人们。它们是什么呢?
是的,编辑是需要耐心和技艺的。以书的出版为例,英国《卫报》上登过一篇《编辑是一门正在消逝的艺术》:作家米勒曾收到一封长达二十多页的编辑回信,信中“充满了绝佳的建议”,从年代错误、前后不一致到不恰当的语言运用。米勒采纳了大概80%的修改建议,然后再交给这位优异的编辑,并在接下来的四次校对中完善了书稿。“我完全被整个出版过程给鼓舞了,”他说,“我完全明白了为什么一本书从代理到出版商再到书店再到读者手中需要花这么长的时间了。我想有我这种疑问的人不在少数。”
是的,编辑也常常会在科技的嬗变中迷失。但一位有眼光的编辑,总能在这种变迁的同时感受到出版面临的机遇。当手机阅读、网络阅读席卷越来越多的读者和市场时,编辑该清楚,这是一场介质的革命,而非内容的死去。正如台湾出版人郝明义所说的那样,任何时代的阅读,都很难绕过“分享”“人性”和“社群意识”这些关键词。
是的,编辑是需要勇气的。若你读过胡愈之1932年在《东方杂志》上发出的关于征集梦想的史料,读过沈昌文先生回忆刊登李以洪《人的太阳必然升起》的故事,读过钟叔河先生讲述策划《走向世界丛书》的经历……也许便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沉思。在一篇好文章、一个好报道、一本好书的背后,出版人除了要有见识和才华,还要有勇气。他们要清楚,在提供阅读的内容时,将会与社会及历史发生怎样的碰撞。
于是我们能理解,一位有担当的编辑,却可能会遭遇风险。在缺乏民主的社会中,与责任相对应的正是风险。让我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挑出下面一段话来作旁证吧——《新莱茵报》的各个编辑的命运是这样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因在爱北斐特发表的演说而受到刑事追究;马克思、德朗克和维尔特,作为非普鲁士臣民,应该离开普鲁士;斐迪南·沃尔弗和威廉·沃尔弗要受司法追究:前者是因为没有履行军职,后者则是因为仿佛曾在旧有各省里犯过政治罪行;今天法院拒绝了把科尔夫交保释放的请求……
而在本书中,你也能隐约了解到一些编辑的坎坷命运。
除了这种风险,编辑面对的,也不总是鲜花和赞誉。对于20世纪最伟大的编辑之一——哈考特出版公司的吉鲁,最大的遗憾便是与《麦田里的守望者》失之交臂。吉鲁的上司雷诺看不懂《麦田里的守望者》,问:“这个霍尔顿·考尔菲尔德是个疯子吗?”雷诺和哈考特管理层还担心出版《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样一部叛逆小说,会影响出版社在教育界的形象(毕竟他们出版社的核心利益在教育类图书),便将书稿交给教材部审读,结果,教材部的结论当然是“不适合哈考特出版”。而吉鲁曾向塞林格保证,他一定会出版这本书,并握手为约。吉鲁后来离开哈考特,加入法劳·斯特劳斯出版社,担任主编,十五位著名作家也跟随吉鲁转到新社。谈到痛失这部影响巨大的文学作品时,吉鲁说,“我一生中从未这么愤怒和羞辱,这是我出版生涯中所受到的最大打击。”可以这么说,一个没有被拒绝过、没有对自己能力失望过的编辑,未必是一个完整的编辑。
是的,就是在这种碰撞中,编辑受时代精神的指引,也影响着时代精神的传播。例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等丛书,便为中国近代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文化繁荣的前提,除了产业政策的激励、资金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宽松的文化氛围。而这种宽松,不会是天赐的礼物,也不会是自然的产物,它源自于思想的奔突,依托于语言、文本的博弈和传播者的努力。毕竟,铁皮盒里的鲜花,若是缺乏阳光照射,生命力总是脆弱的。
而编辑,也许就是那个打开铁皮盒子的人。




![[欧洲]中世纪教育思潮与教育论著选读(上)](https://cdn.zi5.net/images/book/no.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