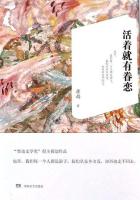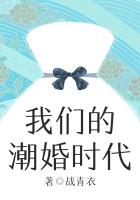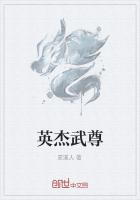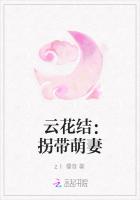随着文体学视角的介入,楚辞研究对其研究对象本身也产生了重新审视的要求。什么是楚辞?楚辞从哪里来?楚辞又到哪里去?即“楚辞体”的特性、渊源和衍变这一楚辞学的核心问题,又成为楚辞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我们搜集1995-2004年间论述“楚辞体”文体特性的有关论文,对其主要论点进行综述,以便对“楚辞体”文体特性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
总体来看,楚辞学者对“楚辞体”文体特性的认识,主要是从《诗》《骚》异同比较、汉代人对楚辞的接受(对辞与赋、赋与骚的文体辨析)、楚辞的“语体”特点(“兮”字句式及其音乐性)和“体性”特征(审美对象和审美精神等)四方面展开的。
一、从《诗》《骚》异同比较中看“楚辞体”的文体特性
从《诗》《骚》异同比较中确认“楚辞体”的文体特性,是“古已有之”的最直接明了的方法。虽然这种比较中并不侧重于对其文体特性的把握,但是通过这种比较,可看出《诗》《骚》的文体差异。
(一)关于《诗》《骚》的“体貌”特征
李诚《诗骚异同简论》:“若诉诸以直观形象,则《诗》恰如满身黄土、手足胼胝的农夫,踟蹰中土,依食黄河;而《骚》则宛若身披蘅芷、搔首弄姿的美人,娇骄山野,沐濯长江。”
(二)关于《诗》《骚》的“体式”结构
陈一平《诗骚辨异》认为:“《楚辞》属于吟唱体式,这是《楚辞》形式上的最大特色,正如《诗经》在形式上最大特色是属于乐府体式一样。”“《楚辞》中一些结构复杂、篇幅大、叙事性强的作品,整体构思上就有吟唱史诗气势磅礴、从容舒卷的特征。《楚辞》代表作《离骚》正是用这种体裁来诉说作者的悲剧身世、坎坷人生。其次,《楚辞》典型句式是句中句末常带有语气助词‘兮’、‘只’、‘些’等等。这些语气助词的作用正是便于吟哦时缓气和拖腔,使之易记易唱,具有吟唱史诗一唱三叹、抑扬顿挫的特征。”“再次,《楚辞》有许多篇章篇末加‘乱’,或者叫‘少歌’、‘倡’、‘重曰’、‘谇’等等。这种结构实际上是吟唱诗的一种标记……吟唱诗人往往在吟唱开始和结尾的时候用歌唱的形式,有音乐伴奏。中间大部分是用吟哦叙述故事,基本不用音乐或只用作节奏伴音。而‘乱’就是吟唱诗结尾的歌唱部分,以引起听众注意和归纳故事主旨。”“《楚辞》属吟唱体式,与民间联系密切,所以多有融汇民俗的作品,乡土气息浓郁,形式较自由活泼,句式容有参差不齐;《楚辞》是吟唱体式,吟唱场合不受限制,可以自我吟哦,所以创作目的多是发抒内心感情,不必通过诗歌进行社交,内容多真情实感,描写个人的内心世界。时间也不受限制,篇幅随内容而定,可以有鸿篇巨制。与音乐联系较松散,配器也不复杂,带叙事性质,故事性强,开始表现出与散文交融的倾向。”
李诚《诗骚异同简论》指出,《诗》《骚》在题材与主题的处理上很不一样,“《诗》的题材是‘当代’的,是取诸自作者身边的”,而《骚》由于“作者历史、文化涵养广厚,因而借以表达其情怀、展示其主题的题材,并不完全取于‘当代’,而还采撷自历史、神话。诗人‘当代’的思维和道德判断乃通过洪荒时代的天神地祗至传说中三皇五帝的种种表现,云蒸霞蔚一般折射而出”,这就形成“题材与主题上时空的反差”——即“悬隔”。“存在着巨大悬隔的文学作品的主题与题材如上所述呈二元状态,而不存在悬隔的文学作品主题与题材则呈一元状态。这最根本、本质的差异,导致了《诗》《骚》之间若干迥异面貌”。《诗》《骚》在文艺学、美学、社会学和伦理学意义上都有“巨大区别”:“从文艺学的角度判断,没有悬隔的文学作品在创作方法上,是写实的……而《骚》主题与题材之间的巨大悬隔正好决定其写作的非写实性。神话和历史传说纷纷被诗人驱遣至诗歌之中”;“从美学的角度判断,没有悬隔的文学作品,就审美的效果而言,给予审美者的感受是和谐、淳朴……而《骚》在主题和题材上的悬隔却予审美者以躁动的、不协和的审美心态”;“从伦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判断,没有悬隔的文学作品强调着强烈的群体意识”,但在《骚》中“诗人的家国乡邦之爱恰恰是通过强烈的个体意识体现出来的”。《诗》《骚》“间根本差异,乃在于主题与题材间悬隔的是否存在”,即作品内在的体式结构方式。“若从纯粹文学的角度看,这悬隔正是作品中鲜明的标志,判然划明了不同类型作品的界线,向人们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正是由于《骚》的主题与题材存在着巨大的悬隔,使其题材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若循此思路,单独将《诗》《骚》二者的题材加以比较,则从艺术生发的源流,从审美的角度,从人类文明和意识演化的程序看,《骚》当在前,《诗》应在后,文学史在此应该稍作回旋,指明这一点”。
(三)关于《诗》《骚》的“体性”特点
李诚在其《诗骚异同简论》中说,《骚》“活跃着远古血缘血亲社会的依稀影子和精灵”,而在其后的《诗骚异同再论》中进一步指出,“《诗》《骚》两者中潜藏着的宗教祭祀内容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者对中国文学迥然不同的影响,从而演绎出了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斑斓色彩”,“在《骚》中,宗教祭祀与男女情事是高度统一的,从文学的角度印证了其他典籍的记载,昭示了远古原始宗教祭祀的本来面目;而在《诗》中,宗教祭祀与男女情事却发生了分离,显示出文明时代宗教祭祀伦理化的发展趋势(或先儒删诗,意在教化,势不得不如此)。但文学本与原始宗教祭祀更有天然血缘关系,因为它们既同有着源自氏族或民族群体内心的深刻动机,也饱含着鲜活的个人情感体验;而后世走向伦理化的宗教祭祀却将原始宗教祭祀中深刻的个人情感体验加以摒除,而仅强调群体的福祉。正由于此,反映着原始宗教祭祀的《骚》保留了其文学本性,而歌颂着伦理化宗教祭祀的《诗》却步入了经典之途”。
(四)关于《诗》《骚》的“语体”特点
作为我国传统诗歌抒情语体的赋、比、兴,在《诗》《骚》的运用有同有异,论述己多。
黄桂凤《〈楚辞〉对比兴的发展》认为,“《楚辞》是在楚地民歌基础上的文人创作,仅就比兴的创作手法这一点来说,是对《诗经》的继承和发展”,《楚辞》“增强了比兴的艺术表现力,从而把它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由单纯的比兴发展为艺术上的象征,创造了完整的艺术意境”:(1)“诗人根据表达理想和情感的需要,选择了内美与外修结合的比兴意象,进行艺术的组合、融接而形成了人格理想、社会理想的象征体系”;(2)“对众多的比兴意象进行艺术组合与熔铸,塑造了完整的贴合诗人思想感情的意境”。2.“《楚辞》运用了新的比兴意象,扩大了比兴的范围,并呈现浓郁的浪漫色彩……总之,《楚辞》中的比兴材料由《诗经》的‘援物入诗’发展到天上地下、古往今来、自然社会均可成为比兴材料,扩大了比兴物象的范围,丰富了比的内涵,延伸了兴的意象,提高了艺术表现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楚辞》比兴的丰富性与多样性”。3.“比兴中融入了诗人独特的感情色彩,赋予了丰富的现实内容,使比兴向个性化、社会化方向迈进了一大步”。4.“《楚辞》中的兴由《诗经》中位于诗歌的发端的位置发展为自由穿插,展示了更为丰富的艺术表现力”。薛胜男《〈诗经〉〈楚辞〉比兴艺术之比较》认为:“《诗经》以兴的大量出现、比的抒情因素增长、用法纯熟巧妙标志着比兴的成熟,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则以比的泛化延伸、比兴构成象征体系并具有形象美和意境美标志着比兴的繁荣。”
二、从汉代人对楚辞的接受和认识中看楚辞的文体特性
从汉代人对楚辞的接受中看“楚辞体”的文体特性,是楚辞文体研究的重要视角。虽然这方面的文章重在探讨“楚辞”的初义、《楚辞》成书及其体例等问题,但也涉及汉人观念中的“楚辞”文体特性。
(一)认为“楚辞”是一种独具楚味的吟唱文体
蒋方《说“楚辞”之名——楚辞文体在汉代的接受情况刍议》则认为,汉代人意识中的“楚辞是一种楚地所特有的文艺形式”,其特点是“虽然无须配乐,却有一种特殊的诵读方式,非寻常的诵读可比,故非一般人所能”,所以,“九江被公所诵‘楚辞’应该既有出于楚地文人之手的书面作品,也有流传于楚地民间的口头作品,而不可能只是后来人们习称为楚辞的以屈原为首的文人作品”。董运庭《楚辞名称再考察》说:“辞与赋虽然同属于‘不歌而诵’的不入乐的作品,但二者的诵读方式是不同的。古代学有专门,游国恩先生考证,《楚辞》后来也变成‘专门学问’。朱买臣被召言‘楚辞’,九江被公应征诵读《楚辞》,这些都说明《楚辞》有专门的授受,西汉时能有地道的‘楚声’诵读它的人已经不多。”张强《“楚辞”的初义和能指》说,“楚辞”的“初义与发生在战国后期屈原、宋玉等人的文学创作无关,其初义所指有二:一是指朱买臣和庄助写作的辞赋;二是指他们用楚国方言诵读所写的辞赋”。
(二)认为“楚辞”是一种似赋而非赋的吟唱文体
董运庭《楚辞名称再考察》也认为,从《史记·酷吏列传》《汉书·朱买臣传》《汉书·王褒传》的记载看,“朱买臣等人讲诵的‘楚辞’就是屈原的《离骚》等作品”,但“同时又有‘辞赋’、‘辞’、‘赋’等称谓,这说明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辞、赋同类,楚辞就是赋。”如果“作进一步的仔细辨析,我们又可发现以下几个似乎不应忽略的问题。首先,在两汉时期,赋是对某一作家和某一篇或某几篇作品的指称,如‘屈原赋’、‘唐勒赋’、‘宋玉赋’、‘《怀沙》之赋’、‘《离骚》诸赋’、‘《九章》赋’等,却未曾有“楚赋”之称。一般说来,对汉人作品,也不直接指称‘贾谊辞’、‘枚乘辞’等等。可见,赋’与‘辞’所指略有不同,使用的场合也有所不同,二者不能完全替代或互换。其次,辞赋则通指楚辞与汉赋。因为辞、赋皆为‘不歌而诵’之体,故汉人每将辞、赋连称或混称”。
(三)认为“楚辞”是一种以屈原为中心、取向悲情的文体
田宜弘《汉人名楚辞漫议》分析,“楚辞命名之初应是专指屈原作品”,“从汉武帝诏命刘安作《离骚传》,到东汉章帝时班固、贾逵都作有《离骚经章句》,中经西汉后期刘向尊《离骚》为‘经’,显然,汉人心目中楚辞之核心是《离骚》无疑”。董运庭《楚辞名称再考察》也认为,从《史记·酷吏列传》《汉书·朱买臣传》《汉书·王褒传》的记载看,“朱买臣等人讲诵的‘楚辞’就是屈原的《离骚》等作品”。力之《从〈楚辞〉成书之体例看其各非屈原作品之旨》一文,对《楚辞》中之非屈原作品进行考辨,结果是:“《楚辞》中之非屈原作品,均代屈原设言。即这些作品中之‘我’,均为‘屈原’。”由此也可佐证汉人观念中的“楚辞”确系以屈原及其作品为中心的。
三、从楚辞的语体特点看“楚辞体”的文体特性
(一)“兮”字句:“楚辞体”的文体标志
楚辞的语体特点最突出的表现在“兮”字句式上。对“兮”字句的研究代不乏论,但从文体学的角度,非常清晰而精到地论述“兮”字句的文体意义,并将其确立为“楚辞体”的文体标志,由此展开对“骚体文学”(即“楚辞体”文学)的系统而深入地研究,郭建勋先生当其首功。这也是近十年来楚辞研究的重要成果。郭先生认为:“楚辞作为一种纯文学的经典体式,具有抒情文学的典范性、句式的独特性和灵活性、表现手法的丰富性,因而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不断扩大它的张力,向各体文学尤其是韵文辐射它多方面的影响。”因此,他提出“骚体文学”的概念,他说:“骚体文学也即楚辞体文学,它是以屈原《离骚》《九章》《九歌》等典范的原初楚辞作品为范式、以‘兮’字句为基本形式特征的作品。”屈宋辞作是其“本源”,“后世同类形式的骚体作品则是‘流变’”,“骚体文学便是以研究屈宋之后楚辞体作家作品和楚骚流变为已任的一个新领域”。“提出‘骚体文学’概念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仅把楚辞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而且是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式来研究,使楚辞学突破战国原初楚辞或《楚辞章句》所录的狭隘范围,以开放的学术态势,在一个宽广得多的时空视域里,去面对更为丰富多彩的研究对象”。“骚体文学”的研究对象,即“包括屈、宋而后的纯楚骚体、楚歌体和骚体赋三种体式的作品,以及楚骚与赋、乐府诗、七言诗、哀吊文、骈文、曲子词、戏曲等多种文体的相互关系,并涉及文体演变史、文学接受史、文人心态史等多个领域”。的确,诚如郭先生所说,“将屈、宋以后的楚辞体作品纳入楚辞研究的视野,不仅开拓了楚辞研究的新领域,而且对整个古代文学史的研究,也必然产生积极的作用”。
那么,根据什么标准来判定哪些作品属于楚辞体的范畴呢?郭先生提出:“‘兮’字句是楚辞体的本质特征,是区别于其他任何韵文体式的标尺……与其他韵文主要以句式的字数多寡、对偶与否作为判断文本的基准不同,楚辞体则以句中是否有特殊虚词为判断依据,这种情况是由楚辞体的特殊性和‘兮’字的特殊作用所决定的。”“‘兮’字具有特别强烈的咏叹表情色彩,构成诗歌节奏的能力,并兼具多种虚词的文法功能,衍化派生其他句式的造句功能,它作为一种文化存在,还反映了荆楚民族的自由浪漫精神和屈原的悲剧精神。兮’字在句中起了其他虚词所无法替代的作用,从而构成一种独特的意味”,诚如闻一多先生指出的那样,“‘感叹字确乎是歌的核心与原动力’,假如把‘兮’字省去,将是一大损失,因为‘损失了的正是歌的意味儿’,而‘意味比意义要紧得多’。兮’字所形成的这种‘意味’,正是前文所述的咏叹意味、节奏意味、楚文化意味以及与屈原身世相联系的悲剧意味。因此,兮’字成为楚辞体表征。而‘兮’字一旦在句中消失,楚辞体所独具的形式和‘意味’就不复存在,其区别于它种文体的特征也不复存在。”
郭先生的论述精到、精妙又精彩,可谓集“兮”字研究之大成,而为“兮”字研究之经典。
(二)“兮”字凝定为楚辞体构句成篇的基本形式
江立中《说“兮”》说,“‘兮’字并不是楚地民歌独有的语气词,而是先秦时南北各地民歌广泛使用的一个语气词”,“‘兮’在古文中主要用作语气词,多用于句末,亦可用于句中”,“‘兮’字与其他语气词通用的情况,在《诗经》中也很多”,“与《诗经》的‘歌’诗不同,诵诗’……《楚辞》却已经形成了构句、成篇的基本形式。因为它不需要合乐歌唱,所以它在运用语气词时,就同《诗经》完全不同了”。“《骚》把《风》中用得极多极灵活的语气词‘兮’字,引入《骚》中,并把它发展成《骚》在语言上最明显的标志,凝定成两种固定的基本形式,还赋予它以其他不同语气词的语法功能”。“楚辞学习《诗经》,便是把‘兮’字凝定成一种构句的基本形式,创制出楚辞诗体”。
(三)“兮”字与“楚辞体”的音乐性
楚辞能否“歌”之?这是楚辞文体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一般认为,楚辞在总体上属于“不歌而诵”的文体,这也是汉代人将其划归赋体文学的主要原因。但它又是诗体文学作品,故将其定位于“诵诗”,以与《诗经》的“歌诗”相区别。但最近十年,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其中主要是从楚辞“兮”字句式的特点出发,论证“楚辞体”的文体特性之一,在于它的可“歌”性,即音乐性。
周秉高《“兮”字与楚辞的音乐性》不仅论证了“秦汉之际用‘兮’之诗可以歌唱……楚辞大量用‘兮’是可以歌唱的标志”,而且进一步指出,从楚辞中“兮”字的分布可以看出“楚辞各篇的曲调,彼此也不完全相同”,“楚辞中‘兮’字的分布有四种情况:句中、单句末、双句末或少‘兮’无‘兮’。句中式’……歌唱时逢‘兮’则气出而扬,达一高潮。此为《九歌》标准式,歌唱时可能呈‘安歌’、‘浩唱’、‘展诗’和‘容与’之状。单句末式’……‘兮’字两侧文字多、音节长,歌唱时大概呈‘长言’、‘咏叹’之状。双句末式’……唱时,繁音促节’,但毕竟‘兮’字作结,句末飞扬,余音袅袅,歌声显得尤其悠扬有力。如《论语》形容‘《关雎》之“乱”’那样:‘洋洋乎盈耳’。少‘兮’无‘兮’式,需作具体分析。《大招》和《招魂》中‘兮’字很少,但双句末有大量的‘些’字或‘只’字来代替,起到了‘兮’字同样的作用,因此歌唱情况大概与‘双句末式’相似。《天问》373句,无一‘兮’字,或许不能歌唱,或许也能歌唱……其形式大概与《大雅》和三颂相似:缓慢、深沉,表现出一种郁悒、凝思的情态。”
郭杰《从“兮”字用法看楚辞〈九歌〉的音乐特性》指出:《九歌》中将“‘兮’字置于句腰的独特句式,并非单纯的语言现象”,“‘兮’字置于句腰(而不是句尾)的根本原因,只有着眼于其音乐性底蕴,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九歌》是“源于荆楚祭神乐歌”的,“为适应宗教祭祀的神秘性质,不仅要求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表现形式,且在实际活动中,其形式往往是乐调缓慢、舞姿舒展的,因为只有通过迂徐、舒缓、悠长、凝重的节奏,才能更充分地创造出庄敬、肃穆、雍容、虔诚的气氛,从而顺利达到沟通人神、祈求驱灾赐福的根本目的”,所以,“从乐舞节奏上看,《九歌》与《周颂》一样,其表演也是非常迂徐缓慢的。当然,《九歌》节奏缓慢的音乐特征,不像《周颂》那样,体现为没有韵脚、篇幅简短等,而是通过‘兮’字置于各句之腰的外在形式得以体现的”。另外,“《九歌》各句尾虽无‘兮’字,亦必出现一次拖音。这样,连同句腰的‘兮’,《九歌》每句均出现两次拖音,无疑延长了演唱时的音乐节拍,产生出迂徐宛转、缓慢舒展的节奏特征,从而与丰富多姿的舞蹈动作达到了和谐统一。这一切,都与《九歌》中‘兮’字置于句腰的特殊用法密切相关,而其根本原因,则蕴含于作品本身的祭神乐舞的性质之中”。
与郭杰先生从“兮”字用法看楚辞《九歌》的音乐特性是“节奏缓慢”相反,李炳海《楚辞语词与楚地歌舞的关系》通过对屈原作品运用语气词的三种类型的分析,指出“骚体作品具有旋律急、节奏快的特点”。“春秋战国是社会转型期,于是,郑卫之音、激楚之声而取代雅颂之乐,声乐风格由舒缓变为明快”,“楚辞最初由楚地歌谣演变而来,与此相应,它的节奏旋律带有所脱胎母体的特点,其具体标志就是语气词的运用有别于《诗经》的多数作品”。李先生认为,“根据诗句长短来判断演唱时的节奏旋律如何,并不是科学的方法,经不起检验和推敲。从古今中外的艺术实践来看,乐曲的缓急与歌词句式的长短关系不大。歌词句式长演唱时未必舒缓,短句子歌词演唱时未必急促,有时倒可以见到相反的情况。因此,根据歌词句子的长短去推断《诗经》和楚辞演唱风格的缓与急,那是误入歧途,是被文本的表面形态所迷惑。按照这种研究方法而得出的《诗经》明快而楚辞舒缓的结论,那是研究者阅读、吟诵作品时的体验,而不是古代演唱时的实际情况。把阅读、吟诵时的感受和古代演唱时的场景区别开来,才不至于只注重句式的长短而忽略音乐的规律”。
许晓林《巫·舞·兮》则认为,“《楚辞》中‘兮’字的运用,并不是一种‘创造性’行为,而是适应歌乐需要的自然表现”,“是由《楚辞》的文化氛围巫风歌舞所决定的”。“‘楚辞’大多是配合楚乐的歌辞,是南国巫风舞风催化的产物”,“‘兮’字的训释,与其说‘语气辞,读如啊’,倒不如解释为‘衬声字,读如啊’来得更为全面。楚辞中频频出现的‘兮’字,使楚辞显得别有情味。浪漫的歌辞,加上悦耳的音乐、美妙的舞蹈,诗、乐、舞‘三位一体’”,形成一种楚国特有的审美情趣。“宣帝时,能够还原楚韵味的,已寥若晨星,士人能‘为’《楚辞》,便会受到朝廷的器重。这里的‘为’,并不是‘诵’,也不是所谓的‘吟唱’。用楚语诵读《楚辞》,沅湘雅士,皆可为之。以楚语‘吟唱’《楚辞》,江汉流域,不乏其人。这里的‘为’,当是‘歌唱’。正因为是‘唱’,所以到了隋朝,能‘为楚声’并‘音韵清切’者,已成凤毛麟角”。
郭纪金《“诵”字的音义辨析与楚辞的歌乐特质》指出:“歌乐结合是中国古典文学在发展中形成的特色。楚辞’就是楚人的歌辞,具有可歌性质。只因证明楚辞为乐歌的文献不足,人们误以为楚辞只能供念诵,而不可歌。”该文“从探讨‘诵’字的音义和功用入手,着力辨析:(1)读音为cong的‘诵’,用为动词,其确切意义是击节歌唱,学‘诵’者必须严格从师,反复训练;(2)读音为yong的‘诵’,用为名词,是兼备歌词与曲调的一种文体,屈原作品的文体原本叫‘诵’,从而确证楚辞是用于歌唱的歌词”。他的《楚辞可歌刍论》一文则从五个方面论证楚辞的可歌性:“(1)从‘为楚辞’、‘辄为歌颂’等记载论述汉代演唱楚辞之风甚盛。(2)从‘春诵夏弦’、‘召见诵读’、‘朝夕诵读’等材料,论证‘诵读’即‘歌讴’,实关声乐,与朗读有异。(3)从‘压按学诵’、‘以声节之’等材料论证即使在‘不比琴瑟’的歌讴中,也必须依循音乐旋律,击‘节’而唱。(4)‘乱声’和‘乱辞’是楚辞可歌的内证。(5)《毛传》‘不歌而诵谓之赋’的含义是:不弦歌而唱诵的方法,就是赋。诵’或‘赋’的时候,要‘依声节之’,或‘点按’而唱。”“楚辞即楚人的歌词,和《诗经》、汉乐府一样,具有可以歌唱的特质”,“楚辞作品,可分‘歌篇’、‘诵篇’两大类。长期流行的楚辞不能歌(或以为其主要作品不能歌)只能‘诵’(口念,朗诵)的说法是应当抛弃的传统陈说”。
王小盾《中国韵文的传播方式及其体制变迁》则认为,“楚辞体的结构特征和语助特征来自相和歌唱”。“相和歌是先秦两汉最流行的艺术歌唱。它包括三种方式:一是以两种歌调彼此相和,二是以无实义的音段与正歌相和,三是以器乐与人声相和。前者即上文说的兴歌,后二者又称‘引和’和‘弦歌’。它们在楚地都有广泛的流行”,“这些歌唱特点是器乐形态的反映……乐器作为音乐的传播手段,往往决定了区域音乐的一般风格。例如瑟、琴、竽、笙等乐器,便使楚地音乐具有节奏舒缓、以语助词为音乐重点的特色”。“楚辞多用“兮”字的特点,从音乐上看,乃反映它节奏舒缓,多用衬腔与应和之声;从文化上看,则说明中国南方祭祀仪式秉有不同于中原的特殊风格”。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王峰的《楚辞、巴歌与新诗》一文,他将楚辞“兮”字句提升为汉语诗歌的重要形式“虚字格”。作者在与国外诗歌“轻重格”、“长短格”的比较中,确认“符合汉语特点的诗歌形式”是兩种:“一种是以楚辞为代表的虚字格,另一种是以唐诗为代表的平仄格。”作者指出,“虚字格”的突出特征是音乐美,“平仄格诗歌在音调的和谐方面可以说达到完美境界了”,“楚辞在音乐美方面,其节奏比唐诗悠扬婉转,其旋律比唐诗自由随意”,也成为种经典文体。“在最典型的虚字格作品《离骚》中,虚字的主要用途有三种:一是用虚字作句腰;二是用虚字加强不同的语气;三是用虚字构成不同的句式关系”。虚字的大量应用,造成“一种短长、短长的节奏,虚字短,实词长。整篇长诗吟唱起来,有一个大致统一的节奏。由于虚字不同、字义不同、用法不同,构成的句式关系也不同,所以大致统一的节奏并没有给人呆板的感觉”。“四句一节是虚字格的标准结构,那么那作句腰的虚字必然四个一组……句腰整齐地将诗句分隔成两部分,由于句腰的位置基本相同,所以参差不齐的字数组成的诗句节奏仍然是整齐、铿锵的。《离骚》长达373句,每句字数从三字到九字不等,却并未给人以散漫无纪的感觉”。
这些对楚辞可歌特性的研究,突破了传统认识,值得学界重视。
四、从楚辞的“体性”特征看“楚辞体”的文体特性
文体研究虽然主要是揭示文本的形式特征,但“由于文本自身的形式与内容具有不可分离性,决定了特定的话语形式总是反映着特定的审美对象,涵蕴着特定的精神结构”,所以,学者们在研究楚辞体的句式特点、音乐特性的同时,也注意研究楚辞体的“体性”特征,因为“任何文体都是一定的审美需要的产物,也是适应一定的审美需要的”。如刘勰《文心雕龙·定势》所说:“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的确,如果只是以“兮”字句作为“楚辞体”的标志,那么楚辞与楚歌、楚辞与骚体赋就无区别可言。所以,文体研究不能忽略文体的“体性”特征。
潘啸龙《“楚辞”的特征和对屈原精神的评价》指出,“倘若只将这些形式的因素视为‘楚辞’的特点,还未免是皮相之见”。他认为,“‘楚辞’之所以称‘楚’,最重要的乃在于它的情调、思致和审美取向,带有鲜明的南楚特点”。楚辞虽然“带有了既与中原文化灵犀相通的精神气质”,但更有“在声情、风调、审美取向和思致等诸方面迥然有异的南方特色”:“‘楚辞’多‘书楚语,作楚声’,具有北方人所不易诵唱的‘清切’音韵,此其一。楚辞’的表现色彩,受江南山水的濡染和‘巫风’对色彩的神秘观念影响,而带有魂奇富艳的特征,此其二。由于神怪观念的流行和巫风那‘神游天地’的习俗影响,楚辞’的构思往往‘上薄旻天,下极黄壤。山川磅礴,巫鬼绣错。鞭电驾螭,阴阳百出’(清人杨金声语),带有‘凿空不经人道’的浪漫奇思……‘其思甚幻’,此其三。楚辞’的作者,无论是屈原还是宋玉,都是具有进步思想的贤人志士,但又处在朝政昏乱、国家危亡关头,或遭放逐,或遭压抑,这又使‘楚辞’的情感表现,几乎都带有深切的‘忧患’感,及强烈的不平和愤懑。骚人之文,发愤之文也。雅多自贤,颇有狂态’(裴度《寄李翱书》)。其审美取向,大多不同于《诗经》的‘温柔敦厚’和儒家的‘中和’、婉曲,而表现为狂放、激烈和悲亢,此其四。可见‘楚辞’虽然是一种新的诗体,但总结其特点,则必须联系它的实际作品,对上述四点作综合考察,方能抓住它所区别于《诗经》的独特风貌。其中最重要的,除了形式上的特点外,恰恰是其表现色彩、浪漫奇思和忧愤、狂放诸特征。这些特征均与独特的南楚文化背景和楚国的特定时世相联系,与屈、宋的遭际和情怀相交织,而同时呈现的。失去了这种联系,也就没有‘楚辞’。这也正可解释,为什么‘楚辞’的传播始于汉代,而其衰落也恰恰是在汉代。”
何念龙《论楚辞体的内在特质兼说楚骚传统》一文中说,“宋人黄伯思对楚辞体特征的论说,只是对这一文体语言外壳的描述,未能涉及问题的本质。楚辞是一种内容和形式密切相关的特殊文体,而浓烈的抒情性则是楚辞体最突出的本质特征”。该文“从情感内涵、情感特征、抒发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具体解析,同时还从文学史的角度对楚骚传统展开论述,认为爱国主义文学传统、‘士文学’传统、‘骚文学’(骚体诗形式)共同构成了楚骚文学传统”。他指出,“按一般文学理论的提法,文体或作品的体裁属于文学形式的范畴。一般说来,某一种文体只是表现内容的载体,文体并不能决定内容。我们可以说某种文体比较适合于表达某方面的内容,如诗歌便于抒情,小说长于叙事,但不能说某种文体只能或必须表达某一特定内容。这就是说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没有固定的必然的联系。然而楚辞这一文体却不同,它有着不同于当时其他文学作品的特有的内在精神,以及由这种内在精神所形成的对当时和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传统。这是楚辞这一文体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现象。具体说来,它既不同于先秦时代已有的一般意义上的诗歌(如《诗经》)、散文(如诸子或历史散文),更不同于后世作为新文体的小说(如魏晋或唐人小说)、戏剧(如元代杂剧或明人传奇)。相对说来,在这些文体中它们所要表达的内容是自由的不确定的。然而楚辞这一文体却不然,我们可以说这一特殊文体从它诞生的那一时刻起,其内容和形式便形成了紧密的关联。一个显著不争的事实是:从屈原直到屈原以后楚辞体的继作者所形成的传统来看,几乎所有楚辞体的作品都有相同或相似的内涵。这一现象说明:楚辞这一种文体并不像其他文学体裁如诗歌、散文、小说、戏剧那样什么内容都可以表现,而是往往具有特定的表达内容,即楚辞这一文体不仅有独特的外在形式,同时也有特定的内在精神,古人已有人注意到这一现象。东汉王逸在论及‘楚辞’这一名称的来由时曾说:‘至于汉兴,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指屈原之作),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辞”。’‘咸悲其文,依而作词’,说明他已隐约看到楚辞体的相同内涵。明人陆时雍在《楚辞疏·楚辞条例》中说:‘自屈原感愤陈情,而沅湘之音,剏为特体。其人楚,其情楚,而其音复楚,谓之楚辞,雅称也。’”“浓烈的抒情色彩是楚辞这一文体内在特质中最为突出的特征”。“当然,所有的诗歌都可以说是抒情的,但对于楚辞,如果仔细分析,就不难看到其中所抒之情又有自己特定的内涵,这便是激烈的爱国之情和深沉的身世之感,屈原诸作是这两方面的最突出的代表”;“就情感特征看,屈原诸作所抒发的情感具有热烈深沉、萦回反复的特点。读屈原作品,常常使我们感到其中的情感如同奔腾的大河汹涌澎湃,不可遏止。《离骚》《九章》自不必说,即使是祭祀乐曲《九歌》,从中也不难看到抒情热烈深沉的特征”,“同时屈原诸作中的抒情往往是回环往复,一唱三叹的,这就使得情感的抒发既淋漓尽致,又动荡深沉,给人回肠荡气之感。在这方面《离骚》表现得最为突出”;“从情感的表达方式看,屈原诸作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或直接倾诉,直抒胸臆,兴会淋漓,明朗畅达;或借助比兴,美人香草,象征寄意,含蓄蕴藉;或驰骋想象,天上人间,昆仑四海,飘忽往来。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表现手法常常是在一篇作品中交织运用,相得益彰。如《离骚》就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
柯伦《论〈楚辞〉强烈抒情性及其文化渊源》则指出,楚辞“强烈的抒情性”主要表现于“心理描写揭示精神矛盾冲突的戏剧情节;借古代神话和历史人物诉说内心痛苦的抒情方式;怒涛式的语言旋律”,而“其文化渊源,在巫术文化”。马悦宁《楚辞体美学风貌阐释》从“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三方面阐释了“楚辞体的美学特质”,同时也指出,“楚辞体的美学特征除上述三点外,还有一点值得重视,那就是强烈的抒情特征……‘言志抒情’是楚辞体的一个重要特征和优良传统,”前人“几乎将‘悲壮激烈’当成了楚辞的专利”。
此外,有关楚辞体文体特性的研究,除了上述的总体研究,也有对《天问》《招魂》《大招》和《九歌》等文体特性的辨析。如褚赋杰先生1995年发表的三篇文章:《论〈九歌〉的性质和作意》《论〈楚辞·九歌〉的来源构成和性质》和《屈原〈九歌〉文体研究》,对传统认为《九歌》是供祭祀典礼用的祭歌(即供祭祀典礼上演唱的歌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九歌》是“屈原创作的一组赋咏祭事的诗,按其内容来说,可称为‘祭事诗’”,但是,“由于描写的对象大都是当时由巫人扮演的诸神歌舞的场景,作者则既记其故事,又兼录其某些唱词,当然也有诗人的抒情,这样一来,抒情主体和抒写对象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称代词和口吻,往往兼杂而出……正是由于诗人表现手法的这种特殊性,给我们带来辨析《九歌》性质、文体的困难。但我认为至终只能说它是一篇‘祭事诗’,而不是祭歌或戏剧”。王琳《试论屈原〈九歌〉为“祭事歌”》也认为《九歌》是“祭事歌”而非“祭祀歌”。
当然,从祭歌或戏剧的视角研究《九歌》,仍然是主流。如王廷信的《〈九歌〉中的戏剧扮演》(《文艺研究》2002年6期)、黄士吉、黄鹤的《论古代歌舞剧〈九歌〉》(《大连大学学报》2003年1期)和李光荣《彝族歌舞与闻一多〈《九歌》古歌舞剧悬解〉》(《民族文学研究》2002年1期)等。王廷信《〈九歌〉中的戏剧扮演》认为:“楚辞《九歌》反映了郊祭与社祭的混杂现象。屈原在改编过程中,不仅基于郊天歌辞,而且基于社祭歌辞。透过《九歌》,我们可以看到,《湘君》《湘夫人》《少司命》三者所基于的祭祀行为因扮演属性明显,从而体现出一定的戏剧特点,可以从中看出戏剧之萌芽。其他诸歌辞虽则亦可反映出一定的扮演因素,但多为请神唱述之辞,戏剧性并不明显。从现存文献来看,楚辞《九歌》所体现的楚地娱乐与扮演特征比中原地区的宗教祭祀明显,但戏剧艺术要直接从中发生还十分困难。”
姚小鸥《〈天问〉意旨、文体与诗学精神探原》(《文艺研究》2004年3期)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证明,从文体上来说,《天问》是史诗式的哲理诗”,对传统认为《天问》是以“问句体”写成的“咏史诗”的观点进行了拨正。
莫道才《〈汨罗民间招魂词〉的程式内容及其对〈招魂〉、〈大招〉研究的启示》(《民族艺术》1997年2期)和张兴武《〈楚辞·大招〉与楚巫文化》(《西北师大学报》2002年1期)对“二招”文体进行了研究。
五、小结
综合言之,关于“楚辞体”文体特性的研究,主要是从《诗》《骚》异同比较、汉代人对楚辞的接受、楚辞的“语体”特点和“体性”特征四方面展开的,并已成为楚辞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从楚辞的“语体”特点确立“楚辞体”的文体特性,并由此展开对“骚体文学”传统的系统研究,从“清流”中去“探源”,这是近十年关于“楚辞体”文体特性研究的重要成果。但是就目前的研究趋势看,用清晰的文体形态学的思路对“楚辞体”文体特性作出层次谨严、系统全面而又能成共识的研究,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争鸣和辨析。李中华、龚贤《楚辞的文体界定与文体渗透》一文,对近十年楚辞体文体特性研究思路进行了总结和拨正,也给出了今后楚辞文体研究的指导性意见。该文指出,“楚辞在当时及后世,有多种的名目称谓。大体而言之,一曰歌、二曰诗、三曰赋、四曰诵、五曰辞(又作词)、六曰骚、七曰赋、八曰文”,这“显示着对于楚辞的文体性质有着不同的认知理解”,“楚辞的文体,不能一概而论:其中包含诗歌(如《九歌》),可唱亦可诵;也包含只能有节奏朗咏的诵(可配乐,亦可不配乐)”,“楚辞是一种介于韵文与散文之间的特殊文体。它不仅句式可长可短,用韵宽松灵活,可以配乐歌唱,也可以有节奏地咏诵;可用来抒情,也可以用于叙事。可以视之为诗歌,也可以称之为文章”,但是,“二十世纪以来,学者因受到西方文体分类观念的影响,以为非诗即文、非文即诗,从而将楚辞简单的界定为诗歌,忽视了它兼有‘文’的性质,这就造成了广泛的误解”。“楚辞是一种特殊的文体。这种特殊性使得它对于中国文学的各类文体发生了特殊的作用。在古代文学的园地中,楚辞像一个光源,它的光芒照亮了各个文学领域。它又像一条支脉纵横的江河,滋润了整个中国文学的原野。楚辞不断地向外辐射出光和热,渗透进其他的文体之中,促进了不同文体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它的这一文学特质,应该引起学者的思考与重视”。因此,今后对于“楚辞体”文体特性的研究,恐怕先须从“非诗即文、非文即诗”的西方文体分类观念中跳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