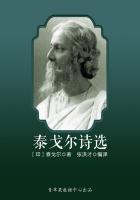我也记不得是在哪本书里读到过的了,书名忘了,作者忘了,但里面有一句话,我却一直未忘。书中的一位主人公说:“我们都是土地的儿子!”人和土地的关系,再比不上这句话更贴切的了。
这句话在那本书里,究竟是用来褒扬人对于土地的感情呢?还是嘲讽耕作于土地的人,那种不可免的农民的狭隘呢?也回忆不起来了。或许两者都有,或许两者都不是,但我,也怪了,我却牢牢地记住了这句话。我相信,人对于土地,总是有一种摆脱不了的归属感。双脚站在土地上,那种实实在在的滋味,平时是不大感觉得出来,只有在你所乘坐的民航飞机,降落时刻,轮子擦着跑道的那一瞬间,体会是最深刻的了。每次到居住在高层建筑物里的朋友家串门,望着窗外的蓝天,站在阳台上往下俯视,心里总有些玄玄乎乎的不踏实感。
因此,也许我勉强可算是个土地的儿子的缘故,如果给我一份选择的权利,高层建筑和普通楼房,宁肯更接近地面一点。我在北京城里,居住的年头也不短了,对那些走来走去的大小胡同,渐渐地看惯了,尽管有的大杂院,条件可说是十分糟,但是到了春天,院里该绿的,全绿了,该开花的,全开了。到了秋天,该结果的,全结了,该落叶的,全落了。一年四季,在你眼下的土地上,实打实地给你可以把握得住的那变化着的一切,使你觉得有一份充实。
多好!别人是否这样看,我不敢说,反正,我觉得好!
有时候,从胡同里走过,那一阵阵槐花的香味,并不因为这院里住着的多是些平民百姓,而不好意思飘出院墙。那一串串脆枣,那一个个红柿,绝对不怕张扬地,映入过路人的眼帘。这时候,我就很羡慕居住在小院里的,有块空地的人家。
终于,三次换房,从三楼而二楼,从二楼而一楼,而且,有了一个小院。虽然,位于楼房的北面,大部分时间被遮住了阳光,然而,那是一个当真的小院,四周有矮墙围着,其中有一块可以种些什么菜和豆、长些什么花和草的土地。刚刚搬来后不久,就在集市上一位老乡手里,买了两棵石榴栽上了。说是一种甜石榴,每个能结得碗那么大,放心吧,两年开花,三年吊果,绝不怕肥,你就侍弄着,准保你不能失望的。过了一年的春天,由于我们采取了防寒措施,那两棵石榴未被冻死,活了过来。于是又买来几株据卖者介绍说,是很不错品种的玫瑰香葡萄插在土中。
我之所以热衷于葡萄和石榴,当然是因为不需要太复杂的栽培技术。所谓园艺,是一门艺术,我何尝不想在小院里,有几竿湘妃翠竹,枝叶掩映,一年四季,绿意盎然。要是再有一兜西府海棠,到花盛季节,引来飞舞的蜜蜂蝴蝶,那必定是赏心悦目的。但我一位有坐北朝南小院的邻居奉劝我,他先声明,决无打击我的积极性的意思,阁下这院子太背阴了,什么都长不好的。别瞎费力气,别指望,别想得那么美好,朋友!
这位直言无讳的朋友,说罢走了,可是,我已经种下了石榴和葡萄,总不能弃之不顾吧?何况在我印象中,一直还保留着对于远祖来自中亚的,这两种果品的最美好的回忆呢?那是几年前在访问前苏联时,到了格鲁吉亚,在美丽的梯比利斯山城,吃到了真正的本乡本土的石榴和葡萄。虽然,现在那里烽烟迭起,厮杀不已,也想不透那样甜美的土地,难道一定要浸透了鲜血才能肥沃吗?
平心而论,我所吃过的石榴,很难称之为水果的,除了一层薄薄的皮,便是涩口的籽核。一粒一粒地吃,费事;一把一把地吃,涩得嘴都张不开。在那里,我讶异的不是它的大小,而是剥开来,每一粒籽实都像一注清冽甜美的甘泉。好像不含有引起口腔酸涩感的单宁质似的。于是产生一种奇怪的想法,也许吃的不是石榴吧?葡萄那就更不用说了,格鲁吉亚是葡萄之乡,诗人叶夫图申科陪我去过一处古老的酒窖,品尝过窖藏了二三十年的我们中国也许该叫做陈酿的葡萄酒。我去过称作高加索山脉的许多地方,每到一处,端上来款待客人的,就是各式品种的葡萄。我一点也没有妄自菲薄的意思,那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好的葡萄。
于是,当在小院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时,无论如何,总是被格鲁吉亚那残留下的记忆所诱惑,一想起来,仿佛仍齿颊生香似的。可是,石榴虽然活了,但总是很孱弱。葡萄拉蔓了,也上了架,始终恹恹地没有生气。按懂行的人指点,枝也剪了,肥也施了,虫药也喷了,杂草也除了,根部的砖头瓦块也捡走了。一年过去,两年过去,三年也过去了,真让人失望,一点也不让人兴奋,石榴非但没挂果,连花也不开一朵,葡萄结过几嘟噜,酸得连尝一尝的勇气也没有。
就在这期间,靠墙根的水泥房基处,长出来一棵泡桐。后来,才明白,这是在盖房子打地基被砍伐了的大树,根部未刨掉又萌生出的新枝。长势很猛,也就一年功夫,蹿出一人来高。有人说,你要不弄掉的话,有这么一个抢嘴的家伙,你浇多少水,喂多少肥,全等于让它独吞了。当时,我好像未加什么考虑,二话没说,拿起铁锹,就把它齐根铲断了。
一棵青枝绿叶的泡桐,就这样倒下来了。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心里涌上来是奇怪的、甚至是忿忿然的感情。因为未经我的许可,竟然在我的小院里长出来,而且长得比我种植的葡萄、石榴还要好,当然触犯了的我尊严。后来我想,也许土地的儿子,在对于土地的依恋外,可能难免产生对于土地的统治、管辖的私有心理吧?
这或许是私有制给人带来的弱点了,嫉妒心是一方面,在你眼皮底下,全不买你账的存在着,伤害了你的自尊心,则是另一方面。这是你的地盘,你的天下,应该你说了算,唯辟作威,唯辟作福,你想要干掉谁,谁就甭想活。于是采取断然措施,恨不能斩草除根而后快。细想起来,太过分了!上帝赐予土地,本是众生共有的,谁都有生长的权力,干吗要斩尽杀绝呢?即或这小院属于我,长出这棵泡桐,给我一片绿,又有什么不好的呢?
小院依旧,冬去春来,石榴剥掉裹着的冬装,已生出淡绿的叶芽,葡萄从土里刨出来,新的枝梗也开始延展,透露出一丝春意。似乎是同时,墙脚下那被砍掉的泡桐,管我赞成不赞成,喜欢不喜欢,拇指粗细的枝条,笔直地拔地而起。也许是我的偏见,我认为它那昂扬着样子,是在向我挑战。
我始则犹豫了一下,结果还是动手,要把它折断。
想不到的,看起来那样柔嫩的枝条,竟是那么坚韧,从撕裂处滴出来的液汁,像切开的血管,向外奔着鲜血似的不可遏止,那情景把我惊吓住了。直到我连根扯断后很久很久,还往外冒出那清洌的晶莹的水滴,淋漓不止,使我有些不安了。
我想,也许是泡桐树痛苦的眼泪吧?
这大既也是我做不成什么事业的缘故了,既缺乏那种歇斯底里的狂热,也没有人皆为敌的可怕的偏执,以及一条道走到黑的死不认错的坚定,当然更不具备说归说,做归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优良”品德。望着我苦心经营,但始终精神不振的石榴、葡萄,我心软了。一个如此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东西,我偏要想方设法地掐死它;而这两种真好像是扶不上去的天子似的,寄托着我中亚甜美之梦的果品,却总像遭霜打过的一样,蔫蔫地了无生气。
有人建议,给葡萄、石榴埋一点维生素吧!有人推荐,一种植物催长剂很灵验的,让我试一试!有人认为,土质不行,干脆换土吧!我都从善如流地照办了,并不见任何效果。直到那位拥有一座向阳小院的邻居,笑吟吟地告诉我,关键在于阳光,万物生长靠太阳,唱了这么多年的歌,你怎么还不明白问题所在呢?我悟了,难道要我拆房子让它们得到充足的日照么?
那么泡桐呢?它甚至一丝阳光也照不到的,无论再三再四的摧折,就在我为我的葡萄、石榴换土施肥之际,一枝比先前更为茁壮的泡桐树苗,管你什么态度,也不看你的眼色行事,又挺拔地,而且无惧无畏地,从墙跟下长出来了。
我问我的邻居,它没有阳光,不也生机勃勃吗?
邻居反过来问我,那你知道,它的根部在泥土里扎得多么深吗?你弄不死的,你对它无可奈何,不管你来硬的,来软的,绝对是在白费心机,你哪怕气得吐血,一个有生命力的东西,它该长出来,你是压制不住的。
由它生长?
这就是世界。再大的小院,也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谁也不可能例外,谁也无权例外,即或暂时例外,除了在历史上留下笑柄外,什么也剩不下的。是不是?我这位学哲学的邻居莞然一笑。
真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说话间,我搬到这幢楼里来住,也快五年了。
葡萄有两年,总是那七八个残缺不全的叶子,结那么可怜巴巴的酸掉牙的十来个果子,仅此而已;后来,也许它自己觉得活得没什么意思,死了。石榴呢,还健在,长高了许多,不过胡乱分蘖,至今既不开花,那肯定更不会结果了。
倒是那棵泡桐,亭亭玉立,长成了树势,硕大的叶片,在夏日里,在微风中婆娑摇曳,也有它自己的一块绿荫。当我推开后窗,那怡悦的绿色和院外的树木连成一气,不也是一番别致么?
真的,我又想我邻居的话,这就是世界。
而且,愈琢磨,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