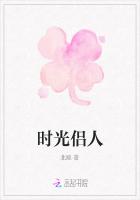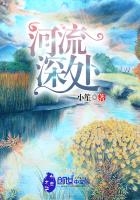若论潇洒风流,以及逞才使气,谁还能比过他呢?在那万象靡弱的元末,除了一个“酸斋”贯云石,能弄得一竿铁笛的,恐怕只有他了。
他的一生,以“五”为尺子,丈量了一个标准文人的毅力究竟有多强韧;以“五十”为界限,划分了一个标准文人与半文人半戏子的前后迥然不同的戏剧人生。
一个人,在铁崖上,五年不下楼,用辘轳运送食物,勉强活着,只为了读书——够倔犟、够有毅力吧?这样的精神,纵是神佛也该被打动了吧?该赐他以无量大才享用终生——他不拥有无量大才谁还配有?虽然他在世俗利益方面失败得那么惨重,那么众目睽睽。
一个人,在家里,五十岁之后,开创了自己的新锐生涯——戏班领导的生涯,一直到死。这是不是比五年不下楼、努力攻书更需要一种勇气呢?
前半生他已经非常成功了——他的确是一代诗伯,总领元末风骚:无论是着眼于文坛,还是注目于剧坛,在他那个时代,他都称得上“学问渊博,才力横轶,掉鞅词坛,牢笼当代”。在文学上,他致力于古乐府诗创作,开创了奇崛瑰丽的“铁崖体”诗风,一时承学者众;在戏剧上,不仅有口自吹曲、身自教舞的艺术实践,不仅在末期所有剧学家中堪称师长、影响众人,而且撰写了一批较受后人重视的戏剧序跋体论……他的这些文论是不能被文学史忽视的,他藉此指斥时弊,反映元末社会极端黑暗的现实,充斥着壮愤雄奇气,与元中期台阁诸臣的所谓“盛世之音”截然不同,有不同于流俗的见识,甚至有非正统色彩。这和他的性格一脉相承:他疾恶如仇,率直无羁,不甘于作和顺逢迎文章,敢于指斥时弊,还往往不留余地,文风豪纵而不以淳雅为美,在整个元文中,都显得很突出。就算写景状物,居然也是如此,笔笔带风。他写的竹枝词一时风头无两,而竹枝词则可以说是香奁诗的自赎,接续了雅正香火。写竹枝词的尝试使他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古代的风人之诗多出于民间社会地位底下的平民之手,却能流传后世,非如今的公卿士大夫作品所能及?因此他提倡较少创作束缚的古乐府而排斥律诗,他想尝试一种风骨情致兼而有之、既有别于文人之诗又不同于当时民间俚曲的新体诗,他把它称为“古乐府”,后人叫它“铁崖体”。他成了。对史上任何一个诗歌流派,我们都乐观其成,只怕他力有不逮——后怕:如果元朝的诗歌顺着香奁诗滑下去,到明清,到今天,就像五代的诗歌顺着香艳诗滑下去到唐朝,再加上北宋的暧昧,以及南宋的靡弱……天,还不要了诗歌的命!简直不敢想象。
然而,这位诗伯,就像一位河伯,他并不满足于在岸边,伸手拿一根竹竿搭救一把落水的诗歌,他干脆跳下去了,与它同命。在他的后半生,真正蜕变成了一位行为艺术家——他之所以风光苏浙,另一个原因是:他成立了一个类似于戏班子的家庭乐班,自己组织、写曲子、谱曲子、导戏并亲自参演、到处演出的乐班——戏班子的前身。这即便在当时的官宦人家也是少有的。
很多人从官场上回归,都是回到大自然那里去;他从官场回归,回到了戏班子这里来。说到底,尽管前者隶属清高一派,但确是主流——主流就是:人们小心翼翼控制自己的生活,跟随大众保证自己的幸福和平安。他选择了非主流生活,成为他的时代和同时代同仁绝妙的对比项,叫你不得不承认:这世上人跟人、事跟事是有远近之别的。他远得他同时代的同仁看不到了。
他为什么做出了这样的选择而不是那样的?显然,那样的更自然,更惬意,更保险,更容易把握。
你知道,从官场到自由身,从退身到选择,这中间是有好大的一段暗黑的通道要走的——“选择”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而那起始的“退身”相较“选择”起始更难上一千倍。
官场,是人人向往、人人怕着、人人怕着却又人人向往的去处——谁都在钻营、享受,更主要在受苦、自作自受。我们对官场爱恨交加,它是我们总无法遂愿的乡愁,总不能左右的命运的象征——庞大、残酷,傲慢而且严肃,混乱而又理性。说到底,官场不过是我们的一个场合,像我们吃过饭、喝过茶、谈过事的另外的“场”一样。而总有一天,我们要回归的,回归这里或那里,回家,经过一个名叫“选择”的通道。这一段暗黑的通道就是自省:我做错过什么?我该怎样矫正?我想做什么?我要怎样达成?要爬着过去,城市的地下道一样,扭曲身子、泥水沾身、灰头土脸地过去——爬过去,才是一个见着太阳和新鲜空气的出口。
五十岁,他气喘吁吁,不无疲累,爬过来,见着了:戏班子。他是如此喜欢这件事物——那时代的新生事物,他喜欢它就等于喜欢元曲。他为那些曲子深深着迷。
无论谁,一生中,总有被忽略被遮蔽、无法完整呈现的吧?总有比起做官更喜欢做的事还没做,来不及或没时间。退下来,那些想做的事一股脑儿全回到脑海里来了,折腾,翻卷,无止无休。唔,与其发问、深究、自省,不如……另建一个场吧,一个乌托邦,按自己的意愿。好像……好像再也不能等了,因为白发,更因为比白发更迫切地冒芽的心。
他如是说,如是做。他以散曲、杂剧当砖石建构,以乐理当石灰抹缝儿,一点一点,居然建成了一座独一无二的私我之“场”。这个“场”并不存在于现在的那个空间里,因为是虚无缥缈的梦,是按照自己脑海里的一个幻觉和印象,任凭他假想与放大的过往,这个“场”全随着他去诠释与驾驭,因此,这是他一个在现实里实现了的理想。而你知道,理想哪有被实现的呢?所以,现出了他的倔犟和意志的强韧——这比五年不下楼还要倔强和强韧些。
够摧残了,我想肯定也有过那样十分厌倦、苦累和怀疑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否有足够价值的瞬间,但相信,那一定只是瞬间,因为他坚持住,做下来,他做成了这件事。在日复一日、似乎永无休止的现实摧残中,他默默承受和呈现,客观、渺小地活着,默默地愁苦着,幻想着,在灵魂深处积累着一砖一瓦,且越是摧残,他越倔强着决意要建出个牢固到固若金汤的那个“场”。他好像被那“场”摄去了魂魄,将所有的心事、理想,都藏在那管铁笛里,或者冻结在那方小小的檀板里。这个“场”并非客观的叙述,而是所有记忆与梦境的纠结。曲子进入那“场”的方式,每个字、每个音符都集聚了无比的奥妙。
然后我们就作为一个漫游者,漫游其间。以往只有梦境,才能让我们将人满为患的喧闹芜杂沉底清空,他则以纯粹的、昂扬的曲子实现并鼓舞我们乘势而入。
然而,他又何尝不知,自己的这次选择和一次特立独行的行为艺术没有什么区别——一样冒着极大的风险,被指责,还有——自身的覆灭。
具体而言,这个“自身的覆灭”几乎是伸手可及的灭顶之灾。最切近的困难就是:怎么养活这些人吃饭?他不做官了,没有一丝收入,那么他靠什么来养自己、养家、以及养这些额外的人等呢?又指导他们演些什么?
但是,难道因为困难就要放弃那么迷人的艺术吗?那个理想?而当理想越来越沉重、越来越沉重、都要沉入海底时,谁还记得打捞?我们不想打捞,他们也不——我们和他们,都真的不知道最终将要牺牲什么,牺牲多少。
他想打捞。
那些都是好宝贝啊——单单宋朝汴京的一个“瓦肆伎艺”就有小唱、嘌唱、杖头鬼儡、讲史、小说、舞旋、手技、相扑、掉刀、影戏、弄虫蚁、诸宫调、商谜、说浑话、神鬼、说三分、叫果子等几十种分派,使人“终日居此,不觉抵暮”,“不以风雨寒暑”,皆要前往;致使“诸棚看人,日日如是”,而且有的唯恐“差晚看不及也”(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卷五)……的好宝贝们,难道要让它们自由更替消长、在我们(元人)手里消失了吗?难道崇雅黜俗风头的重新抬头将把曲子这一本时代刚刚兴起的诗歌样式打压下去吗?难道精英文化仍旧可以将话语权、文化大势垄断起来吗?
当然不能。
打捞一样儿是一样儿。他一定诸如这般地考虑过,就像我们心血来潮时也急于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否则不会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无法回避,就是:他的经济收入来自何处?
正如我们相信或不相信的那样:一个人立志要想做成一件事,就一定有办法。我们成功了就相信,不成功就不相信;而我们相信了就成功,不相信就不成功。这几乎是个可逆的因果。他相信。他很快理清了思路并付诸实施,不辞劳苦。他可以到一些公办的机构任教获得收入,如早年,他到吴兴东湖书院执教,后来又到松江吕良佐璜溪授《春秋》学;再者可以到巨室人家做家庭教师,如他曾授学于姑苏首富蒋家;另外,他还有作序跋、写墓志铭的本事,而且这种费用比较高,如《致理斋尺牍》中提到“兼有润笔之礼”,这是收到润笔后的回信;还有,友人经常慷慨解囊——这虽然依靠不得,但确实也解了一些燃眉之急;最后,在这期间他断断续续也做过一些小官,有点俸禄,如1350年,到杭州任四务提举(实际上他并未赴任)、1359年授江西等处儒学提举等;零零散散的,他也做一点给人校雠诗文的小事等等,也不是免费的。这些辛苦钱加起来,就能养活这一套家庭音乐班了。那时他已经六十九岁了。也着实难为了老人。
还有一个问题,他的这些乐班是如何组织起来的,或者说如何招来的?费了多少工夫?又有多少唇舌白费了呢?
第一种是家里的侍女,有的是妾。曾经有一个阶段,他以及身边的朋友和弟子整日宴饮,所谓“无日无宾,亦无日不沉醉”,有时还做出了以侍女绣鞋盛杯行酒的事情。彼时所作诗歌也大抵为香奁体诗歌,不足取,也不必讳言——我们有什么权利去苛责古人?生而为人,有谁能随便忽略了肉体呢?它几乎承载着所有的悲欢:眼看口嚼。当然,那些温软可人的一切,到底还要手的抚摸和揉捏才能深得其味。况且,人是很复杂的动物,有另外的一面反而正常——有高洁就一定有不可看的暗影,多多少少的区别罢了。大约人的一生都得在灵魂堕落与提升的相抵相依中度过吧?只不过谁在提升的力度上略强些,谁的灵魂就进了天堂。因此,天堂里的灵魂也绝对不是洁白无瑕的——不漆黑如墨就不错了。现在漆黑如墨的灵魂还少吗?查查国外账户就知道了。
说下去……这种侍女是他音乐家姬的主要成员,而古代买侍女、蓄妾本是平常的事,所以,他拥有这种侍女,并且还不少,然而大抵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一年,顾瑛大兴土木,广建亭台楼阁,顾瑛本有这种歌舞美姬为他的朋友唱歌跳舞,这一年也为他买了几个,他乐得笑纳——心里想着:捎带着招聘了演员。《铁崖先生诗集》有一首诗记之。
顾仲瑛为铁心子买妾歌
铁心子,好吹箫,自怜垂鸾之律今老矣,笛声忽起蓝桥津……玉山人,铁心友,左芙蓉,右杨柳,绿花今年当十九。一笑千金呼不售……铁心子,结习缠,苦无官家敕赐钱,五云下覆韦郎笺。
这首诗表明,当时他已有好几个擅长歌舞的妾,芙蓉、杨柳等都在以后带到松江——买妾的价钱不便宜,也不是他能买得起的,当时他也不在任上,没有进项。此时的他已经五十三岁了。对古人来说,这个年纪也算不小了,就算多情,也就是看看罢了,还能怎样?所以,我并不以为他买了侍女主要为了做妾。
第二种是临时搭建的曲班子。他们这批文人并不是天天雅集歌舞。平时只需几个就行了,客人多的时候,就临时借几个。例如至正九年三月的汾湖之游,其中的珠帘氏就是临时借来的舞姬。那些人出场的次数有限,越是次数少越是珍贵,觉得难得。就好比政府,权力有限的政府才可能成为好的政府,但你见过哪个政府权力有限呢?因此,这样的政府理论上存在,实际上不存在。也因此,这种曲班子跟现在的明星走穴似的,一会儿就散,指望不得,约等于望梅止渴。
第三种,他看中的器乐高手。如吹笙的周奇就是他门下的伶。张雨有《玉笙谣为铁崖门生伶周奇赋》,其中说“金华周郎妙宫徵,子晋仙人初教成。月下吹参差,群雏亦和鸣”。这种伶他是随身带的。杨亦有《周郎玉笙谣》一诗赞其技。音乐班子中亦有谱曲的声伎。譬如翠儿,就是专门谱曲的高手。他读赵孟婿王德涟的《踏莎行》八首,读后大喜,“谨以付翠儿,度腔歌之”……“度腔歌之”好是好,可这种高手也同第一种的侍女一样,是需要高价钱养着的。因此,唱的和伴奏的,都张着口等着他喂。也因此,他自贬身价到处打零工赚钱也成为不得已的事情了——不能要读书人的面子了。
说到底,读书人的力量还是有限,一个戏班子,必须要各种辅助才行,譬如,必须有数种乐器相配。他自己能笛、箫、古筝等多种乐器,常常直接参与演出,放下这个是那个,忙得不亦乐乎,却也是一个节省开支的好法子。而那些侍女——也就是那些演员——一个个都身怀绝技,既有姣好的面容、优美的舞姿,也擅长一两种乐器,并略懂诗文。例如小璚花是琴姬,弹古琴;而琼花是舞女;柳枝是歌者……还有一些男伶。另外有弹琵琶的、拉二胡的,不一而足。《挥麈诗话》记:“杨铁崖在金粟道人(顾瑛)家,每食,主人必出佳醖,以芙蓉金盘令美伎捧劝。铁崖出对曰:‘芙蓉盘捧金茎液。’有能者赠以此盘。一伎应声曰:‘杨柳人吹铁笛风。’遂以盘酬之。”这虽然只是一次吃饭,夹进了文学沙龙和音乐茶座的性质,就成了一场散曲、杂剧折子戏演唱会。
他有戏瘾,既然组织了班子,就不可能不带着这帮家庭音乐班子经常到处演出。他甚至还为此打造了一条船,名叫“春水宅”,在宜兴、无锡、苏州不断游览、展演。自言放于宛陵、昆陵间,又自九龙山(无锡)涉太湖,南溯大小雷之泽,访缥缈七十二峰,东抵海。至正九年的游汾湖,是舞乐班大显身手的一次汇演。《珊瑚木难》卷二有详细记录《游汾湖记》:
至正十年(应作九)三月十有六日,吴江顾君逖既招客游东林。明日,复命钓雪舫载声伎酒具游汾湖。客凡七人:会稽杨维桢、甫里陆宣、大梁程翼、金陵孙焕、青云王佐、吴郡陆恒、汝南殷奎;伎二人:珠帘氏、金粟氏。朝出自武陵溪,过五子滩……又五里……遂解舟来秀桥,不问主,径诣亭所。亭曰‘翠岩’。主人为陆君继善,出肃客……饮堂上,出铁笛一支,云江南后唐物也,有刻字:‘七点明列星,一枝横寒玉。’予为作《清江引》一弄,声劲亮甚。笛阕,陆君恒揳予三弦琴,顾君逖亦自起弹十四弦,命珠帘氏与孙君焕作‘十六魔’舞。珠帘氏用白莲瓣令行杯酌主客,舟中鼓吹交作,两岸女妇逐而观者襁履不绝。
因为要行船,所以他不能多带声伎,但所幸来捧场的客人们个个会吹弹跳舞,他也善吹铁笛,并且填了[清江引]等曲,因此,那次演出还是极为成功的。
在组织演出和参与演出期间,他还写下了大量具有鲜明的剧场性的散曲,灵感像汩汩的旺泉,按捺不下。那些散曲个个都是有生命的,跟他这个人一样,同样经过了艰苦的积累、沉淀、等待,似乎是酝酿了许多年的葡萄酒——从生长在枝头,经历阳光的照耀、细雨的拍打,让人禁不住想象:在葡萄园时究竟发生过什么?葡萄枝怎样发芽?葡萄怎样结子?怎样由青变红变紫?……而那些散曲,也像早已长在他的心里,酿在那里,储存在那里,只不过是在这一刻被打开,被一首一首、不断地抄了出来。
他的声伎们唱的歌曲有他作的大量散曲,可惜少有流布。但他的散曲别具风味,神气雄阔,诗歌意象耽嗜诡谲,沉沦绮藻,震荡凌厉,直将逼盛唐——这是他学习李白、李贺浪漫主义创作风格的结果。元代诗坛学李贺之风颇盛,但真正能不停留于色泽、词句而能掌握李贺诗作艺术精髓的,他是极少的诗人中的一个,句子瑰奇如同神从天落。譬如[双调·夜行船]《吊古》这一支:
霸业艰危,叹吴王端为。苎罗西子,倾城处,妆出捧心娇媚。奢侈,玉液金茎,宝凤雕龙,银鱼丝。游戏,沉溺在翠红乡,忘却卧薪滋味。
[前腔]乘机,勾践雄图。聚干戈要雪,会稽羞耻。怀奸计,越赂私通伯嚭。谁知,忠谏不听,剑赐属镂,灵胥空死。狼狈,不想道请行成,北面称臣不许。
结尾处的“北面称臣不许”一句,让情感兀地饱满,整首曲子随之站了起来。
同时,声伎们歌曲里也有梨园供奉曲。例如有一年,他与张雨、顾瑛等游石湖渚,顾瑛唱的就是张雨的《点绛唇》或《殿前欢》这类他们自己填词的曲子。他吹的笛子曲,也是《君子弄》、《梅花弄》等曲子。很多是他自己谱的新曲。
他为什么要自己谱曲让声伎歌唱,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众所周知,元代的散曲,用的是当时北方话的音韵,元曲学家周德清著的《中原音韵》分十九个韵部,四个声调。“作北曲者守之,兢兢无敢出入”,历来北方曲家视为准则。但对南方人而言,很多方言俗语就不合曲谱之韵。就是王世贞说的“胡乐嘈杂凄紧,缓急高下不合南人之调”。所以,南方人,特别是苏州、昆山一带的梨园之曲,就有南方的南曲声腔。他有一篇《舒啸台记》说:“今年春,尝觞予轩所,酒酣,为予作苏门之音。”“苏门之音”,大概就是用南方声调唱的梨园曲。钟嗣成《录鬼簿》记萧徳祥作有“南曲戏文”。南曲,用南方语言,南方曲调。当时,在昆山一带流传着一种“昆山腔”,它的曲调舒徐宛转,演奏的乐曲则多是笛、箫、笙、琵琶。这个“昆山腔”就是后来“昆曲”的滥觞。
又有《南词引证》说:“元朝有顾坚者,虽离昆山三十里,居千墩,精于南词,善作古赋。扩廓贴木耳闻其善歌,屡招不屈。与杨铁笛、顾阿瑛、倪云镇为友,自号风月散人。其著有《陶真雅集》十卷、《风月散人乐府》八卷行于世,善发南曲之奥,故国初有昆山腔之称。”因此,这样看来,史上也承认他在昆曲的行程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当然得承认。必须的,不得不。
去看世间万物,流动的实际上是不动的;不动的,实际上又是动着的。这世界就是这么复杂,这么模棱两可,这么变化莫测,也一定有一些我们还不知道的好事物在哪里猫着。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一样儿事物真正属于我们,当然更没有一件事物能够挂在墙上,我们随时可以去摘。然而,曲子留了下来,在我们伸不长、够不着的历史的哭墙上,温存地垂挂下来,像童话故事里王子赖以攀爬的莴苣姑娘的长发,垂挂下来,让我们攀援而上,得到了幸福。
就这样,他也并不满脸正经地布道,说大家要怎样爱护艺术什么的,只低着头,做了一个别人眼里的下九流,带领着一帮别人眼里的下九流,将“行家生活”与“戾家把戏”用一个具备特异功能的戏班子紧密联接,用曲子——那些散曲、杂剧和曲调,默默建筑了一个场,像孙猴子用金箍棒画的那个圈,妖魔鬼怪别进来,而他珍爱的,别出去。
[原作欣赏]
[清江引]
铁笛一声星散彩,夜宴重新摆,金莲款款挨,玉盏深深拜。消受得小娇娇红绣鞋。
铁笛一声吹破秋,海底鱼龙斗。月涌大江流,河泻清天溜。先生醉眠看北斗。
铁笛一声云气飘,人生三山表。濯足洞庭波,翻身蓬莱岛。先生眼空天地小。
铁笛一声翻海涛,海上麻姑到。龙公送酒船,山鬼烧丹灶,先生不知天地老。
[曲人小传]
杨维桢(1296—1370),元代散曲作家、戏剧理论家、诗人,字廉夫,号铁崖,浙江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人。元末兵乱,避地富春山。后又迁苏州、松江等地。筑室松江,和一批文人墨客“笔墨纵横,铅粉狼藉”。在元末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复杂的情况下,他借此保全自己,故作狂放。
杨维桢创作以诗歌为主,还写了一些传记。如《冰壶先生传》、《竹夫人传》,都写假想的人物和事件,近乎小说。由于作者要避开现实的矛盾,又不敢敞开幻想的大门,故其人其事不免显得单薄,但文字却十分朴雅。
著有《铁崖先生古乐府》十卷,《复古诗集》六卷,《东维子文集》三十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