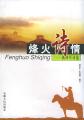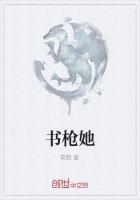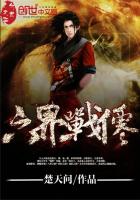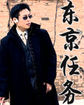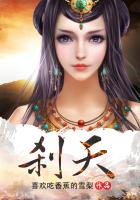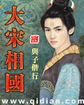□大规划和大拼盘
1950年6月出版的《人民文学》登出一张表格。这一表格以行政区划、体裁为类别列举出《人民文学》的投稿状况。在此前后,全国文联对作家创作计划的调查也在《人民文学》接连公布。
这种张榜公布的举动,固然有展示当前文学创作状况的想法,《人民文学》1950年4月登载的《1950年文学工作者创作计划调查》。
但更重要的则是《人民文学》在执行全国文联的意图、行使一种管理和规划全国文学的权力。如果说文协对全国文学的规划还停留于文学批评和宏观督促的话,1953年由文协改组的作协,则落实为实际的行动。其行动之一,是重新审核作家会员的资格,一方面发展新的会员,另一方面取消多年不发表作品者的会员资格。在那一时期,会员资格是否获取,等同于体制的内外之别。也许是感受于这种压力,曹禺在第二次文代会曾真诚地检讨:“四年来,在创作上我没有写出一样东西……我是一个没有完成任务的人……多么不光彩。”《人民文学》1953年11月号。作协加强各协会和文艺团体的类似举动,实质是以强烈的管理意识督促作家的创作,将作家纳入到一体化的创作活动之中。这种由上而下的规划,既是新中国期望在人类历史的新阶段扫除“非无产阶级”的文学、塑造“人民文学”的战略需要,又是聚合全国文学力量共同完成此一目的的现实策略。它有历史的合理性,但强调一律、集体参与的、类似工业生产的组织模式也带来了诸多问题。
二、百分比系以某区某类作品之总数与全国各区某类作品之总数相比得之。
以全国性的视野来规划文学,显然是《人民文学》的任务和愿望之一。《人民文学》曾多次声明,这是“全国作家的刊物”,代表着中国文学的发展水平。参见《人民文学》1953年2月号的“编者按”。每一次声明中,事实上都包含着一种管理性的要求。
规划造成了《人民文学》版面上的“大拼盘”。《人民文学》虽然以短篇小说为主,但因承担着规划全国性、全局性文学的任务,其稿件编发中不得不照顾到某一时期文学生态上的平衡。从1949~1966年间,各种文艺体裁的作品都在《人民文学》上留有踪影。茅盾任主编的1949~1953年,翻译类的论文、报告几乎与国内原创作品分庭抗礼。即使在翻译类文章中,属于同一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的作品,一个不漏地在《人民文学》上出现。也有美国作家的作品,但这些作品必须是斥责美帝国主义的腐朽、没落之作,如第3卷第6期(1951年4月)上美国作家马尔兹的《马戏团来到了镇上》《世界上最快乐的人》。1958年之后,在“革命浪漫主义”促动之下,《人民文学》上的体裁尤为众多。《人民文学》也有意“纵容”体裁的无规则化。《人民文学》1958年6月号从《人民日报》转载沈汉民的文章《思想大解放,生产翻一番》。该期“编者的话”写道:“转载这篇文章,是为着表明我们这样一种看法:有些文章,看来不符合任何文学体裁的‘规格’,但是却有着结实的生活内容和强烈的感人力量,我们未尝不可以把它看成是最有力的文学作品。”此后,地方戏、相声、歌词、快板、民歌……纷纷被作为“最有力的文学作品”,登上了《人民文学》。《人民文学》在1958年前后真是充分体现了自己的文学“全局性”视野。
在类似1958年这些非常态的时段里,《人民文学》对文学的规划意识主要体现在对需要促进、但创作力量薄弱的题材和体裁上,如工业题材、少数民族题材,以及儿童文学、电影剧本等体裁。
在1949~1966年间,农村题材和战争题材的作品一直“繁荣”,而工业题材的作品相对缺乏。从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来看,这种状况显然是一种文学“失误”的表征。所以,《人民文学》对工业题材的稿子表现出极高的热情。比如在1952年离开《人民文学》之前,秦兆阳作为文学指导者的一面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总结一般来稿而写的《论一般化和公式化》连续刊登在《人民文学》上,对反映落后转变方面的公式化写作多有批评意见。但是,秦兆阳在这一期间唯一热情赞扬的文章却是工人作者左介贻的《红花朵朵开》。《人民文学》1952年2月号。这是一篇写工人中先进人物的速写。由于作者文化水平不高,文章又是处女作,其幼稚可以想象。但《人民文学》不仅登载这篇文章,还配发左介贻《给〈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信》,让作者以示范的姿态在信中介绍自己的创作经验。秦兆阳在《文艺报》上又写《评〈红花朵朵开〉》一文推荐,称这篇作品虽然是作者“初次的作品”,却是“很好的中篇小说”,结构形式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例子”。《文艺报》1952年5号。作为《人民文学》主编的茅盾和艾青,也参与到对工业题材的提倡上。在《人民文学》第2卷第1期(1950年5月)上,茅盾发表了指导工人写作的文章《关于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艾青发表了《谈工人诗歌》。在同一期,不知名的作者叶淘的《炼狱》成为头题小说。此后,只要是工业题材的作品,《人民文学》常常给以显著的位置。
如《人民文学》第4卷第1、2期(1951年5、6月),连续的头题小说是《老工人郭福山》(丁克辛)和《工厂里的战斗》(何苦),作者都属初登文坛。对工业题材的重视,在17年间的《人民文学》基本上始终如一。它成了《人民文学》从全局性来引导全国文学发展的一条重要原则。这一原则甚至不容藐视和触动。2003年8月14日笔者采访涂光群时知道,张天翼主持《人民文学》时期,老报人张白曾有一段时间做小说散文组的组长。但是有人向张天翼反映,张白对待工农兵作家的态度不好,对他们的作品也有意见。其时正在1958年的“大跃进”前后,张白这一表现显然不合时势,结果张白从《人民文学》调离。
《人民文学》1952年1月号发表了玛拉沁夫的《科尔沁草原的人们》,这是新中国最早的少数民族作品之一。
少数民族题材方面的作品也受到极高的重视。玛拉沁夫的处女作《科尔沁草原的人们》之所以登在《人民文学》上,与作者的民族身份和小说所反映的民族生活不无关联。在全国性的文学会议上,玛拉沁夫时常被作为少数民族文学崛起的例证。茅盾在第二次文代会上将玛拉沁夫、纳·赛音朝克图等少数民族的作家提升到中国文学史的地位上,“还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以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的先进人物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茅盾:《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中国新文艺大系·理论史料集(1949—1966)》,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90页。其他写民族生活的小说,如白桦的《山间铃响马帮来》等也受到重视。此后,《人民文学》有意识地发表了许多民族史诗,如《阿诗玛》等。
儿童文学一直是当代文学中创作比较薄弱的一个领域。1953年张天翼就带头写儿童文学作品,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罗文应的故事》。王蒙登上《人民文学》的第一篇作品即是写小学生的《小豆儿》。1957年,《人民文学》又连载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张天翼成为主编后,儿童文学更成了《人民文学》持续发表的作品。贺宜、金近、葛翠琳等第一代儿童文学作家开始涌现。
总之,《人民文学》在基本稳固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这四大块之外,时常呈现出光怪陆离的文学景象。甚至说,“大拼盘”的丰富与单纯之变,直接折射着文学的气候变化。
□审稿机制的六次微变
艾芜的小说《夜归》发表在《人民文学》1954年3月号,自邵荃麟担任《人民文学》副主编后,老作家在刊物出现的频率增高。
由于文艺方针的不断变化,《人民文学》对文学规划的具体趋向也出现不确定性,与之相适应的编辑部组织形式也不断调整。但是,三审制,尤其是规避犯忌的审查机制一直存在。
《人民文学》创刊之初,内部体制还不完备,承袭着类似1949年前同人杂志社那种合伙的方式。当时只有严辰、秦兆阳、古立高三位编辑,三个人没有职位上分别,共同负责《人民文学》的编辑工作。这种松散的、作家合作的方式,在丁玲代替艾青做副主编时期还在延续。其时,陈涌、萧殷轮流主持《人民文学》。他们同样无编辑部主任之名,却有执行编政之实。
在这一段时期,编辑部内气氛和睦,相互之间能够平等地交流和学习。据涂光群回忆,编辑部中人大都住在一个院子,喜爱音乐的萧殷曾引导年轻人欣赏西方的乐曲,还鼓励年轻编辑多写些作品。2003年8月14日涂光群口述资料。这一时期的编辑部弥漫着一种旧文人的情调。
1953年邵荃麟成为《人民文学》主编之后,编辑部开始出现职业性和内敛型特色,编辑部的文人情调被等级、分工明显的工业化模式所代替。我们看到,编辑部第一次出现了“主任”一职。主任以下,又依据文学体裁分设各小组组长。至于将编辑归于哪个小组,虽然考虑编辑个人的文学特长,但又不完全依据这种条件,所依据的是某小组的工作量、某体裁是否需要加强的程度来定。比如1953年上半年进入《人民文学》的涂光群,曾先后在秘书处(回复读者来信)、版面美术设计、评论组、小说散文组周转。
白桦的小说《一个无铃的马帮》发表在《人民文学》1954年11月号,这篇小说在1954年、1955年分别被拍摄成电影《神秘伴侣》和《山间铃响马帮来》。
编辑部的内敛型表现为编辑方针和编辑部重点工作的转移。茅盾时期的《人民文学》大量发表翻译文章,国内作品集中在解放区来的作家和某些初露头角的新锐身上。邵荃麟上任之初,即提出发表作品的多样化。《人民文学》公开说:“我们认为,像《人民文学》这样全国性的文学刊物,它应该积极扶初学的青年的作者,但应该首先依靠专业的作家,没有人数众多的专业作家经常撰稿来,没有中国的创作由沉寂衰退而转变到活跃和繁荣,要办好这样的一个刊物,要使这个刊物成为真正能够代表中国的刊物,是不可能的。”见《人民文学》1953年2月号的“编者按”。由此,作者对象转向国内的老作家。所谓依靠老作家其实是向国统区作家开放,如巴金、路翎、骆宾基等等。1953年7、8月合刊号上,独有巴金的《黄文元同志》以老五号字排出,在整本刊物中显得大而美观。邵荃麟曾为此受到非议。有人据此指出,《人民文学》重视国统区作家,不重视解放区来的作家。涂光群:《回忆邵荃麟》,《中国三代作家纪实》,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35~36页。但《人民文学》并不是无原则地开放,在发表这些老作家的作品之前,要经过严格的筛选和审查。此一时期的编辑部建立了秩序明确的三审制。
经由普通编辑、小组长、编辑部主任、主编,稿件要经过层层把关。一些在政治上拿不准的稿子,必须经过来自延安鲁艺、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葛洛。如路翎《洼地上的“战役”》就经过葛洛的严格把关。
1956年秦兆阳担任《人民文学》副主编后,编辑部出现了打破三审制的倾向。其组织方式也由内敛型向外向型扩张。此一时期中国作协对文学的要求是配合“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文学应该体现出“群众性、战斗性和现实性”。《人民文学》为实现此目标,编辑方针调整为反对“无冲突论”、反对“保守主义”的方向。秦兆阳的编辑思想,实际上可以概括为发表有独立见解、能干预生活的文章。适应此一规划目标,《人民文学》编辑部组织形式开始改组。此前严格的三审制以及工业化的组织方式,此时显得僵化和束缚。秦兆何迟的讽刺相声《开会迷》发表在《人民文学》1956年8月号。
阳常常直接从普通编辑的案头拿来作品看,而不是等待秩序化的层层上报。同时,秦兆阳也要求编辑们主动向外组稿,而不是紧盯着已经成名的老作家。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即出自普通编辑谭之仁之手。这一时期的《人民文学》,一方面有许多政论文章,如张春桥的《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们》;另一方面也有电影剧本如《钟义和小白龙》,地方戏《祭头巾》(常德高腔)、《借亲配》(滇剧),相声《开会迷》(何迟),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丁玲)、《铁木前传》(孙犁)等等。但更引人注目的是秦兆阳根据个人的编辑思想组来的一些“干预”特写和小说。《人民文学》一时间集聚了一批思想比较契合的作家。这些作家基本上都属于青年人,之前多在地方刊物上发表作品。后来,随着“反右运动”的来临,秦兆阳对编辑部的这种改动,被指责为“拉派”、“轻视老作家”。
1957年张天翼成为《人民文学》主编后,经历过1957年的“反右”和1958年的“大跃进”,也经历过1960年的“调整”和1962年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紧张形势。
郭小川反击右派的诗歌《射出我的第一枪》发表在《人民文学》1957年9月号。
张天翼接受前任的教训,在编辑部内实行秩序化和外向型交叉管理的办法。一方面督促编辑们走出编辑部,到火热的“生活现场”组稿,以配合“大跃进”和1962年“大写十三年”的文艺形势;另一方面由副主编陈白尘或李季亲自把握某些可能犯忌的作品。冷暖交迭的文艺形势和督促全国文学发展的规划意识,使张天翼感受到作家命运的神秘莫测:没有哪一位作家敢保证永远正确,哪个作家都可能随时出问题。因此,张天翼在编辑部秘而不宣地制定出一、二、三线作家联络图。时任小说散文组组长的涂光群回忆道:“《人民文学》编辑部在小说、散文等方面分别拟订了周详的全国作家的组稿名单,定稿后打印出来,每个编辑人手一份。小说作家名单,分为一、二、三线。‘一线’是指那些创作活跃、水平稳定的一批著名作家,这是刊物经常联系、重点组稿的对象;‘二线’通常是指因各种原因写稿不够经常或水平不够稳定的作家;‘三线’是指已经在全国或地方露头,但作品不多,创作状况尚欠稳定的青年作家……每个编辑都分工联系一批一、二、三线作家,并制定每季、每月的具体联系、组稿计划,或写信或出访。应当说明的是,这一、二、三线作家名单被严格规定仅限编辑部内部使用,不许对外公开。”涂光群:《张天翼和〈人民文学〉》,《中国三代作家纪实》,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52页。这张联络图既体现着《人民文学》将全国作家都纳入进来的全国性视野,又可准确掌握作家的动态,以便某方面的文章需要侧重时有联系的对象;但更为重要的,恐怕是随时掌握作家是否还有权利写作的动向。
1962年李季担任《人民文学》副主编时,编辑部组织形式再次出现变化。之前的外向型在此时体现得更为明显。李季的口号是“每个人都要做主编”。2003年11月5日周明口述资料。他沿用编辑分行政区负责的办法,要求编辑们到全国各地去,现场抓题材、抓作者,现场将作品修改、编辑完毕,然后寄回发表。这是一种近似于报社抓新闻的措施。事实上,这一措施与《人民文学》此一时期的任务正好合拍。在上海柯庆施倡议的“大写十三年”、讲述革命故事受到最高领导的鼓励后,《人民文学》对文学的规划已经不再是以题材、体裁为主了,直接变成了以地区为主,重要的工厂、革命老区、先进地区……每一个似乎都要在《人民文学》上留下影子。由此,1962年之后的《人民文学》出现了异常热闹的景象——“青海速写”、“西安速写”、“大庆人写大庆”、“故事会”、“大写社会主义新英雄”等等栏目让人目不暇接。
无论编辑部的组织形式如何变换,对作品的严格审稿始终是编辑部不变的一项任务。只是这审稿有些时候紧而严,有些时候相对松弛一点。在邵荃麟时期,严文井、葛洛对稿件的审查相当严格。严谨是这二人共同的风格。严文井曾经编辑过《东北日报》,党报的做法被他带到了编辑部。葛洛虽然年轻一点,但他是鲁艺出身、又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政治观念更强。王蒙一篇写儿童的短篇孙谦的《大寨英雄谱》发表在《人民文学》1964年4月号。
小说《小豆儿》在发表前就被大量删改,以致引起王蒙登门抱怨。关于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经过,涂光群认为首先是来自胡乔木的关照;当这篇小说受到侯金镜等人的批判时,涂光群说:“这里值得提出一说的是审稿、定稿,除了副主编严文井(严文井的编辑作风一向严谨、认真、细致),编辑部副主任葛洛那儿也是重要的一关。葛洛……对作家们的稿件,一向要求严格,审读认真、1961年10月,老作家陈翔鹤在《人民文学》发表《陶渊明写〈挽歌〉》。这篇文章成为陈翔鹤被批判的重要罪状。细致,颇善‘挑毛病’。解放战争期间他曾随军参战,调任前刚从朝鲜战场归来,说他是个‘战争通’并不过分。路翎写朝鲜战争的小说,假如作者想‘偷运’什么‘私货’(后来的批评者语),在葛洛那儿是很难通过的……葛洛对作品的看法是比较稳实、客观、可靠的,这更坚定了编辑部当时一般不谙战争生活的人们的信心。”
侯金镜等人的批判虽然曾使《人民文学》惶恐不安,但编辑部还是有一定的底气,原因就在于这篇小说经过了葛洛、严文井的把关。
秦兆阳时期的审稿工作相对松弛。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严文井后来批评秦兆阳“看不起同时代的作家”,其中即包含着对秦兆阳独断作品、不严格履行主编终审的指责。严文井:《评“本报内部消息”》,《人民文学》1958年9月号。即便如此,刘绍棠的作品还是在已经排版、即将发稿的时候被突然抽掉。张光年:《好一个“改进计划”》,《人民文学》,1957年11月号。1960~1962年的陈白尘,在文学规范相对放缓的这一时期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尽管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最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陈白尘还是预先表示过异议的。
《陶渊明写〈挽歌〉》是我自己发稿的,因为我喜欢它。《广陵散》写出时,我已实际脱离了《人民文学》的编务了,我读了更喜欢,但我有点担心。因为那时已在广州会议以后,上海一位“大人物”不仅喊出“大写十三年”,而且盘马弯弓,不知意欲何为;我劝翔老和编辑部要持慎重态度,暂缓发表。但编辑部坚持要发,而且对翔老在篇末写的《附记》,我认为可删的,他们却特别欣赏。
陈白尘不在编辑部,就已经表达了“暂缓发表”的意见。假如他仍在编辑部呢?这篇小说不发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又如对郭小川的《一个和八个》,陈白尘就明确表示不能发。在陈白尘之后上任的李季,从《广陵散》发表不久就受到批评中意识到形势已经变化,开始绷紧了审查作品的神经。涂光群在比较李季和郭小川的创作性格时曾谈道,“在李季的创作构想世界里,似乎有明显的区分,哪些是可以表现的,哪些是不可触撞的;他决不‘越位’,决不像小川那样不守本、不安分,总是想在新的领域去探索,总想做个开拓者、跋涉者……这也许正是李季作为一个诗人在政治上的老到之处。”涂光群:《小川和李季》,见《中国三代作家纪实》,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63页。1962年,周扬曾指示编辑部联系发表李建彤的长篇小说《刘志丹》,这篇小说经责任编辑、编辑室主任、执行主编阅读通过后,“决定将其发表于《人民文学》第10期头条,稿子立即发排”。然而形势马上发生了变化,“还未等看校样,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传达下来”,防范意识极强的“李季十万火急地要编辑部抽掉长篇小说《刘志丹》那篇稿件”。结果《人民文学》避免了“险些陷入反党活动的陷阱”的灾难。黎之在《回忆与思考——大连会议·“中间人物”·〈刘志丹〉》一文中,详细介绍了此书在中央高层权力斗争中的情况,周扬将此书介绍给李季、李季听闻不许发表时曾向中宣部打电话等细节在此文中有反映。
总之,17年期间,《人民文学》一开始就将为新中国文学规划蓝图当作了自己的任务。在这一任务下,《人民文学》以“拼盘化”编辑刊物的同时,也推动了某些题材、体裁的发展。编辑人员的组织形式也随着文艺方针的不确定而频繁波动,但其中稳固的是审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