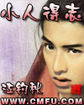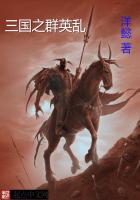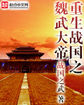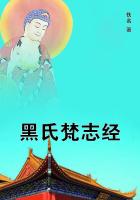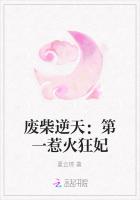字应军
唐代以前今滇池北岸(即今昆明市区范围内)文献中记载有苴兰城、谷昌城、昆州城、益宁城等几座城池,但这几座城虽有文献提及,但有关城址、城池规模、建城时间的记载各种史料均不一致,即使是城名的记载也各不相同。且多数史料为明清时期的后人推测,因此时有张冠李戴的情况出现,如:将元梁王所筑的王(玉)女城及元代所筑的碧鸡关城、金马关城当做汉城等。有关前述几个城池考古方面也一直未能提供有力的证据,因此唐代以前的几座城池进一步的准确的考证还有待新的文献资料和实物材料面世之时。今滇池北岸(今昆明市区)范围内的筑城确凿记载,亦即今昆明城的发端是在唐代(南诏)时的公元765年的拓东城。
一、拓东城的建立
大唐帝国盛极一时,但在其近三个世纪的统治时间里,四周都面临少数民族的侵扰而穷于应付,其中势力最强、威胁最大,能与唐一较雄长的就是西边的吐蕃政权。甚至,唐代后期,吐蕃还一度成功地攻入了唐京城长安,并建立过一个傀儡政权。
唐代前期,吐蕃势力不断南下,一度控制了洱海北部的今剑川一带。洱海地区的各部大多数归附吐蕃。若洱海地区为吐蕃所控制,将对唐构成极大威胁。唐必须稳定洱海地区。而洱海地区各部又充分利用唐蕃矛盾,时而归唐,时而附蕃,叛服无常,在两大势力的夹缝之间艰难寻觅生存和发展的机遇。局势混乱而无序,唐朝便想从洱海地区各大诏中,选择一个首领加以扶持培植,帮助其统一洱海各部,进而通过这个亲信实施唐中央在此地区的统治,以便既能稳固洱海地区局势,又能牵制吐蕃势力南下。
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间(734—737年),唐朝调动力量对南诏首领皮罗阁进行策划劝导,并支持他从南诏老窝巍山出兵攻伐其余各诏,737年,南诏统一了洱海地区,建立了南诏国。南诏政权建立后,唐中央封皮罗阁为云南王,使其成为西南少数民族中的一个王侯。唐中央也企图假借其手镇压西南其他少数民族的反抗,并成为吐蕃势力南下的强有力的屏障。然而唐王朝美好的愿望却招致了相反的结果。南诏是一个新兴的势力,极富扩张欲望,其雄心飞扬、目光深远,其志不在偏安滇西一隅,不甘雌伏于唐朝之下。于是巧妙利用唐蕃矛盾,在夹缝中生存并积蓄力量,时机一至,便四出用兵。
南诏建国前后,滇东、滇中一带的爨氏已江河日下,力量削弱,无统一的强有力的统治者。诸爨之间互相攻杀兼并,局势混乱不堪。南诏建国后不久,唐王朝委派南诏军队东进,以平息诸爨之乱。南诏利用这次平叛的合法身份,吞并了两爨之地,并乘机夺取姚州及其他三十二州,割据之势已成。
唐王朝不甘于苦心扶持起来的南诏倒成了其在西南统治的最大障碍,于是天宝年间三次出兵讨伐,南诏在吐蕃的支持下大败唐军,唐二十多万大军血本无归。天宝战争使南诏完全倒向吐蕃,唐朝苦心经营多年的成果毁了一旦,而吐蕃却坐收成果。752年,吐蕃册封阁罗凤为“赞普钟(小赞普)南诏大国”,“赐为兄弟之国”。
天宝战争的胜利,使南诏将唐朝的势力完全赶出云南。完全据有云南后,南诏统治集团在吐蕃的支持配合下,雄心万丈,极想建立一个军事大帝国。于是修筑道路,建立制度,设置城池,训练军队,四出用兵,攻城占地。764年,南诏王阁罗凤视察滇池地区,他站在滇池边的高处,指着滇池坝子说,这里的山川可以作为天然屏障,富饶的土地足以养活人民。于是第二年(765年)命长子凤伽异在此筑城,取名拓东城,并命凤伽异以南诏副王的身份,坐镇拓东城。拓东城是有准确史料记载的在今昆明市区范围内的首次建城,后拓东城在南诏统治力量的整盘布局中地位越来越重要,成为陪都、东京。大理国时期,拓东城(称鄯阐城)地位、作用一如南诏。
二、城名含义及建城时间
绝大多数人将南诏筑的此城记作“拓东城”,唯有樊绰《云南志》及《新唐书》记作“柘东”,“拓”字从“木”。《通鉴》胡三省的《注》说拓东“言开拓东境也”。从《南诏德化碑》的记载看,拓东城的设置就是为了控制东北至今昭通、东川、贵州威宁—带的爨区,南至今红河州南部的广大地区。拓东城设立前后,正是南诏雄心万丈之时,欲从东、西、南三面扩张。从城池的设置及取名也可看出南诏国欲称霸一方的雄心。东边的重镇叫“拓东”,南边的叫“开南城”(今景东南),西边的叫“镇西城”(今盈江),唯北面尚忌惮于吐蕃,因此只好低调地称“宁北城”(今剑川南)。四方要塞均各派重将以节度使、大军将的身份镇守。因此“拓东”之意就是“向东拓展”无疑。只有极少数学者称不太清楚“拓东”的含义,如贾耽《路程》认为拓东之意“不可考”。
关于拓东城的建立时间,各种史书记载不同,《南诏德化碑》记载:“赞普钟十二年(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冬,诏(阁罗凤)候隙省方,观俗恤隐,次昆川,审形势,言山河可以作藩屏,陆川可以养人民。十四年春,命长男凤伽异于昆川置拓东城,居贰诏,佐镇抚。”明白无误地记载拓东城建于公元765年的春季。樊绰《云南志》则记载:“拓东城,广德二年(764年)凤伽异所置也。”两者相差一年。本人认为《南诏德化碑》立于公元766年,亦即建拓东城后的次年即立碑,立碑时间与拓东城始建时间紧紧相连,此外碑为南诏官方所立,立碑时作出筑城命令的决策者及筑城的亲历者尚健在人世,因此其记载更为可信。《云南志》作者樊绰,咸通三年(862年)随蔡袭入安南(今越南),后在安南留居一年,其《云南志》就是作于这两年间,成书时间与建城时间已相隔九十多年。其次,樊绰的素材大都来自别人的记述或他人的介绍,并未亲历拓东城在内的南诏国绝大部分城镇,因此其史料的准确性不可能有《南诏德化碑》高。此外,《南诏野史》“南诏古迹”中认为后来作为省城的拓东城筑于永泰十一年(775年)。但该书中多处关于拓东城的记载矛盾太多,可信度小。(需作说明的是《云南信息报》在刊登有关纪念昆明建城1240年有关采访文章时,在本人与廖国强先生均不知晓的情况下,将本人上述观点几乎原文加在廖先生的访谈录中。)受俄罗斯圣彼得堡建市纪念活动启示,省内著名画家、省政协委员赵力中先生前年在省政协会上提出了关于确定昆明建城纪念日及举行昆明建城纪念活动的提案。提案得到了重视,由有关方面转由昆明市地方志办公室答复。市志办马颖生、字应军、廖国强经与赵力中先生进行讨论后,认为昆明城准确的建城之始应从拓东城起;时间为南诏赞普钟十四年、唐永泰元年,即公元765年;具体的月、日没有记载,但《南诏德化碑》中表明是春季,此“春”指的是夏历的“春季”。市政协委员廖国强先生在2005年市政协会上提出了《确立昆明建城纪念日的建议》提案,引起了市有关各方的高度重视。廖国强为此查阅陈垣先生的《二十史朔闰表》(中华书局1962年版,1999年第四次印刷),永泰元年(公元765年)的农历“春”当为该年公历的1月26日至4月24日。廖国强建议将昆明建城纪念日定在3月18日,既尊重了拓东城建于春季的史实,又符合中国人“讨口彩”的习俗,与民国期间将省城定名为“昆明”的用心也相同。
三、地理位置
《南诏德化碑》记载“命长男凤伽异于昆川置拓东城”,元代的许多著述及碑刻都有“中庆,古鄯阐也”的记述,明白地告诉人们中庆城就是南诏拓东城(鄯阐城)。从《南诏德化碑》记载的阁罗凤“次昆川(今昆明)”及樊绰的《云南志》的记载中也清楚地表明拓东就在今昆明市区范围。《云南志》记载:“拓东城,广德二年凤伽异所置也。其地汉旧昆川。”“晋宁馆八十里至拓东城,八十里至安宁故城。”则拓东城在今昆明坝子。“金马山在拓东城螺山南二十余里”、“碧鸡山在昆池的岸上,与拓东城隔水相对”,以及唐宋时期史籍记载的东西寺塔、圆通寺与拓东城的位置关系均充分说明拓东城就在今昆明市。
有关拓东城的地理位置也有不同的说法,明代的《南诏野史》载:“永泰元年(765年),凤伽异筑云南城,即今云南府省城。又筑拓东城,今云南府昆阳州北平定乡。”据众多史学家证明,古之“云南”,指的是今祥云一带,“云南城”则在今祥云云南驿,今昆明地区唐代称昆川,南诏国时称鄯阐府。《南诏野史》作者认为南诏时期的云南城系明代云南府城即今昆明城,既有省城在今昆明,那作者只好替又筑的拓东城另择风水宝地,于是拓东城搬到今昆阳北了。据《晋宁县志》载,今昆阳北海口一带旧时称平定乡。海口稍南即为昆阳古城,现尚有“古城”地名,但昆阳古城系明正德年间所筑,该处尚未发现南诏古城之遗迹。此外,还有些史家认为拓东城在罗次、安宁,不知何据?
关于拓东城的具体位置有两种主要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拓东城在盘龙江西岸,金碧路、东寺街一带,或者说,明代的砖城就是在拓东城的基础上建立的。而且考古工作者也曾在此发掘出一些唐宋时期的文物(考古学家胡绍锦先生就此问题已发表过文章)。另一种观点认为大理国的鄯阐城是在拓东城基础上增修的,而段素兴时期的绕城金棱河和萦城银棱河即为东边的金汁河一段及西边的盘龙江一段,并且在城之南、北连接绕城金棱河和萦城银棱河修筑“来镇堰”和“佑文堰”蓄水以灌农田(参见明陈文《新建南坝闸记》、景泰《云南图经志》)。因此拓东城应在盘龙江以东金汁河以西。如《昆明市志长编》的编者认为,根据文献和实地调查材料考证,拓东城应建在今状元楼一带,具体方位应在今民航路五里多以西、盘龙江东岸地带,亦即今拓东路、和平村、塘子巷一带。《昆明市志长编》编者已作过详细的考证。
关于拓东城址问题,笔者暂无法进行详细考证,但有几点想提请有关考证者注意:一是拓东城最初是为了向东拓展而筑的军事基地,而非是因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而自然产生、发展、壮大之城,因此,可以肯定最初只是一个小土城,否则隆舜也不至于在城外另筑小城予其子居住,世守鄯阐的高氏家族也不会将其府第建在城外。三是今书林街、东寺街一带曾被段氏家族划为宫苑。二是1119年三十七部起事后,据有鄯阐地区三年后才被镇压下去。鄯阐城在三年的双方攻守焚杀中遭严重摧残,几乎被夷为平地,后世将被毁之城称为“废城”。起义被镇压后,大理国统治者(主要是高氏)鉴于鄯阐城已毁,因而连接段素兴宫苑旧址和高氏府宅区域,重新筑土城,称作“新城”,沿称“鄯阐城”。清《高宗实录》记述征得胜桥以西冠生园一带的税赋时,明确称此地为“新城”,直到民国年间,这一带仍称“新城铺”(1924年张维翰《昆明市志》)。新筑的鄯阐城比原拓东城古城占地面积扩大。
南诏国在今昆明市区范围内筑有拓东城外,尚于9世纪后期新筑一城。据《南诏野史》“南诏古迹”记载:“城东古城,宣武王(南诏王蒙隆舜谥宣武王,在位时间为877年至897年)筑小城与子舜化贞,即古城。”“古城,云南府省城(明砖城)东,南诏蒙隆舜筑与其子舜化贞者。”即南诏至隆舜时在鄯阐(拓东)城外,另筑小城与其子舜化贞,新筑之城明代称古城,而明代所称古城并非拓东城。张道宗《记古滇说集》也具体地记载了舜化贞“小城”与拓东城的关系,即隆舜筑新城给其儿子舜化贞,并称新筑之城为“中城”。
四、关于拓东龟城
“拓东”之名并非最先在今昆明市使用,据文献记载在“拓东城”之前还有“拓东龟城”。但这些记载均无拓东龟城的具体位置。雍正《云南通志》则记载拓东龟城在昆阳平定乡,为张建(俭)成入唐时(748年)所建。此外,李孝友先生编著的《昆明风物志》载,在唐诏天宝战争前,“南诏曾经在今晋宁南面三四十里的地方,建筑过一座‘拓东龟城’”。则将拓东龟城放在晋宁以南。
各种史籍对筑拓东龟城的时间记载相差也较大。康熙《蒙化府志》记载,乾元元年(758年)凤伽异筑“拓东龟城”。此为记载拓东龟城建筑的时间最晚者。《滇史》载,开元十年(722年)左右,“盛罗皮始筑拓东龟城,其形象龟,以江萦之,蛇其相,取义《易》之既济也。”天启《滇志》载:“开元二年(714年),盛罗皮遣张建成入朝,西筑拓东龟城。”《滇系》也载:“玄宗开元二年,南诏晟罗皮遣张建成入朝,乃筑拓东龟城。”两书均将拓东龟城的建筑时间定在714年。《滇考》载:“太极元年(712年),罗盛炎死,子盛罗皮嗣,始立孔子庙于国中,筑拓东龟城。”此为见诸史籍中的最早的拓东龟城。以上诸种记述时间相差较大,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拓东龟城建于张建(俭)成使唐前后。
历史上到底有无“拓东龟城”?“拓东龟城”在何处?罗次、晋宁南三四十里及昆阳北平定乡等与“拓东龟城”有何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笔者尽自己的条件查阅了一些资料,但一直找不到“龟城”的解释,只在《汉语大词典》中查到“龟城”曾是成都的别称,但无“月城”、“卫星城”之类的含义。元人张道宗撰的《纪古滇说集》则将“龟城”建立的时间提得更早,但仍无城的具体位置;不过却能解释清楚“龟城”的含义。《纪古滇说集》系采录《僰古通纪》及汉唐史书以编撰云南历史之著述,因作者采录较杂,史实与神话混杂,且在流传过程中又多经后人篡改,因此谬误丛生。在此只当做一种说法介绍给读者。《纪古滇说集》记道:“时有滇人杨道清者,殉道忘躯,日课经典,感现观音大士,遐迩钦风,渔者焚网于滇水之旁,酒家隳其器具,皆以利物为心。蒙氏威成王闻知,及亲幸于滇,册道清为显密融通大义法师。始塑大灵土主天神圣像,曰摩诃迦罗,筑滇之城,以龟其形,江萦之蛇,其相取义《易》之既济,王慕清净法身,以摩诃迦罗神像立庙以镇城工,五年龟城完也……王建都城中,册为天府,祛邪辅正为事,复像二神,一镇龟城之顶,一镇城之南,灵德一然。”记载中没有道明“龟城”的地理位置,但从书中的“金马”、“碧鸡”之类的记载推,“龟城”似在今昆明。从记载中得知,所谓“龟城”是城形似龟,并取《易经》中的含义。作者认为以龟蛇作城池的象征主要是因为:一是中国古人认为龟蛇是有灵性而吉祥的动物,龟有甲壳能抵御灾难,蛇虽无壳,但进退自如,可以避害,因此行军打仗,常将龟蛇绣于旗帜之上;其次,古人认为麒凤龙蛇是四种吉祥的有灵之物;第三,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北方之神“玄武”以及后来道教信奉的四方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中的“玄武”,其塑像就是龟或龟蛇合体。《纪古滇说集》中记载的“以龟其形,江萦之蛇”估计取义为第一种和第二种,如果取方位之意,则龟城应在今大理之北。该书记载“龟城”建于“蒙氏威成王”即位之初,“威成王”即南诏国王盛罗皮。盛罗皮于唐先天元年(712年)即位,开元十六年(728年)卒,那么“龟城”建设比拓东城早五十多年(可能即为李孝友先生所说之“龟城”)。但当时今昆明地区仍属爨地,南诏尚未统一洱海地区建立南诏国,势力未达今滇池地区,不具备在滇池地区筑城的条件,即使真有拓东城龟城,也当在当时南诏势力所及的今巍山一带,因此,《纪古滇说集》之说显然不可信。况且天启《滇志》记载的是“西筑拓东龟城”,既然是“西”,那就不可能是今昆明地区。
五、拓东城的地位及规模
拓东城一经建立,其在南诏国的向东向南拓展中越来越显示出其巨大的作用,加之,滇池地区本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较省内其他地方超前,因此,拓东城(中后期的鄯阐城)成了南诏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另一个中心。建城初期,即成为“居贰诏”的重镇,后来又先后被正式定为副都、东京、上京,其地位逐渐超过了南诏的都城。关于这个问题,作者将在下一篇文章里详述。
据《昆明市志长编》考证,南诏拓东城周长约六华里,是一个狭长形的土城,由于防御的需要,东、南、北三面有城墙,河上有木桥可通滇池,类似南诏太和城。
拓东城的具体布局今已不得而知,樊绰《云南志》说南诏“城池郭邑皆如汉制”,因此其特点应与同期内地的一些城池相近,当然也有可能如《纪古滇说集》说的城形似龟。或者可以从与拓东城建筑时间相近的南诏都城太和城、阳苴咩城的布局风格中得到启示。
南诏王阁罗凤时南诏建国,739年始,在今大理市中和镇南、太和村西筑都城,称“太和城”。城西倚天然屏障苍山,东俯视洱海,因此只筑南北两道土夯城墙,面积约3平方公里,747年建成(早拓东城8年)。估计南诏王对太和都城不太中意,因此在阁罗凤定都太和的同时,一直在西洱河蛮原有城池的基础上筑阳苴咩城。779年到南诏王异牟寻时,迁都阳苴咩城(晚拓东城14年)。阳苴咩城在今苍山中和峰下,今大理古城及周围一带,布局和形式与太和城相似。大理国也以阳苴咩城为国都,一直到元代初,此城作为云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存在了五百多年。《云南志》对城的规模和建筑有详细的记载:“阳苴咩城,南诏大衙门,上重楼,左右又有阶道,高二丈余,以青石为磴。楼前方二三里,南北城门相对,太和往来通衢也。从楼下门行三百步至第二重门,门屋五间。两行门相对,各有牖,并清平官、大军将、六曹长宅也。入第二重门,行二百余步,至第三重门。门列戟,上有重楼。入门是屏墙。又行一百余步至大厅,阶高丈余。重屋制如蛛网,架空无柱,两边皆有门。楼下临清池,大厅后小厅,小厅后即南诏宅也。客馆在门楼外东南二里。馆前有亭,亭临方池,周七里,水深数丈,鱼鳖悉有。”拓东城为南诏重镇,其地位后来超过阳苴咩城,因此其规模及形制应不输于阳苴咩城。
因为拓东城于南诏国无比重要,且南诏王中有在此登基者,有在此驾崩者,有长期在此居住者,因此历代国王应不断对其扩建增修。拓东城内城外王宫、官署、馆驿、寺庙、善阐台(即今南天台)一应俱全,史书也记载有寻阁劝曾与臣僚在善阐台吟诗作对。南诏拓东城内外给后人留下许多遗迹,如829年,南诏弄栋节度使王嵯巅请中原工匠尉迟恭韬在拓东城西一里外滇池水滨建觉昭、慧光二寺,并建东、西两塔。
尚有文献记载,南诏曾在拓东城内建有五华楼,楼甚巨大,上可容万人。按此说法,拓东城的五华楼要比大理城的五华楼宏伟。但因只是一家之说,其他史书均不见拓东城有巨大的五华楼之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