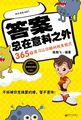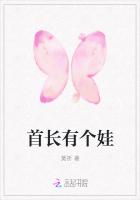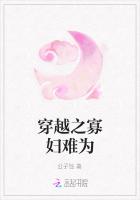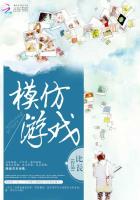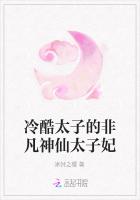摩尔根在科研工作中的一个很大特点,便是同时进行很多实验。 1908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各种胚胎学研究实验的同时,要他的一名叫佩恩的研究生做一项关于果蝇的实验。在摩尔根同时进行的多种实验中,有不少做进了死胡同,但果蝇的这项实验,却使他获得了生物学研究中的杰出发现。由此,果蝇也成了科学史上最著名的动物之一。
摩尔根要佩恩在暗室中饲养果蝇,希望能得到一种处在这种环境中的果蝇,因眼睛不用而退化,并在其后代中消失。此前,佩恩曾用瞎蜥蜴和印第安无眼穴居鱼进行过有关研究,因此,摩尔根提议他做一个这样的果蝇实验。
果蝇又名醋蝇、果渣蝇及香蕉蝇。其名称是因这种小蝇当初被从北美招引来时所用的水果名称而定的。为了收集果蝇,佩恩在实验室窗架上放上一些香蕉。果蝇被招来之后,便开始一代一代地繁殖。果蝇被放置在一个终日不见光线的实验中饲养,但一直毫无结果。当第 69代果蝇眼睛出现昏花现象而乱窜时,佩恩立即叫来摩尔根,让他看这似乎是成功的结果,可这一代果蝇很快就恢复了视力,并向窗户飞去。师生俩在一阵兴奋之后,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但是,这种并不知道会产生什么结果的实验仍然进行着。果蝇因其繁殖快、食物便宜而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间实验室里被大量饲养着。这个实验室很快就被冠以“果蝇”之名。它面积近 60平方米,墙边靠着每个都装有成千上万只果蝇的小奶瓶。
与此同时,摩尔根还与佩恩一起用果蝇做了一项诱发突变的实验。 1904年,生物学家德弗里斯曾提出可通过人工方法诱发突变的观点,他认为,可以用具有穿透功能的伦琴射线和居里射线来改变生殖细胞中的遗传粒子。可能是受德弗里斯这一观点的启发,摩尔根和佩恩俩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用 X射线、镭、大幅温差变化、盐、糖类、碱类等因素,来刺激果蝇,可一直也未引起突变。于是,摩尔根有点绝望了。他在实验室里挥动着双手,指着那装满果蝇的一排排瓶子说:“两年的研究工作泡汤了。这两年,我一直在繁殖这些果蝇,可是却一无所得。”
但是,两年的研究空白并没有使对果蝇的研究进入死胡同。约在 1910年5月,摩尔根的“果蝇室”里诞生了一只白眼雄果蝇,而它的兄弟姐妹们的眼睛都是红色的。显然,这个“白眼睛”是个突变种。
它从何而来?摩尔根认为,这是他们诱发突变的成功。他说,在这只“白眼睛”出世的同一个月里,他用放射线处理了不少果蝇成虫、蛹、幼虫和卵,并说他的大量翅膀突变型果蝇都与他用镭处理过有关。但当时在美国自然博物馆工作的弗兰克 ·E·卢茨则说,这只白果蝇成果有他的一份,他说:“托 ·亨·摩尔根教授访问我曾工作过的冷泉港卡内基实验室时,我告诉他,在一种有血统来历可查的种系中,曾出现过一只白眼果蝇,但由于我忙于研究果蝇的反常翅膀,所以无暇顾及它。摩尔根带走了这只白眼突变种的活的后裔,并用它们进行繁殖,最终获得了白眼果蝇。那时,我要是意识到这只突变种有多大价值时,我才不会乐意送人呢!”
摩尔根不接受这种说法。他说自己确实从卢茨那里要过一种果蝇培养种,但卢茨的白眼果蝇并不在其内,因为那只“白眼睛”被发现时就已死亡。也不存在“白眼睛”的后代,因为如果有,在其下一代中会产生不少白眼果蝇,但实际上一只也没有出现。
据说这只白眼果蝇是在摩尔根的第三个孩子出世前突然产生的。他的第三个孩子长得很好,可这只白眼果蝇却很虚弱。摩尔根晚上把它从实验室带回家,让它睡在床边的一只瓶子里,白天再把它带回实验室。它临死前,精神抖擞地与一只红眼睛果蝇进行了交配,把突变基因传给了后来发展成为庞大家族的果蝇。
10天后,这只白眼果蝇产生了 1240只后代。用孟德尔学说原理来解释,所有后代均应为红眼睛,因为红眼对白眼是显性。可奇怪的是,在“白眼睛”的第一代果蝇中,却出现了三只白眼雄果蝇。
从遗传学角度而言,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摩尔根认为,这 3只白眼果蝇的产生是突变作用引起的。事实上,这可简单地解释为“没有分离”或实验室管理不严有别的果蝇类侵入,要么就是卢茨说摩尔根曾从他那里接受了白眼果蝇是对的。但是,如果卢茨的白眼果蝇确实活过一段时间,并曾繁殖过,而且,在他给摩尔根的培养种中,有一只是该白眼雄果蝇的雌性后代,那么,这只果蝇是会继承一个白眼基因和一个红眼基因的。这只雌果蝇应该有红眼睛,因为红眼基因是显性。但在它的下一代里,任何继承了白眼基因的果蝇都应具有白眼睛。要了解为什么是这样的,那么,至少得等到另一代果蝇产生的时候。
10天后,下一代果蝇出来了。当白眼果蝇的子代彼此交配时,其结果则与孟德尔法则相符,一共有 3470只红眼子代, 782只白眼子代,基本上是每 4只之中就有 1只继承并表现出隐性状态,两代果蝇中都没有出现混合遗传现象,不同的亲本性状分离得很好。
摩尔根立即将这一繁殖结果写成论文《果蝇的限性遗传》, 1910年7月22日,这篇关于果蝇的第一篇论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它为用果蝇实验证实孟德尔遗传原理的正确性开了先河。
但是,紧接着的一次实验便出现了一个异常结果。按孟德尔原理进行推测,在果蝇的第二代中,应各有 1/4的雄性和雌性表现出隐性性状。可摩尔根发现实验结果不是这样,雄蝇中一半是红眼,一半是白眼;而雌蝇中却没有白眼,全部雌性一律都是红眼睛。
那么,白眼果蝇中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雄性呢?接着的实验回答了这个问题。当一只白眼雄蝇与一只正常雌蝇交配时,全部后代均为红眼;当一只白眼雌蝇与一只正常的雄蝇交配时,其后代中的一半是白眼,而且都是雄蝇。显然这种白眼基因并不像孟德尔所说的其他隐性性状,其结果是要受双亲的性别影响的。摩尔根对此所作的解释相当复杂,后人研究发现,其中有的细节是错误的,但结论却是正确的,即决定眼睛颜色的基因与决定性别的基因是结合在一起的,即后来生物遗传学中所说的“连锁”。
摩尔根已经知道,雌蝇有两个 X染色体,雄蝇则只有一个,但能不能确定 X因子就是 X染色体,摩尔根还举棋不定。其原因首先是他不喜欢假设,而当时的染色体理论就是一种假设。其次,他的实验结果与当时英国人做的蛾类和鸟类的研究结果相矛盾。英国人的研究结果表明,某些性状经常见于雌性个体中,这意味着雌性只有一个 X因子,而雄性则有两个 X因子。再次,摩尔根认为假设发育是由一组主宰一切的染色体所决定的理论,与先成论观点一脉相承,而这种学说错误地否定了环境和细胞质对生物遗传的影响。还有一点,就是关于染色体的实验表明,染色体好像不是控制一切遗传的基质。染色体的数目,因不同的生物而有异。如果蝇有 8条染色体,而金鱼有 104条,一种西班牙小蝴蝶有 380条,狗和鸡各有 78条,马有 64条,人有 48条( 1956年后被研究认为 46条)。摩尔根还说:“由于染色体数目小,而个体的性状却十分繁多,根据这个理论,许多性状势必包含在同一条染色体中,因此,许多性状必定随之一并‘孟德尔化’。各种事实与该假设中的这一先决条件果真一致吗?我看不尽然。”
随后几个月的实验中,又出现了另外 4种眼睛颜色的突变种。有粉红色眼睛,这种类型的分离与性别无关,与白眼无关;而朱红色眼睛的果蝇则受到性别制约,表现出与白眼睛相同的分布情况。于是,摩尔根说:“如果正如事实所表明的那样,粉红色的因子存在于遗传机制的另一部分中,而白色因子则不然,那么,为什么在一般情况下(白色和粉红色),存在着限性遗传,而在另一种情况下(红色和粉红色),则存在着另一类遗传。换言之,白色因子是与决定性别的因子联结在一起的,而粉红色因子则存在于细胞的别的部分中。这个证据似乎向我表明:限性遗传现象是由于在性别因子和所论及的其他各种因子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物质联系所引起的。而最明显的联系则为在既带有性别因子,又带有受性别限制的那些因子的染色体中所发现的这种关系。”(见《科学》杂志, 1911年第 33期第 536页)就在同一篇文章中,摩尔根说自己已完全相信,果蝇突变实验是按孟德尔原理所说的那样发生的,“对于每个留意到这些新类型的历史、其性状的‘分离’,以及在大多数情况下缺乏中间类型的这一现象的人来说,有一个事实颇为令人注目”。(同上,第 496页)不久,实验进一步证明,基因是成群地一起遗传下来的,其群数与染色体条数相一致。由此,人们认为,基因很可能就是染色体的一部分。
进一步的实验使摩尔根颇感兴奋。因为,一连两年的果蝇实验,未曾让摩尔根获得一个突变种,可两年后,几乎每月都有一两种新的突变型出现。从实验记录中看,在 1910年白眼果蝇出现之前,曾出现过一只胸部带有呈三叉戟形黑斑的果蝇;还有一只躯体呈橄榄色;第三只翅膀呈串珠状;还有一只翅膀根部带有不同寻常的颜色。可是,摩尔根似乎把这些仅仅看成是新果蝇的一种特殊而无关紧要的“胎记”,而没有把它们看成是应珍视的特例。但五月份之后,突变型竟然如此频繁地出现,这使很多研究者不禁要问:此前摩尔根是否并未用镭处理的方法来增加突变率。这个问题现在已搞不清楚,因为当时摩尔根实验的重点是关注特殊突变的规模,而不是出现率的精确计量。摩尔根尤为关注的是全部新果蝇的分类和交配,因而,他的实验记录肯定不会着眼于回答这一突变问题。作这种推测是有据可依的,他在给学生莫尔(后来成为他的同事)的一封信中说:“现寄上有关上次所送原种的简短说明。那是在我培养的果蝇里新产生的一种平头变种。但它到底来自哪一种培养蝇,我现在连想也想不起来了,尽管我可能在什么地方存有一份记录。”
到1912年末,已发现能与普通果蝇明显的新类型 40种。这些突变种一经被发现,就用来进行交配,先让它在子代的兄弟姐妹中进行交配,然后,再与每一个亲本交配,并与其他变种交配。就这样,繁殖出具有为研究工作所用的各种基因的果蝇。
这成千上万的果蝇大多被放在摩尔根从哥伦比亚大学自助食堂“借来”的一种小玻璃瓶内。实验所需的果蝇数量如此之多,而又要求计量准确,那么,怎么来数清这些一刻也不停乱窜的果蝇呢?摩尔根和他的合作者们用乙醚把新的子代麻醉在瓶子里,然后将被麻醉的果蝇摊开,用手握透镜或简单的显微镜进行计数。数完了就把它们拧死。如果还想做进一步的实验,就将它们再放回瓶子里,等它们醒来后,再让它们饱餐一顿烂香蕉。因为每次实验都需要对成千上万的果蝇进行计数,所以,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人们常常能看到一些学生带着一瓶瓶的果蝇回家,那是为了回家后在厨房或餐桌上计数果蝇。这种工作虽枯燥,但没有人嫌烦和看不起它。有一次,有人问摩尔根一个学生的孩子:“你爸爸是干什么的?”这个孩子自豪地答道:“我爸是替哥伦比亚大学数苍蝇的!”
如果说要数清成千上万的果蝇和观察到实验中的反常现象是艰难的,那么,要对导致观察结果的种种看不见的机制作出合理推论,那就更难了。摩尔根和他的学生们绞尽脑汁,通过在果蝇中转移基因的一系列实验,来加速对遗传规律的观察和推理的过程。
摩尔根通过实验,断言在显性基因和携带性别因子的染色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他发现了一种小型翅膀的果蝇。这种突式还表现出与白眼果蝇一样的遗传模式,即是性连锁的。至此,摩尔根已拥有果蝇的3种因子,即白眼、朱红色眼和小翅膀。这些因子显然就处在携带性别因子的同一染色体上。
但不久,摩尔根又发现,正如他料想的那样,这些分离成 3类的几十个突变种与果蝇中的 3对大染色体是一一对应的。
摩尔根对这一可喜发现依然感到诚惶诚恐,因为如果大染色体与连锁群呈一一对应关系的话,那么,果蝇有 4对大染色体,那又如何解释呢?虽然果蝇的第四对染色体很小,但到 1914年,摩尔根还是预测到第四个连锁群的存在。他的学生米勒很快发现了弯翅膀,即第四对染色体上的第一个基因。后来发现只有少数几个基因是与弯翅膀这种性状相分离的。因此,在每一连锁群中,基因数目与它们所从属的染色体对的长度是成正比的。
摩尔根在说他发现小型翅膀果蝇时,并没有透露其数据,因为他无法解释这样的事实:虽然小翅膀和白眼是“受限于性别”的,或者说是性连锁的,但这两种性状有时又各自分离。换言之,即母蝇在一条染色体上携带白眼或小翅膀,其所发生的雄蝇有 3种类型:一种是带普通眼睛和小翅膀的;一种是带白眼和普通翅膀的;还有一种是带普通眼睛和普通翅膀的。
后来,摩尔根对这两种显性基因不能一起分离的现象作了这样的解释:也许它们在 X染色体上所处的位置不是很近。如果在减数分裂过程中这两个 X染色体像其他各自染色体一样交换了基因,那么,染色体上距离得远的部分就有可能进行交换,而对靠得很近的两个基因来说,这种交换就不大可能了。由此,摩尔根“发明”了遗传学上的两个重要名词:交换——染色体之间相互交换基因的过程;连锁——因子处在一起的倾向。
从科学史角度看,摩尔根提出的这种“交换”,曾有萨顿、威尔逊等提及过,但摩尔根和他的学生斯特蒂文特为此提供了遗传证据,并进一步提出了一个重要看法:即基因之间的距离(仅为 2.54厘米的几万分之几)以及它们的次序,是可以从遗传交换的结果加以推算的。独立分离的程度越大,则处在同一条染色体上的基因相距可能相远;完全独立的分离,就意味着这些基因处于不同的染色体上,或是处在同一染色体上,但间隔甚远。
斯特蒂文特曾说:到 1911年后期,他“突然”理解到连锁强度的变化(而此前,摩尔根已将其归因于基因之间距离的不同了),可为测定一个染色体的线性循序提供可能。于是,当晚他在家里绘制出一张染色体图。这张图包括性连锁基因 y(带色身躯)、 w(白眼)、 v(朱红色眼睛)、 m(小翅膀)和 r(退化的翅膀),其排列与标准图上的次序相同,其距离也大致接近。
于是,摩尔根和他的伙伴们开始测量,更确切地说,是开始由基因交换频率来推算所有突变基因彼此之间的距离。他们精心推算,所绘的染色体图,甚至在半个世纪之后的遗传学研究中,仍保持原样。测得的距离单位,被后人称之为“摩尔根”,如斯特蒂文特发现黄色身躯的果蝇基因,距离白眼基因 1.5“厘摩尔根”。
1913年,当摩尔根确信染色体实验具有重要意义时,就立即撰写了《遗传与性》一书。 1915年,他与 3名年轻同事斯特蒂文特、布里奇和米勒合著出版摩尔根最著名的一本书:《孟德尔遗传原理》。该书总结了果蝇的全部研究工作。它第一次尝试把遗传学的全部内容与染色体的行为统一起来。书中证实了孟德尔定律及其例外情况,并用基因对这些现象作了解释;基因是可见的染色体的基本构成部分,它们呈直线排列成条型;在遗传研究中,基因的行为与染色体行为完全相互关联。基因成对,染色体也成对。每对中只有一个传给任一子代中。基因存在于与染色体的数目和大小相一致的各连锁群中。
摩尔根染色体的理论,很快获得了世界遗传学领域内的至高评价。科学家韦丁顿称这种理论“体现了想象力的巨大飞跃,比之伽利略和牛顿毫不逊色”;达林顿则认为,摩尔根是第一个借实验作桥梁,填补了那条传统的、总是将卵和躯体、精神和物质分开的鸿沟。摩尔根染色体理论的产生,开创了人类建树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
《孟德尔遗传原理》逐步被文明世界的大部分人认为言之凿凿;在美国,各种荣誉对着摩尔根纷至沓来。霍普金斯大学授予摩尔根法学荣誉博士学位,并成为国家科学院院士。 1927年成为国家科学院院长;被任命为英国皇家学会的外国会员。这些荣誉为他日后获得各种基金会的奖金提供了重要条件。事实上,各种荣誉中,最适合于他的,莫非是生物研究事业中的,而对各种行政职务及其本职之一的教书,人们实在不愿做任何恭维。他教书的态度依然如故。学生们不难发现,他在从课堂向实验室的途中,常常呵欠不止。对待行政职务,他似乎也毫无激情。他曾与哥伦比亚大学同事邓恩说道:你得学会远离走廊,因为走廊通常会把你引到会议室里去。他曾问邓恩:“你的办公室里有几把椅子?”邓恩说:“有两把。”摩尔根摇摇头说:“那是一个错误。那里只应该有一把椅子,而坐在那把椅子里的,应该是你本人。”
摩尔根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的办公室里没有“多余”的椅子,他坚忍不拔地在果蝇室里工作了 15年之久。而这 15年的工作实践,却折射出科学发展史上永不褪色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