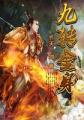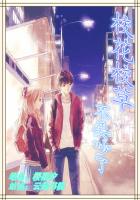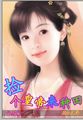这一期所摘编的刘纳的一篇文章则以“文学既是历史现象,又保留着非历史的性质”这样的文学观立论,她认为由此而形成了不同的评价“角度与尺度”,都不可忽视。文学“有自己超历史的审美追求”,对它进行审美的评价是必要的,但从“文学的历史性”出发,文学也“有理由直接反映历史的变动”,“当我们谈论中国近现代文学曾经因为接近政治而使自身的审美品格受到某种抑制时,我们更应该顾及这样的事实:政党斗争也曾经为文学的变革和发展开辟道路。当我们认识到‘服务’于政治体现着一种狭隘的文学观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参与政治斗争与社会生活曾经使文学的表现领域得到扩展”,“‘宣传’和‘说教’自然不是文学必须具有的本质的属性,却是文学可以具有的属性。而且,只有在现代社会里,由于印刷方式和传播方式的改进,人们才有可能充分地估量与实现文学的‘宣传’作用”,“‘近代意识’、‘现代意识’、‘当代意识’往往最先浮现在‘传声筒’式的或准‘传声筒’式的作品里”,“从历史进步与文学进步的角度,我们有理由对那些为文学转折开路的作品格外厚爱”。
不难看出,1989年前后,围绕着“重写文学史”所发表的各种意见,所引发《论文摘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84)论略〉及其讨论》,《丛刊》1989年第1期。
黄子平、李稢:《文学答问录·文学史框架及其他》,《北京文学》1988年第7期。
《论文摘编·关于文学的历史性和非历史性———从一个角度谈现当代文学研究》(刘纳),《丛刊》1989年第1期。
的种种争论,都是学术性的,它所显示的是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重写”的冲动背后是重建自己的历史观、文学观、文学史观与现代文学观的冲动,这也正是争论的分歧所在。争论中思维的活跃与无忌,态度的坦诚与执著,更是显示了这个学科的创造活力。但在后来,“重写文学史”的主张与实践,受到批判。针对于此,唐等老一辈学者及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大多数学人则坚持把讨论限制在学术探讨的范围内,反对一切非学术的干扰。最后的结果,如樊骏所说,并“没有掀起什么大的风浪”。这同样显示了现代文学研究这支队伍的日趋成熟:经历了历史的风风雨雨,他们已不再屈从政治的压力,能够坚持自己的独立的立场了。
创刊十周年纪念
我们的《丛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迎来了自己的创刊十周年纪念。主编王瑶用“蹒跚十年”来概括其所走过的路程;并且说“已有几次濒于‘心肌梗塞’,面临停刊危机”,“这主要是经济的危机”。副主编樊骏则谈到《丛刊》出版发行陷入困境,“印数锐减”的情况:据统计,“创刊号的印数是3万册,1980年各期的平均印数为18500册,1985年降至8250册,1989年每期只唐在1989年10月20日应约而写的《关于重写文学史》一文中,顶住压力,明确表示:“我赞成重写文学史。”在谈到讨论中的不同意见时,也表示“我也不同意有些人立刻给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政治概念,这里谈的只是对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
文收《唐文集》第9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在此之前,王瑶也表示了这样的意见:“每个时代的文学史都应该达到自己的时代的高度。我们正处在一个重新思考的时代,已经到了重新审视我们走过的道路,重新来研究文学史学科如何发展的时候了。”他同时强调:“现在要重写文学史,我看就要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些人愿意以这种框架、这种观点来写,可以;那些人愿意以那种观点、那种框架来写,也可以。”但他又提醒年轻人:“不要以为过去的都不好,我们的这本就最好,这种办法恐怕不行。还是大家都来写文学史,都来接受历史的不断检验。通过历史的检验,优秀的文学史总会出现的。”见《文学史著作应该后来居上———在〈上海文论〉主持的“重写文学史”座谈会上的发言》,文收《王瑶全集》第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樊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又一个十年(1989—1999)———兼及现代文学学科在此期间的若干变化》(上),《丛刊》2000年第2期。
王瑶:《蹒跚十年》,《丛刊》1989年第3期。
印2750册”。这里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要作具体的分析,但却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术研究的内外环境的日趋恶化,而且这也并不只限于现代文学研究这一个领域。也正因为如此,《丛刊》十年所作的努力就显得格外可贵。
樊骏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十年(1979—1989)》一文中,首先用大量的统计数字,强调“《丛刊》十年的版面告诉我们,就整体而言,革命文学、进步文学依然是研究的主要对象,关于它们的思考和探讨,以及由此得出的成果,都明显地多于现代文学的其他组成部分”,说明现代文学研究“总体格局的相对稳定”。———这显然是针对着关于“革命文学、进步文学受到研究者轻视忽略的议论”,而按当时(1989年)的时代语言,这是关系“这些年来的研究工作的根本导向的估计”的。樊骏的这一分析,既反映了客观事实,又带有某种自我辩解与维护的性质,是应该为后来者所理解的。樊文接着又用大量篇幅详尽地分析了“部分研究者创新开拓的努力”,并且认为只有把“稳定”与“创新”这两个侧面“放在一起考察,方能对于《丛刊》十年有个全局的把握和如实的评价”。
这正是反映了《丛刊》所特有的风格的;如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到的,唐曾以“持重”二字概括《丛刊》的“个性”。樊骏对此作了如下发挥:“学术工作从来都要求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严格严谨的作风,任何轻率随意的做法,都是有违于科学原则的。对于这个工作越是深入下去,就会越自觉地采取持重的态度”;“有些文章虽然不一定立刻引起轰动效应,但只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确有所得、内容充实的,总是有参考价值的。经过时间的考验,‘持重’的风格将会受到更多读者的赏识,其积极意义也会得到更充分的理解”。但也正如唐所说,“一个刊物还应该拓荒,创新,力求进步”,《丛刊》在总结自己的十年之路时,也正以此激励自己,这都预示着90年代的新的开拓与发展。
樊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十年(1979—1989)》,《丛刊》1990年第2期。
唐:《祝贺与希望》,《丛刊》1989年第3期。
樊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十年(1979—1989)》,《丛刊》1990年第2期。
中篇:第二个十年(1989—2000)(一)政治风波影响与商业大潮冲击下的学术坚守(1989—1994)相濡以沫“进入90年代以后,现代文学史研究相对平静,甚至给人以沉寂感”:这是一位学者的感受,大体上是有根据的。于是就有了基础性研究与平实的学风的倡导。《丛刊》1990年第1期特设“作品专论”专栏,《编后记》说明这是“意在提倡细致扎实的微观研究”,并作了如下阐述:“文学史的大厦,是由一块块作品基石支撑起来的;作品研究理所当然地应成为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工作。
对于每个研究者,更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功训练”;“大题可以小作,小题也可以大作;无论是课题的选择、方法的试验,还是研究深度的探求,作品研究都大有可为”。这一期的另一个新辟栏目是“文学期刊研究”,发表了殷国明的《〈浅草〉论》。《编后记》强调:“关于文学期刊的研究,也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基础工程,它应该是正在创建中的‘现代文学史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期望“有更多的研究者,都能下一番工夫认真阅读、研究文学期刊,从大量接触第一手原始材料入手,经过自己的独立研究,作出新的理论概括”。这一期的“短文选编”也是精心设置的,并特加“编者按”:“本栏目的文章篇幅均在五千字以下,而且大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史理论与实践的回忆》,《丛刊》1995年第1期。
事实上,到了9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以至整个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都被边缘化了,这也体现在《丛刊》的出版发行上:它的印数从总40期(1989年第3期)的2725册下降到总80期(1999年3期)的1400册,几乎打了一个对折。樊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又一个十年(1989—1999)———兼及现代文学学科在此期间的若干变化》(上),《丛刊》2000年第2期。
《编后记》,《丛刊》1990年第1期。
都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这对澄清诸如‘不上万言不像学术文章’之类的误解,大有作用;对下笔数万言,废话、套话、空话连篇的学风也是有力的针砭。”
三年后,也即1994年第1期《丛刊》,又有了这样的《编后记》:“在看稿时,眼前时时闪动着作者孤灯一盏艰难‘爬格’的身影,心头也就滚过阵阵热浪,感受着一种‘相濡以沫’的温暖,作者与编者就这样相互搀扶着,勉力编出了一期又一期的刊物,表示着‘学术’的微弱的存在”,“这里确实没有追求广告效应的惊人之论,但也都言之成理,言之有据,付出了大量的诚实的劳动。自然,谈不上大的突破,但多数文章至少做到了对所研究的课题有所发现,有所推进。这在有些人看来可能是一个低标准。但在到处都是伪劣产品,连学术界也不例外的情况下,能够不说连自己也不相信的假话,少说空话与废话,也就不易了”;“我们不敢有什么奢望,只愿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朋友始终保持这种平实的学风和人生态度,就像当年朱自清先生所说的那样,‘还原了一个平平常常的我’、‘只谨慎着自己双双的脚步’,‘一步步踏在泥土上,打上深深的脚印’!”樊骏后来在总结《丛刊》第二个十年时,曾引述了这段《编后记》,认为是体现了一种“没有彷徨,没有感伤,在寂寞中依然焕发着献身学术而一往无前的炽热精神”,这大概是可以代表9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界占主导地位的一种精神状态与学风的。
坚持探索
但在坚守中仍有新的探索的努力与创新的尝试。《丛刊》自1991年第2期起,连续三期组织的“文学史观讨论”可以看作是80年代有关讨论的延续,并且有新的发展。同期设置的“现代作家与地域文化”专栏,1993年第1期开辟“沦陷区文学研究”专栏,1993年第4期设“现代作家与宗教文化”专栏,1994年第4期组织“现代女性文学研究”专栏,1994年第3期发表孙玉石的《现代诗樊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又一个十年(1989—1999)———兼及现代文学学科在此期间的若干变化》(上),《丛刊》2000年第2期。
《丛刊》1994年第1期又组织了一个“现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专栏。
《丛刊》1994年第1期与1996年第1期都组织了“沦陷区文学研究”专栏。
人的玄想思维与文化结构》提出“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都意在开拓现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新视野、新方法。此外,还发表了一些具有开拓性的文章,如《从近代到“五四”翻译观的演变》(汤哲声,1990年第1期),《稿费制度的确立与职业作家的出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之一》(栾梅健,1993年第2期),《作为文学(商品)生产的海派期刊》(吴福辉,1994年第1期),《毛泽东文艺思想与现代性》(李扬,1993年第4期)等,都显示了90年代初期现代文学研究在稳健中求新的态势。
面对经济大潮的困惑与选择
但从那段历史中走过来的人都知道,这是不断挣扎中的前进。《丛刊》1994年第2期发表的一个学术研讨会的“综述”即是以“面对经济大潮的困惑与选择”为题。据报道,与会者注意到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新的变化: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的价值观发生较大变化,社会文化心理也产生了广泛的位移,对物质经济的关注超溢了对精神文化的关注,现代文学多年来备受青睐的‘显学’地位已告失落。如:现代文学研究论著难以出版;有学术价值的专著滞销亏本,而粗糙平庸的通俗读本却充斥市场;大学生对学习现代文学不热心,报考现代文学专业的硕士博士人数逐年减少;大学文科里,加速发展的是直接获取经济效应的学科等。社会文化的选择呈现功利主义的幼稚病”。
于是,就有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面对市场经济的对策”这样的议题。
与会者对此作出了不同的回应,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一部分学者认为上述现象“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为社会进步的某种必然”,“我们决不能因为现代文学陷入困境,就退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而应该迅速调整自己,找准自己所处的社会位置,发展现代文学学科”。有的学者则认为,“经济大潮固然使现代文学研究失落了‘显学’地位,但也使之从政治束缚下解放出来,从而有可能成为古典意义上的独立的学问,摆脱虚假的使命感和现实功利性,向文学本体回归,这又从另一个意义上标志着现代文学研究真正开始走向正路”。
早在20世纪80年代孙玉石即在《丛刊》发表了《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的文章,并引发了一批研究成果。文载1987年第2期。
而另一些学者则提出异议,他们认为,“经济发展不能以削弱人文科学为代价。拜金大潮的涌现,人文学科的受轻视,完全是短视的实利主义思想的产物。
如不纠正,历史的惩罚将是必然的。物质利益的递增而精神文化的迷失乃是历史的悲剧。我们决不能为迎合市场,满足一部分人的世俗的欣赏趣味,而降低现代文学的品味”。
对应态度的不同背后是对文学、学术(包括现代文学)研究的性质、功能、作用的不同理解。有的学者认为,“文学价值要通过商品价值才能得以实现和获得自身本位。在商品经济社会里,文学必须面对市场,才有发展前途”,因此,“现代文学研究要从‘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要改变中国现代文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文人学者的现象。面对市场,首先就是面对读者市场,让更多的读者喜欢和理解现代文学”,“大力做好现代文学的普及工作”。另一些学者则强调“市场价值不是一切,许多精神产品的价值不是市场价值所能衡量的,它们超越了当前的市场价值,而属于将来或永恒的范畴。文学在今天无疑具有商品的属性,但文学作品的价值与一般商品依据赢利的多寡而定价值又有不同,文学要有自己的价值”;“纯文学从来就不是为大多数的,现代文学研究是严肃的文学研究,属‘精英文化’。在尚有二亿文盲的中国,今天难以激发大众对纯文学的热情,这需要一个渐进过程。现代文学普及工作要待文化素质整体性提高以后方能奏效。现代文学研究者应是‘精英文化’的维护者,我们不能只顾迎合大众口味,而失去高雅的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