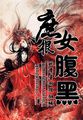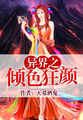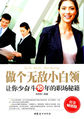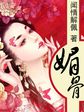作为大将,能抓住对手的皇子,那是多大的功劳呀!这种千载难逢的立功机会,他怎么可能一声不吭地舍弃而走?很明显的例子是,李世民在虎牢前线侦察时,说了一句“我秦王也”,就呼啦啦引出了窦建德五六千立功心切的追兵。至于唐书上说其“惶惧”而退,我看也值得推敲。在李世民面前,单雄信有什么必要“惶惧”呢?李世民是李唐的皇子,又不是王郑的皇子。他职位再高,权力再大,也不能给单雄信提拔一下职务,多发一些年薪。他左右不了在王世充手下效力的单雄信的生活,所以,单雄信在心理上不可能忌惮李世民。这就好比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可能“惶惧”自己的顶头上司厂长和经理,而不会“惶惧”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的市长或者总理一样。
二是根据洛阳战役的整体部署,李世勣并不是跟随在主帅李世民身边的,他应该是被派到东线作战的东路军指挥,因为一直在洛口一带作战的大将王君廓就属于李世勣部。所以,当李世民在魏宣武陵被王世充的大部队包围并和单雄信相互厮杀时,李世勣不可能身在现场喝止单雄信。
无论李世勣在不在,单雄信被俘后是很快就不在了。面对勇将,李世民这次没有惺惺相惜而执意要动刀子的确切原因,没有人知道。和此事有瓜葛的三方当事人李世民、李世勣和单雄信的传记中,均无对此事的任何文字记载。
随着王世充和窦建德的相继被擒,真切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洛阳会战宣告结束。本书之所以将人们习惯称呼的“洛阳之战”改为“洛阳会战”,是因为本人觉得用“会战”更为确切。这场数十万人参加的惊天动地的三方大战只有用“会战”一词才能更显出它浩大的声势和磅礴的气势。
洛阳会战是李世民一生最经典的代表战例,可以作为教案写入战史教科书。这场战役胜利的取得,除了唐军的勇猛顽强,李世民个人的指挥能力、军事水平以及坚韧不拔的意志发挥了很大作用。
当然,李渊的后勤保障工作也做得十分到位。在长达十个月的会战时间里,唐军大量人马从未有过粮草之忧,各种战争所需的物资在李渊的亲自安排督办下,通过黄河和渭河水运直达洛阳战场。即使在北方突厥和梁师都侵扰边境期间,东方战场的后勤供给依然保障有力,丝毫没有影响军粮供应。
可见,一个伟大王朝的建立,必须要有一帮伟大的人物在关键时刻严丝合缝地密切配合,一根独木是撑不起皇宫大厦的。而王世充和窦建德就是独木不成林的牺牲品。这两人要是真心联手,对李唐来说,就是一坚硬的“双截棍”,随便怎么“哼哈”,唐军也奈何不了他们。当年曹魏那么强大,尚且一人难敌蜀吴四手,如果两人一开始就合纵联兵,共同进退,李唐是拿他们没有办法的。当时唐政权的实力虽然足以傲视群雄,但还没有强大到能一下吃掉两大军事集团的份上。本来李渊就是计划各个击破的,但没想到自己那个“全无敌”的二儿子却奇迹般地一击两破。这就是传说中的“种‘窦’得瓜”。种下去的是绿豆黄豆,收获到的却是西瓜南瓜,发大啦!
李世民在洛阳城内看到隋朝房地产公司老总杨广建造出的巍峨宫殿群,感慨万千地叹道:“逞侈心,穷人欲,无亡得乎!”
的确如此,一个铺张奢靡、无休止地放纵个人私欲的皇帝,任何时候都避免不了灭亡的命运。攻克洛阳后,李渊曾指示李世民将象征隋炀帝暴政的高门大殿尽皆烧毁,但很有些勤俭持家头脑的李世民觉得烧掉太可惜,便向父亲建议改烧为拆,将木料和瓦片分给城内居民二次利用。这本是件既实用又环保的好方法,但李渊为扩大政治影响,没批准儿子的做法。没想到皇帝这个最高领导也热衷于“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比较一下,当时焚烧宫殿的行为和现在动不动就集中焚烧盗版书籍、假冒香烟的做法如出一辙,醉翁之意不在“烧”,而在于看烧和看不见烧的人。
以现代人的眼光看,这种快意焚烧是严重破坏文物的恶劣行为。不过,在中国数千年的改朝换代史中,焚烧已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常态,好似当下很多新上任的地方一把手总不愿再坐上一任的公务用车一样,每一次大的政局洗牌都无一例外地伴随着不灭的大火。上下五千年,火龙漫天飞。冲天大火照不亮点火者心灵的黑洞,熊熊烈焰烤不软施暴者的铁石心肠。如果没有这些来来往往的祝融先生,中国的古代文明将比现在不知璀璨多少倍!
烧完了乾阳殿等宫廷建筑后,李世民又在佛教兴盛的洛阳对佛教徒采取了削限措施,下令废止城中过多过滥的佛寺,并强制僧尼蓄发还俗,只留下了几十位德高望重的专职僧尼,拉开了唐政府第一次抑佛政策的序幕。
佛教自西汉末年开始从天竺(即今天的印度)传入中国后,到唐朝时已有六百年的历史。
整个唐朝,佛教和道教两派因争夺最高统治者青睐的斗争一直都很激烈。从实际情况看,在这场佛道之争中,道教占了上风。特别是在唐初,道教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原因大家都知道,唐高祖李渊说他的老祖宗就是《道德经》的作者、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李耳。凭着大唐一哥祖爷爷这层硬关系,道教在唐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一教独大。但唐初抑制佛教的最深层原因还是因为经济问题。因为当时的寺庙大都拥有众多田产,庙里的僧尼都属于“特权人士”,不需要向朝廷缴纳租赋,这种富庙富方丈的现象导致僧尼越来越多,而僧尼越多,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就越少,国家的赋税征收也就会跟着受到影响。所以,刚经历激烈战争,急需休养生息的唐初政权不可能容忍这样严重影响国家GDP事情的长期存在。
李世民在洛阳向“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的僧尼的首次亮剑就代表了唐政府的这种意图。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名闻遐迩的“少林寺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就发生在李世民和王世充的洛阳攻战期间。只不过这是一个经过艺术加工的虚构故事,可以确定历史上没有发生过这件事。这么重大的事情,如果属实的话,正史上是不可能没有任何记载的。更何况,少林寺和尚的绝世神功多半只存在于“成人童话”的武侠小说中,而现实中,和尚们的再武功高强,也难高过尉迟敬德、秦叔宝这些长期充当李世民贴身保镖的高手。李世民手下有一个勇将如云的庞大将军群,即使是遇到危险,也轮不到少林寺和尚去救。况且,“十三棍僧救唐王”这个故事的标题就很“演义”。“唐王”这个称呼就很模糊化。李世民从未有过“唐王”这个封号。登基前他的最高职称一直是“秦王”,而登基后就该称“唐皇”了。在这个故事发生的时期,“唐”是一个国家的名称,它的后面如果配上“王、皇、后”这些至高无上的名词,就代表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而当时有资格拥有“唐王”这张名片的只有李渊一人,而李渊却根本没有来过洛阳。
唯一一点不可否认的就是,少林寺僧人确实帮助唐军对付过抢占了少林寺寺庙土地的王世充军队,战斗结束后,李世民还特地给少林寺颁发了“表彰决定”。现存于少林寺内的《李世民碑》,正面镌刻的就是李世民的这个“表彰决定”,内容记录了少林寺僧众的战功,上面还有李世民亲笔草书的“世民”两字签名。有机会去少林寺旅游的朋友不妨仔细欣赏一下这个军事天才的书法真迹,因为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皇帝,也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
再说窦建德的老婆曹氏与夏国左仆射齐善行等人从虎牢关带着几百人逃到洺州后,就聚在一起商量以后的路到底怎么走。当时夏政权还拥有洺州、魏州和相州等地盘,具体位置处于今天的河北南部和河南北部交界地带,就是现在的河北省永年、大名两县以及河南省安阳市。这些后窦建德时代的夏国将领提出了两个发展方向:
第一,立窦建德养子为皇帝,继承先皇“遗志”,继续高举旗帜,和李唐针锋相对。
第二,在这里放开手脚大肆抢劫一番,然后满载北上,到海边落草为盗。
这两种方案都有个相同的特点:不与李唐为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