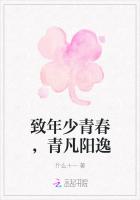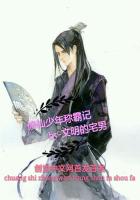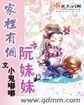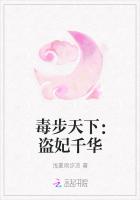站在没有死亡痕迹的自杀现场,我不知道死者最后一眼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的是斜坡下面那一口被工厂的油污覆盖住的水塘。附近的农民每年都将水塘里半死的鱼打捞出来在路边出卖。因为价钱便宜,鱼每次都是一抢而光。当然,我还看到了几步远处的那棵半死的矮树。那上面曾经有一个很大的马蜂窝。所有人都说马蜂窝捅不得。我早就听腻了捅马蜂窝的后果。但是,在1974年暑假里的一天中午,我还是用好不容易找到的一根长树枝,用力朝那个马蜂窝捅去。惊飞的马蜂中的一只闪电似的朝我飞来。众所周知的后果立刻凸显在我的额头上,吓得我拔腿就往设在招待所一层的工厂医务所跑去。我比《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提早四年认识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里发表的那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是1978年最有特色的理论动态)。
1978年底,中国正开始朝世纪末的“四个现代化”跑去。可是,从北京出差回来的人却带来了《第五个现代化》的消息。我认识的一个年轻人激情地将文章油印出来(我一度是他油印的帮手),四处散发。与大摇大摆的“赛先生”不同,“德先生”走的是地下通道。但是,这丝毫也没有降低它的身份。我们一见如故。它与我的荷尔蒙联手,诱发我的叛逆。我开始与生物上的父亲冲突,我准备与精神上的父亲决裂。对七十年代的许多少年来说,这两个过程相辅相成。我与父亲的冲突都是由大是大非的问题引起:他主张姓“社”,我主张姓“资”;他要“基本原则”,我要“绝对自由”。有好几次,我们的冲突几乎以武斗的形式结束。其中一次,我举起了一只茶杯,险些朝“社会主义”砸过去。
在这“你死我活”的关头,父亲被调往离长沙八十公里远的益阳地区,主管当地的经济工作。他的离开为我青春期的自由发展扫除了障碍,又在我生命的旅途上标出了一个新的车站。但是,我们的家庭又一次被拆散了。与生命一样,“家庭”也是七十年代廉价的牺牲品。
11
与科学的“春天”相比,1979年北京的“春天”显得非常短暂。二月中旬,战争爆发了。它转移了所有人对位于西单的那一堵矮墙的注意。与我们在儿童时代参与的战争不同,这是七十年代唯一的一次实战。我兴奋异常,密切注视着前线的动向。我盼望着“我军”尽快攻入凉山,同时也有点犹豫不决,不知道在那之后是不是应该继续南下,拿下河内。我已经不再是那个滥用核武器的孩子,我已经被爱因斯坦为原子弹爆炸留下的眼泪深深地感染。胜利已经难以冲昏我的头脑。对伤亡的敏感正在悄悄改变我对战争的看法。这种敏感最后将演变成对一切战争的厌倦和反感。
1979年忙于为活人摘帽,为死人追悼,是活人和死人都很受重视的年份。但同时,它却通过战争炮制了更多的死人。这是历史中常见的荒谬。那些死去的生命当时与人民币的比价让“人民”和“人命”都蒙受羞辱。而后来随着边境贸易的活跃,那种死亡变得比鸿毛更轻。1979年的战争引起了我对战争的思考。这些思考为我后来的“战争小说”奠定了基调。
同样,1979年在忙于摘帽的同时,又给更多的人戴上了那顶传统的帽子。这也是历史中常见的荒谬。政治生命的结束并没有降低我对政治的激情。3月底的拘捕和十月底的审判使我对权力失去了敬意。“反革命”、“右派”和“野猫”在幼儿时代是母亲用来恐吓我的“三剑客”,据说只要提及其中的一位,我的哭声就会戛然而止。1979年,野猫已经叼不走我,而绝大多数的“右派”又都摘了帽,只剩下“反革命”还能够惊动我的神经。但是,这一次,我不是因为恐惧而受惊,是因为怀疑。“反革命”作为一种1979年的罪过诱发了我对“革命”的怀疑。这是我自己的思想解放。这怀疑将在未来开花,最后结成一系列文学的果实。
1979年用喧嚣和骚动构筑了我意识形态的分水岭。七十年代很快就要结束了。那个想让自己的历史保持“鲜红鲜红的颜色”的少年经历了一场语言的血崩。他在表格里不得不填写的“坚决拥护”已经词不达意。他的“自我”已经开始膨胀,而他的“超我”被比“基本原则”更基本的人性的原则取代。语言本身的造血功能让我的语言顺利地完成了最关键的新陈代谢。来自过去的语言终于向过去告别。
发生在1979年的两次搬家使这一年的告别变得更加具象。在秋天里,我们搬离了与那么多集体和个人的记忆纠绕在一起的工厂家属区的房间,搬到了位于工厂对面的母亲工作的学校(也是我自己的母校)。“沸腾的生活”从此淡出我的生活。
二十六年后,我带着十五岁的儿子,“不远万里”,从地球的另一侧回到长沙,去寻找那七十年代的“故地”。我们在生产区的见闻完全是另外的版本:没有声音、没有人影、没有任何的生机。我所有的记忆和叙述都变成了谎言。工厂已经停产好几年了,大部分土地和机床都已经出卖。在变得十分狭窄的家属区的入口,我终于看见几个正在阴影中乘凉的老人。这很像是马可·波罗在《看不见的城市》的第二座“记忆之城”里目睹的场面。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们,那些“欲望已经变成了记忆”的老人。我记得他们二十六年前的样子以及他们生活中的一些故事。同样我想,他们可能还记得当年总是穿着工作服在车间劳动的那个瘦弱又懂事的孩子,那个“党委副书记”的儿子。但是我肯定,他们没有认出我,或者通过我身边的少年认出我。
而夏天的搬家终止了我与农村的对话,它对我生活的影响也许更为复杂。
七十年代几乎所有的寒暑假,我都会去宁乡县历经铺人民公社立新大队第四生产队看望外公外婆。外公曾经是沈阳一家大型国营工厂里的会计。“四清”之后携全家回到宁乡老家务农。他不可能预计到“浩劫”的到来,也不会想到他个人的成分有机会由“职员”升格(或者降格)为“地主”,令“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就像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爷爷一样,在1979年夏天的那个中午之前,我经常见到的外公也并没有作为一个外公而“存在”。在我的眼中,他只是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而且,我像其他孩子们一样,对他十分惧怕:原因之一是我知道他的“地主”身份;原因之二是他很少说话,从没有笑脸。他总是微微驼着背,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里,抽着他的“喇叭筒”(自制的卷烟)。他与我外婆的包办婚姻符合辩证法的著名规律,是名副其实的“对立统一”。我外婆幽默、“阳光”、有取之不尽的故事。她已经95岁了,仍然能够一字不漏地背诵《长恨歌》和《琵琶行》等古典诗文以及《鸟儿问答》等现代诗篇。她在七十年代的日常生活中经常用伟大领袖的伟大诗篇对我进行生动的义务教育。
我保留着外公于1969年写的一份交代材料,他在那里面交代了自己的“历史”问题。像七十年代的许多年轻人怀着“崇高的理想”加入共产党一样,他在国难当头的1939年集体加入过当时正在领导抗战的执政党;像现在的许多年轻人向往稳定体面的工作一样,他在风雨飘摇的“行政院”做过一段时间(不到两年)的公务员。背着如此沉重的历史包袱,他的七十年代与我的七十年代当然会截然不同。我不知道当他经过整天的批斗和整夜的逼供之后回到自己的茅草屋里,除了沉默之外,是否还想到过其他的出路。
可是,1979年夏天的那一天中午,外公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那一天,我跟着一辆大卡车去乡下给他搬家。他那样的兴奋,忙进忙出,忙上忙下。他满脸的笑容,他讲了那么多的话。那一天是他翻身做主的日子。他不再是“地主”了。因此,他也没有必要再当农民了。母亲要将他接到城里去。他将永远离开那曾经属于他的父亲而他自己又在上面辛勤耕作过的土地。
我坐在卡车的驾驶室里,突然有点怀念那位“不存在的”外公,不仅因为他为我提供了一个度假的场所,还因为他向我展示过一个另外的语言世界。那是1974年春节中的一天,我无意中打开外公桌子的抽屉,在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中间,我竟看到了一本书。那本很旧很小的书的封面上只有两行我认识的字。一行是“李耳王”;另一行是“莎士比亚”。我不知道这两行字是什么意思,彼此又有什么联系。我大概能猜到第一行是一个人名,这个人的耳朵应该很大,等等。八年以后,在装外公遗物的小木箱里,我又见到了那本书。那是我一生中见过的第一本英文书。在现实中,它的出现是七十年代的一个意外,而在我的想象中,它的出现是生命的必然。
1982年寒假过后,刚刚告别外公回到北京,我就接到他因脑溢血突然去世的消息。这轻如鸿毛的死亡在我已经有点存在主义意味的日记里留下了沉重的痕迹。这离我最近的死亡将七十年代的阴影更深地带进了一个新的年代。
12
对我来说,七十年代是“死亡的年代”。一生中只会遭遇一次的神死了。那些可爱和可恨的半神,以及先可爱后可恨(或者先可恨后可爱)的半神也陆陆续续死了。不少熟悉的凡人也以不同的方式死去。而一位可能已经不在人世的工人甚至对我的寿命也作出了悲观的估计。死亡是我的恩师:它向我指明了生命的极限,它解除了我关于生命的疑惑,它教育我卑微地活着。
生活是不断的告别。然而,我不可能向用死亡教育我和用语言哺育我的七十年代告别。那个年代为将要用语言回报语言的生命编制了详尽的基因图谱:痛苦、躁动、虚荣、恐惧、羞辱、满足、谬误、隐秘……一个年代的副本其实就是一个生命,或者一个生命的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