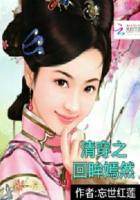张问陶的论诗诗,时间跨度之大,涉及人物之广,体式之全面,世不多见。其论诗诗有五古七古,也有五言、七言绝句。各种诗歌体式在船山论诗诗里运用自如,难分伯仲。在论诗诗内容上,元遗山《论诗三十首》所评诗人自魏晋至宋;王士禛《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首》,品鉴自汉末建安时期至明代一些诗人;袁枚《仿元遗山论诗》所评仅限于清代诗人;张问陶论诗诗所评诗人自屈原至船山生活的清代乾嘉年间。评论作品自《诗三百》开始,如《蟋蟀吟》、《秋燕飞》6二首自序言:“《诗》三百篇,大抵贤人发愤之作为。”论诗诗之外,还有论文诗及大量论画诗,扩大了以诗论诗的范围。但船山论诗诗的贡献不在于此,而是打破了论诗诗在重理论阐释方面的瓶颈,打破了论诗诗在纯粹的理论阐释方面历来缺少影响的局面。
论诗诗既为诗歌,又是理论。诗歌要求韵味、具象,而理论则讲究思辨、抽象,两者相互难容。前人在创立论诗诗这一体式时,其实已经把矛盾潜伏于诗体之中留与后人。杜甫《戏为六绝句》以诗体形式来表达诗歌见解,开创了以组诗论诗的先河。自杜甫作《戏为六绝句》,戴复古、元遗山承其衣钵,“各得其一体。戴氏所作,重在阐说原理;元氏所作,重在衡量作家”,7成为后来论诗诗的两大支派。不可否认,元遗山的论诗诗融完整的文艺思想于一个个具体形象的作家作品的个案评骘之中,妥善处理了论诗诗创作中感性思维与理性批评结构中的一与多之间的关系,创造了论诗诗史上杜甫之外的又一种典范,并以其新发展新成就,一跃成为论诗绝句史上新宗师。但应注意的是,元好问与杜甫在论诗诗的表现领域是殊途同归的。阐发诗歌创作原理,尽管是杜甫以诗论诗中的一项内容,但毕竟只占极少的份额。而元好问的论诗诗虽阐发诗歌理论,也只是将其融入对作家和作品的批评中。换另一个角度说,聪明如遗山者在表现领域的选择上的扬长避短是对杜甫的继承,又未尝不可说是对论诗诗重点阐述理论这一难题的有意的回避。从现有资料看,以阐述艺术创作观点为主的论诗诗当滥觞于南宋戴复古的《论诗十绝》。戴氏(包括吴可等人)论诗专门探讨诗歌理论,在论诗诗的表现领域方面,是对杜甫的继承和发展。戴氏之初衷从其《论诗十绝》“续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句能够得以充分解释。遗憾的是戴氏有超越杜甫之勇气,却乏杜甫之才力,殊难深入到诗学内核,只能泛泛游谈诗理而已。从论诗诗的历史发展看,元好问的影响要远远超过戴复古,论诗诗的两大支派的发展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这里虽由各自论诗诗的成就所致,但也与二人的论诗诗所选择的表现领域的难易程度不无关系。衡量作家属于实际批评,阐述理论则为理论批评,后者的难度要远远地超过前者。尽管戴复古未能如元好问般影响之大,但其创立论诗诗的新范式,敢为人先的学术勇气和拓荒精神是值得肯定的。戴氏之后,论诗诗之纯粹阐述理论的领域冷冷清清,这种状况直到清代方有所改观。以诗论诗的形式清代甚多,或重在阐述诗歌创作的理论原则;或重在品评作家作品,由此表述论诗见解;或既论作家也谈诗论艺。但清人的论诗诗,大致亦不外乎两派——阐述理论和评论诗人。前者如赵执信、宋湘、张问陶等,尤以张问陶为代表。张问陶的论诗诗创作,也有对诗人诗作的批评,但总体上是以阐述诗歌理论为主,又兼评诗人。可贵的是,船山并非抽象的议论和分析,而是采用诗化的语言,以诗作为表达自己诗学主张的工具。在张问陶的论诗诗中,诗服务于诗论,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为“论”而“诗”,突出了论诗诗之“论”的特点。打破了以往论诗诗“诗”之特征明显,“论”之特征不彰的局限。可以说船山论诗诗的独特贡献,在于承继了戴复古开创的以诗歌来阐述诗歌理论的传统,发展和完善了子美、遗山之外的另一种论诗诗的范式。中国文学批评,实际批评所占的比重远远超过理论批评,原因诸多,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应该是理论批评相对来说难度要大于实际批评。张问陶完全有理由像大多数清人那样,沿着杜甫开创、元遗山发展的已臻于成熟的论诗诗的路子轻松地走下去,或衡量作家,或融理论阐述于作家品评之中。但是张问陶却知难而上,自觉地循着由戴复古开创、后人极少问津的在论诗诗中重点阐述诗歌理论的路子艰难地行进。在论诗诗阐述诗歌理论方面,如果说戴复古有开创之功的话,张问陶则有弘扬光大的杰出贡献。
张问陶论诗诗分析
《论文八首》、《论诗十二绝句》、《题屠琴隖论诗图十首》、《冬夜饮酒偶然作》、《赠徐寿徵诗》、《题朱少仙同年诗题后》、《颇有谓予诗学随园者笑而赋此二首》、《题法时帆(式善)前辈诗龛向往图》、《题方铁船工部元鹍诗兼呈榖人祭酒》等论诗诗,集中反映了张问陶的论诗主张,本节予以逐一分析。另外,散见于张问陶其它诗篇中的用以谈诗论诗的诗句的数量也不少,将于着重于他的论诗诗的解读,并从中探寻张问陶的诗学观。
《论文八首》8
甘心腐臭不神奇,字字寻源苦繫縻。
只有圣人能杜撰,凭空一画爱庖牺。
一代舆图妙斩新,薄今爱古转陈陈。
寻名枉受翻书苦,乱写齐秦误后人。
职官志表辨兴旺,忍署头衔属汉唐。
此事好奇奇不得,特书人爵要遵王。
识字何须问子云,强依篆隶转纷纷。
写书累煞诸名士,搦管迟疑画《说文》。
笺注争奇那得奇,古人只是性情诗。
可怜工部文章外,幻出千家杜十姨。
志传安能事事新,须知载笔为传真。
平生颇笑抄书手,牵率今人和古人。
诗中无我不如删,万卷堆床亦等闲。
莫学近来糊壁画,图成刚道仿荆关。
文场酸涩可怜伤,训诂艰难考订忙。
别有诗人闲肺腑,空灵不属转轮王。
《论文八首》作于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二月,是年张问陶三十岁,正值诗歌创作的高峰期。四十岁以前是张问陶诗歌创作的主要时期,诗人全部诗作的三分之二都完成于此期,每年写诗数百首也是寻常之事。仅写作《论文八首》当年,就存诗二百四十篇左右。写《论文八首》时,诗人进行诗歌创作已经有十五年之久。所以,这组最早的集中探讨诗歌理论的论诗绝句,也是张问陶从多年的学习和创作实践中总结出的理论认识。张问陶的《论文八首》旁征博引,引经据典,但还是有着一个统一的主旨贯穿全诗,这就是对于文场中矫揉造作,生硬模仿,训诂考证等不良之风的批判。首首都是反对当时文坛写古字,用古地名、官名,讲考据,重摹拟等弊端。《论文八首》以破为主,又破中有立,其中五首(二、五、六、七、八)兼及论诗论文,不乏对文学本质问题的讨论,虽不够系统和全面,却可透视张问陶早年的诗学思想。
甘心腐臭不神奇,字字寻源苦繫縻。
只有圣人能杜撰,凭空一画爱庖牺。
神奇的作品能获得无限的、新生的意义。超现实主义的理论发言人布勒东曾极端地宣称:“神奇永远是美的,任何神奇的事物都是美的,甚至只有神奇的事物才是美的!”我国古代也十分重视对艺术表现上“神奇”性的强调,而艺术上的“神奇”离不开语言的提炼。文学尤其是诗歌,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最本原而且最本真的艺术,诗歌语言应该具备“化腐朽为神奇”的功能。相反若执于文字的寻根求源,则难达“神奇”之效。庖牺氏(伏羲氏)“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创造文字,其实是原始先民满足日常活动的共同需求,决非某个“圣人”杜撰。而且文字自产生之日起,就随着现实社会活动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修正和补充。张问陶在此批评训诂考据等不良文风,学宋人所谓“杜诗韩笔无一字无来处”的陈规陋习,有违文学抒情的本质,所作诗文毫无价值可言。
一代舆图妙斩新,薄今爱古转陈陈。寻名枉受翻书苦,乱写齐秦误后人。
舆图之名,来源于古人“天地有覆载之德,故谓天为盖,谓地为舆”。一代之舆图贵在与他朝有异,其妙在崭新。无奈地图修订者不谙此理,薄今爱古,陈陈相因。为寻一地名,遍检古书,到头来费时耗力,乱写了齐国和秦国,不仅徒受翻书之苦,且贻误后人。文学是一种创造活动,创新是文学作品的生命,创新应该是每个作家的自觉追求。张问陶的这首诗旨在借古讽今,批判拟古者的厚古薄今。
职官志表辨兴旺,忍署头衔属汉唐。此事好奇奇不得,特书人爵要遵王。
“人爵”与“天爵”相对,源自孟子的《孟子·告子上》。孟子言:“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孟子所讲的“要人爵”,即把“学”作为追求名利的手段。职官作“志、表”乃记录一代的典章制度,作用在于全面认识兴亡史。但署汉唐两朝的职官为显尊贵,置撰写目的于不顾,强署职位与姓名于“志、表”中。张问陶反对以诗人名世,这里借用孟子的说法,影射了文学创作中重外在因素而忽视本质的做法,实为沽名钓誉之举。
识字何须问子云,强依篆隶转纷纷。写书累煞诸名士,搦管迟疑画《说文》。
我国最早的字典是东汉许慎编的《说文解字》,最早的方言词典是西汉扬雄(子云)的《方言》。识字、认字、写字,缘何必须查检扬雄的《方言》,其实完全可以博采众长,在篆书、隶书之外,另辟一种妍美流便、雄逸俊雅的新书风。名士们每逢执笔,迟疑再三,总要以《说文解字》为蓝本。如此写书,煞是辛苦。本章继续批评不事创新,依傍门户,不能生面独开,落入他人窠臼的拟古派。
笺注争奇那得奇,古人只是性情诗。可怜工部文章外,幻出千家杜十姨。
“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传统诗论中古老的论题。尽管在后来的发展中,诗论家根据不同的目的,各取所需,但“诗以道性情”,几乎是一致的认定。即便汉儒的“诗教”说也仍未摆脱性情的阐发,只不过在他们那里,“性情”被囿于温柔敦厚之中而已。“性灵”说是张问陶诗学的灵魂,且贯穿于张问陶的诗歌创作的始终。张问陶主张诗歌抒写性情,认为古人的诗是自我内心的真实抒发,是出自肺腑的“性情诗”。作诗必须“自吐胸中所欲言,”才能写出天然浑成的自然之趣,充满人情的真诗,即所谓:“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不过近人情”9。但是当时的诗坛却将教条的“义理”、“考据”文章”奉为正宗。为此,张问陶有意选用宋元笑话“二男相配”10中的部分内容,匪夷所思地与“千家注杜”11相联系,对当时的不良文风予以辛辣的讽刺。
志传安能事事新,须知载笔为传真。平生颇笑抄书手,牵率今人和古人。
文学创作如同自然物的生存一般,不当掺以丝毫的矫揉造作。撰写志传文体有着特殊的要求,即真实地记人录事。“真实”是志传体的基本要求。徐复观在《中国文学论集》中云:“真正的好诗歌,它所涉及的客观对象,必定是先摄取在诗人的灵魂之中,经过诗人感情的熔铸、酝酿,而构成他灵魂的一部分,然后再挟带着诗人的血肉以表达出来,于是诗的字句,都是诗人的生命;字句的节律,也是生命的节律。”12但规唐摹宋者,既忽略文艺抒情的本质,又无视时代的变更,今古不分,实有牵强附会之嫌。
诗中无我不如删,万卷堆床亦等闲。莫学近来糊壁画,图成刚道仿荆关。
诗歌必须渗透着诗人自己的感情色彩,即“诗中有我。”袁枚强调写诗从“自我”出发,表现诗人的独特个性。“作诗不可无我,无我,则剿袭敷衍之弊大。”13。张问陶更是明确指出:“诗中无我不如删,万卷堆床亦等闲。”拟古者的无我之诗,但使万卷堆床亦枉然。后句“莫学近来糊壁画,图成刚道仿荆关”,采用比喻,讥刺跟在古人身后,亦步亦趋的诗风。五代的山水画,尤其是水墨山水画进入了成熟阶段,画家体味生活,将所见自然环境的特色,用不同技法加以再现,形成了不同的风格流派。在北方,以荆浩、关仝师徒为代表,素称“荆关”。张问陶工书画,他在此即以画论诗。诗中无我,如同绘画的一味仿古。画虽完工,但无较高的水准,难出荆关之右,只能供人糊壁而已。
文场酸涩可怜伤,训诂艰难考订忙。别有诗人闲肺腑,空灵不属转轮王。
感情是诗歌的灵魂,—首好诗,必须是作者强烈的感情与生动的艺术形象的统一。如同朱光潜在《谈文学》中所言:“一切艺术都是抒情的,都必表现一种心灵上的感触。不表现任何情致的文字就不算是文学作品。”诗歌创作,或直抒胸臆,或借景抒情,或托物言志,或因事缘情。只要是源于诗人内心,则易达到超凡脱俗的空灵之境。王夫之在《姜斋诗话》里说:“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则自由灵通文句,参化工之妙。若但于句求巧,则性情失为外荡,生意索然矣。”在王夫之看来,好诗当从胸中溢出,也不排斥文句之灵通。但过于追求字句之巧,则伤其真美。张问陶认为翁方纲之流的考据之学,忙于训诂和考订,虽有史料的价值,却缺少诗歌的艺术性。14本章还指出了创作主体的心“闲”问题。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