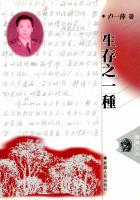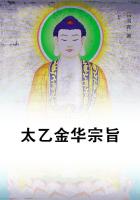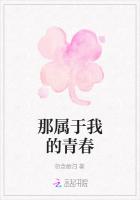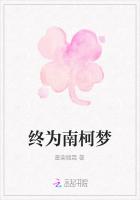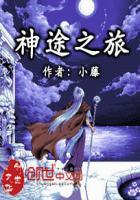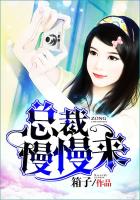“认真地考察从真实作者到文本叙述者的心灵投影方式,在许多场合往往具有解开文本蕴含的文化密码的关键性价值。”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00.吴组缃的小说多选择第一人称叙述,通过“我”的多重角色,变换叙述视角,展开文本叙事,从而增强故事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以冷静但不冷漠的叙述模式展现客观现实,尤其是技法圆熟的速写,更是借“缩影”来显示社会生活的全貌,形成其小说精确、细密,又蕴含巨大情绪力量的叙事风格。本文即从以下三方面,结合文本就吴组缃小说的叙述艺术展开分析。
一、第一人称叙述
茅盾曾在《读〈呐喊〉》里说过:“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10多篇小说几乎每一篇有每一篇的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去实验。”吴组缃当属这些青年中的一个。鲁迅的《呐喊》、《彷徨》中有25篇小说,几乎一半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吴组缃现存的小说中,采用第一人称叙述的作品也占了半数。吴组缃曾经解释说,选择第一人称叙述方式来叙事,是因为“用第一人称,它的视角比较单纯……第一人称口气比较亲切一点”,吴组缃,苑外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138.“好像觉得这样写比较容易下笔些”。吴组缃,苑外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168.其实,这是一个叙事角度的问题,采用怎样的叙事角度是作者的一个叙事谋略,绝不仅仅因为“容易下笔些”。用第一人称写小说,看似娓娓道来,信笔走去,其实不易,存在各种技巧。第一人称叙述的真正困境在于叙述者形象的构成上。由于这类叙述话语的魅力主要维系于叙述者的独白,这就要求叙述者必须具有独特的个性气质,否则,在同一作家那里,用第一人称写作的文本中的叙述者往往容易千人一面,从而影响一部作品的风格化。吴组缃诸篇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是不尽相同的,通过“我”的多重角色,变换多种叙述视角,让读者领略了文本更深层次的蕴意,细细品味不难发现作者的匠心。
(一)“我”——叙述者
采用第一人称“我”进行叙述的最大好处,首先在于真实感强。伴随真实感而来的是一种亲切感,即没有距离,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显得真诚、坦白。吴组缃在《离家的前夜》、《黄昏》、《卐字金银花》、《铁闷子》等作品中,以第一人称“我”作为视点:“我”在离家的前夜,目睹了作为知识女性的妻子“蝶”,想要离开“没落的封建乡村”、“寂寞古旧的家庭”和襁褓中的婴儿,去追求“活跃的、前进的、充实的生活”,却被重重羁绊所阻挠,最终不得不放弃学业,带着无限幽怨,留守家中,做了贤妻良母(《离家的前夜》);“我”回乡歇暑,黄昏在自家小院纳凉,却听到院墙外嘉庆膏子的叫卖声,天香奶奶寻猪的锣声,三太太的喊魂声,松寿针匠妻子的哭号声,桂花嫂子的刀板咒声,更夫老八哥的怒骂声……这些声音正诉说着一个个与“贫”、“病”、“死”、“偷”、“倒闭”、“失业”、“谷践伤农”等字眼相关联的悲惨的故事,使“我”窒息,家乡凋敝破产至如此惨状,“我”不知家乡“几时才走上活路”(《黄昏》);“我”童年偶遇一个喜爱“卐字金银花”的姑娘,并结下纯真的友谊,可成年后再次相遇,却看到已成寡妇的她,“做了社会不容的事”,被逐出家门,孤苦无助,最后在荒郊的残垣断壁中难产而死(《卐字金银花》);“我”作为前线报人,耳闻目睹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但也亲眼看到一个“逃兵”的英勇献身,客观揭示了在全民族的抗日热潮中,光明与黑暗的两面(《铁闷子》)。
小说中,“我”作为故事的叙述者,现场的旁观者,向读者讲述“自己”的亲见亲闻,读者误把“我”当作者,对文章的原始性和珍贵价值信之不疑。但由于第一人称限知视角,读者只能跟随叙述人了解“我”的所见所闻,至于“我”不曾知晓的情节,作者巧妙地通过“第三者”来完成。如《黄昏》中每个声音背后的故事,是通过“妻子”的“解说”来完成的;《铁闷子》中,作者在“逃兵”出场前不惜用了大量笔墨描写“第三者”——勤务兵“刘大开”的善良、淳朴、勇敢、正义,篇末通过“刘大开”,介绍了“逃兵”在正义的感召下,思想觉醒,准备重返战场,却为保护列车和他人的安全而壮烈牺牲的过程。至此,读者也就自然将“逃兵”与“刘大开”联系在一起,“逃兵”是在国民党部队沾染了恶习,犯了命案,想潜逃回家,其实,他的“本质是好的”,和“刘大开”一样,都属于淳朴、勇敢、正义的农村青年。小说这样处理让读者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二)“我”——叙述者、主人公
第一人称的情感判断与价值取向与隐含作者既有一致的一面,又有相悖的一面,甚至于叙述者从反面传达隐含作者的意图,造成不可信的叙述者,读者必须透过叙述者造成的迷雾去洞察作者的真实意图,这样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具有反讽性质。因此,第一人称写反面人物会达到批判的效果。《官官的补品》就是一篇采用非常独特的叙述技法写成的作品。作品也采用第一人称,即“官官”的自述。作品中的“我”既是叙述者,也是小说的主人公,叙述者与主人公“官官”的观点是一致的。“我”住在城里整日吃喝玩乐,因车祸险些丧命,输入乡民“小秃子”的血得以生还,因伤了元气,回乡调养,每日雇奶婆(小秃子的妻子)挤奶进补。贫苦农民的鲜血和奶汁成为地主阔少的补品,而农民出卖了自己的鲜血和奶汁仍然难以维持生计,“小秃子”只好当了土匪,最后被“官官”的叔叔为首的地主乡团活活砍死。小说以这个地主阔少的眼睛和意识活动为叙事角度,显然带着阶级的偏见,隐含作者对“官官”所代表的地主阶级的憎恨,透过“官官”那骄蹇和冷酷无情的自述渗透读者心里,使读者清晰地看到中国农村充满血腥味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感受到隐含作者对“官官”作为剥削阶级的思想、道德与价值判断的否定和揭露,这正是作家所追求的效果。吴组缃在这里的反讽叙述是一目了然的,读者可以轻易超越反讽叙述者走向隐含作者。因此,有学者认为,与鲁迅第一人称的运用技巧相比,这里的反讽只是一种戏剧化的修辞技巧;而我以为,文本中的隐含作者就是要通过“官官”的自供状,让读者直接面对这群吸血者的真实嘴脸,揭露“体面人家”的丑恶灵魂,引发读者共鸣,更直接感受农民的不幸与悲苦,使读者从否定的角度更清楚地看出地主阶级的“吃人”本质。
把“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作为一对关系来考察,不言自明,“我”的叙述态度并不代表作者本人的态度。这里,作者和叙述者拉开距离,“真实作者和叙述者的错位,以及由此造成的心理距离的接近和视角的偏斜,是能够使读者在真实感和迷惑的矛盾心理中体验着作品的审美张力的。”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04.反讽叙述,增加了小说作用于读者的心理张力,造成读者阅读心理上对叙述者的某种优越感,读者越过叙事者设置的障碍接近隐含作者的立场时就会产生对文本破译的快感,与作者取得默契的愉悦,从而在更大意义上实现阅读的本质,在阅读过程中体验自我的力量和获得自身的实现。从这一点来看,《官官的补品》无疑是一部成功的佳作。
(三)“我”——叙述者、故事人物、见证人
熟悉吴组缃作品的人没有不提他的名作《菉竹山房》的,在研究吴组缃小说的论著中,论者解读最多的就是《菉竹山房》。这篇以吴组缃的姐姐为人物原形的小说,讲述的是中国封建时代才子佳人的悲剧故事。这样一个情节简单的传统旧题却引人关注,叙述技巧是其一大特点。小说没有采用以女主人公为第一人称的叙述视点,而是以叙述者“我”的眼光来看二姑姑悲剧的故事。小说叙述了“我”与新婚的妻子“阿园”归乡探亲而接到二姑姑的邀请,接着通过“我”,追忆二姑姑红颜时代的故事。由于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传统故事,作者未加渲染,用极为简省的笔墨简单介绍之后作结:“这故事要不是二姑姑的,并不多么有趣;二姑姑要没这故事,我们这次也就不至急于要去。”因这段话,小说回到现实,“我”和妻子到了二姑姑家——菉竹山房。至此,叙述者仍是现在的“我”,但“我”并不仅仅是叙述者,还是二姑姑现实生活的见证人,成为小说里的人物之一。“我”目睹了二姑姑现在的生存处境,发现当年与公子遗像结婚的二姑姑,在锁闭了她一生幸福的菉竹山房里,营造了一个幻想中的夫妻世界,还有蝠公公(蝙蝠)、虎爷爷(壁虎)和青姑娘(燕子)等家庭成员,让我们看到了二姑姑在漠然、寡语的外表下那颗凄寂、悲苦的心。文章最后以二姑姑的“窥房”作结,有论者评论,“窥房”是二姑姑的变态心理的表现,揭示了封建制度对女性泯灭人性的摧残。而我以为“窥房”说明二姑姑对新时代年轻夫妻的好奇(或许还有羡慕),他们的到来,唤醒了二姑姑对自己永逝的年轻时代的爱情。由于叙述者也是人物之一,与主人公生活在一起,见证了二姑姑生活的真实,读者可以深切感受到封建文化埋葬了二姑姑一生的幸福,但却没有泯灭二姑姑内心深处的美好爱情,也正是因为这未泯的人性,二姑姑的人生更显悲戚。这就昭示着小说的叙述是真实可靠的,但吴组缃觉得还不够,在小说的结尾又加上一段话:
朋友某君供给我这篇短文的材料,说是虽无意思,但颇有趣味,叫我写写看。我知道不会弄得好,果然被我白白糟蹋。
原来“朋友某君”才是二姑姑故事的真正叙述者与人物之一,而“我”成了故事的转述者、旁观者。作者再一次转换视角,跳出故事,作为旁观者、读者。拉开作者与故事人物的距离,使读者更理智地观照叙述者讲述的故事,作为外在的观察者在更高的层次审视“朋友”讲述的故事,更易接受故事的真实性。有趣的是,这个结尾常被人忽视,甚至在有些选本里,这段话完全被删除。其实,这并非画蛇添足,从小说叙事学角度来看,“我”无论是故事的叙述者,还是故事人物,无论是隐含作者,还是转述者,通过“我”的多重身份,更增强了故事的真实可信度。
二、冷静但不冷漠的叙述
吴组缃的另一个叙述特点是冷静但不冷漠的叙述模式。吴组缃在创作时,基本上采取了对生活进行冷静谛视的态度——一种寓主观情感于客观描写之中的艺术方法,这也有来自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他特别推崇古代文学家所倡导的行文要“含蓄”、要“意在言外”、要“不落言诠”的“春秋笔法”,讲求写诗作文不把道理或议论直接明说出来,而要经过具体描写透露出来,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要求在创作中能像史家那样着重叙写人的言行事实,“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故此,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冷静但却爱憎分明的叙写。在《官官的补品》中作者有几处令人过目难忘的叙述。首先写官官的母亲对奶婆的态度。先是写母亲见了奶婆,又是给座又是让丫头倒茶,还不时逗逗奶婆的孩子。在这过程中,已观察了奶婆——“结实,也知礼。我喜欢。就是不知你奶子可好?”顺而提出验奶的要求,但奶婆不想解衣验奶,“奶婆红了脸,羞涩地再望一望母亲,但母亲已走到她身边,没奈何,只有忸怩地解开纽扣来”,“母亲以一个买客鉴别货品的神势把奶子凝神仔细看,伸过手去揉了一揉,豆浆似的白奶就望外直冒”。“看了颜色就知好”后,母亲安详地坐下来谈数目,“照平常说么,雇个奶婆到家里领小官官,是三块钱一个月。现在,我只要你每天来挤两次,你的毛毛是照常吃。——你们寒苦人,我也知道你们的难处,就让你一月拿一块半钱。”(仅是当时掺了豆浆的牛奶的四分之一的价格)字面上,吴组缃似乎不带任何情感,非常客观地叙述这一过程,但是,通过简洁的对话和细节描写,一个在“慈悲”的面纱笼罩之下,既精明又狡诈的剥削者形象跃然纸上。在她眼里,奶婆不过是一头会酿奶的牛,完全失去了人的尊严,在她那充满“体恤”之情的话语中,毫无商量余地地就敲定了这笔生意。作家正是在这冷静的叙写中,不动声色地写足了剥削者令人心寒的伪善。
再写官官看奶婆挤奶时,更是赤裸裸将奶婆与奶牛加以比照:“我远远地望着,觉得很有趣。这婆娘真蠢得如一只牛,但到底比牛聪明了:牛酿了奶子,要人替挤捏出来卖钱,自己只会探头在草盆里,嚼着现成的食。这奶婆,这只牛,却会自己用手挤,卖了钱,养活自己,还好养家口。我想,人到底比牛聪明啊!”作者用官官以为有趣的一段心理独白,揭露了剥削者视辛勤的劳动者为牛马,对用奶汁喂养他的农民的刻薄嘲弄,深刻表现了剥削者的冷酷无情,在他们眼中,“这世界真是个有趣的好世界,有了钱,原来什么东西都好买的”。这段独白,作者写得冷静,而我们似乎看到了作者笔端正喷射着愤怒的火焰,他正积蓄着满腔的激愤向读者控诉剥削者冷酷无情的罪恶——他们有钱,什么都不缺,唯一缺的就是人性。
另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叙述是陈小秃子在河滩上被刽子手乱刀砍杀的骇人场景:
小秃子押到河滩上,大叔叫那刽子手用脚踢倒他。可是刽子手踢不好,就胡乱用手把他推到在乱石上。这小秃子到死不降气,还故意把头颈贴在一块大石头上,扶也扶不起来。刽子手没奈何,双手把住刀柄,不住地抖,没法砍下去。大叔过去把他臭骂一顿,他才像砍柴似的乱砍了三四刀,把马刀口砍成狗牙齿。
看的人都严肃无声息,只有几个野孩子拍手嚷。
小秃子被砍了几刀,鲜血溅满在乱石上,已经僵卧不动,刽子手也被其他团勇扶着走了。忽然那尸首又挣扎起来,举着双手,像个恶鬼凶神似的放着尖嗓子叫嚷。大家都吓得向远处逃避,嚷的嚷,跌的跌……只有几个胆大的庄稼人走拢去,拾了大石头,对着那尸首的头如打蛇似的一阵乱击,白的红的溅满地。
一路上,人们谈论着“这龟子,该这么死”。这场凶杀的指挥者——官官的大叔竟然还“打趣”说:“这龟子的血现在可不值半文钱了,去年要卖五元一个夸特啦!”小说结尾写奶婆得知丈夫被杀,她哭嚷着扑向河滩时,却被同样死了男人的铁芭蕉嫂子一把拉住,“放着青蛙似的男人声音骂着说:‘你这婆娘才叫屎迷了心窍!你这老公就配零肉细剐——杀了还是造化了他!你不回去给我家官官挤奶子,却碰着五通神似的哭你娘的什么丧!你……’”这惨绝人寰的场景,这淋漓鲜血,还有这刻毒的打趣和同处被剥削地位的同类的冷漠和无情的辱骂,作家以冷峻无比的笔触,写尽了剥削者的凶暴和残忍,以及人性的泯灭。这一切都融化在冷静的客观描写之中,作家的思想、感情则隐藏在所描写的事情背后,冷静但不冷漠的叙述得到的是更加感人的艺术真实性。
再如《樊家铺》中女儿弑母的情节描写。本应是震撼人心的场面,但吴组缃却用了白描手法,简略的几笔就完成了惊心动魄的场面描写,将作家主观感情的评价隐藏在冷静的客观描写中。且看:
她看见烛台头上的那根尖尖拔拔的铁签。——说时迟,那时快,她倒过那烛台,对着娘头上猛力一阵乱扎。娘尖叫了两声,倒在床边,没响动了。
同样是杀人场景,一个是残忍、愚昧的刽子手暴行,一个是丧失伦理的弑母行为;一个写得鲜血淋淋、吵吵闹闹,一个是干干净净,没有什么声息。显然,前者作者是要通过这种残忍的画面,揭露剥削者泯灭人性的罪恶,从而激发读者对剥削阶级的愤怒和对劳苦农民的同情。而后者,作者要展现的并非是一个杀人场面,并非要引发读者对这种逆伦弑母作道德的谴责,而是通过这一事件,揭示出这一对母女的阶级观、价值观的矛盾。她们同处在被奴役、被压迫地位,“线子”要在痛苦的挣扎中寻求反抗,而母亲却千方百计要做稳奴隶;“线子”要钱是为救被捕入狱的丈夫,而母亲要钱是为了贪婪敛财。母女俩这一尖锐的矛盾冲突在之前的叙述中已作了大量的铺垫,在小说一开篇两人一来一往的问答中,这份母女情已可见一斑:
“娘么!”线子懒懒地说,“又回家去做什么?”
“回家做什么?回家去养老!娘也快要饿死了!”
“饿不到你头上来。”
……
“打了多少稻?莫问那个话。我们饿死也不问你老娘贷一个。你放心!”
“你这没有天良的×,你当娘怎么了?你当娘是个有钱的?你当娘腰里留着多少钱?”
“有钱没钱我不管。”
女儿的说话听在娘耳里,犹如生吞了几块冷石头。娘望望她那张冷硬的脸子,觉得自己的苦楚都无从说出来……
线子丈夫因抢劫被捕之后,线子娘知道了也不顾女儿的悲痛心情。小说是这样写的:
“恩爱!这样的女婿,真把我的脸都丢完嘞!不是我说狠心肝的话,就是真的平平安安出来了,这个女婿我也不能认:肉臭同味呀。”
……
“什么事这样要紧,放着在难中的女儿也不进去望一望?”
“她今天摇会。50块洋钱,可比女儿女婿要紧?”
因此,当线子救夫心切,急需用钱,而母亲中彩有钱却藏在包里不肯相助时,两人的矛盾冲突达到高潮,积蓄在线子心中的怒火与反抗力量一举爆发,顺势刺死了母亲。所以,这里的“杀人”只是她们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冷静的叙述只是为了展现客观的现实,用简明的语言,抓住典型的细节特征以传达出人物内在的神韵,而作者的思想感情已深蕴其中。这正是写作高手的匠心所在,也是吴组缃独特的冷静但不冷漠的叙述模式。
三、速写
“速写”是绘画术语,一般指用简练的线条在短时间内扼要地画出对象的形体动作和神态的简笔画,目的在于及时记录生活,反映现实。吴组缃的“速写体”小说正好印证这一解释,他把这一绘画技巧圆熟地用于文学创作中,写下了《一千八百担》、《卐字金银花》、《黄昏》、《女人》等多篇“速写体”小说,并得到很高的评价。茅盾在评论《西柳集》时,谈了两个感想,“速写体”是其中之一。他认为,“《西柳集》中诸篇‘速写体’的无例外的美妙”,使他的“速写”比正规的小说“光芒更觉炫耀”。茅盾,西柳集[J],文学,1943,三卷(5)。
常被提及的是两篇经典作品《一千八百担》与《黄昏》。《一千八百担》在标题中就点明这是“七月十五日宋氏大宗祠速写”。按理,“速写”的篇幅都比较短小,而这篇“速写”却长达两万多字,连茅盾都感叹:“这样长,这样包罗万象似的,这样有力地写出了10多个典型人物的‘速写’,似乎还没有见过。”茅盾,西柳集[J],文学,1943,三卷(5),并将两万多字基本都用在了典型人物的“速写”,他们每个人一个身份,一个典型,各有自己的容貌、思想和语言行为特征:老谋深算、虚伪贪婪的义庄管事柏堂;愚昧保守、麻木自私又攀高附上的豆腐店老板步青;工于心计、唯利是图的商会会长子寿;穷困潦倒的教员叔鸿;下流无耻的讼师子渔;无所事事的花花公子松龄少爷;老实可怜的塾师肃堂;磕巴的景元……他们各个登台亮相,出尽了洋相。小说没有突出、集中地塑造一两个中心人物,而是采取群像勾勒的方法,用白描手法,通过简明的语言,抓住典型的细节特征以传达出人物内在的神韵。
另一篇《黄昏》,字数只有《一千八百担》的四分之一,短小精悍,没有故事情节,只是一些错综缭乱的人生侧影。独特之处在于,除了家庆膏子和更夫老八哥照面之外,其余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但这些仅匆匆掠过的侧影,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挥之不去,集中展现了中国农村在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民不聊生的凋敝惨相。
吴组缃作品不多,却写出诸篇形式各异的“速写体”小说,难怪茅盾会称赞:“在‘速写体’上,吴先生常常能够造出这样惊人的‘神奇’来!”茅盾,西柳集[J],文学,1943,三卷(5),是什么原因使吴组缃特别擅长速写,而且成果骄人呢?茅盾分析说,是因为吴组缃没有较长的、连续的时间写作,无法构思连绵发展的故事,而速写则不受这一局限,这应当仅是原因之一。因为,速写要求作者有敏锐的观察力,迅速捕捉对象特征的能力。吴组缃从练笔初始就特别注意在这方面下工夫,这从他早期的散文、小说中不难看出。因此,他善于以简括有力的笔墨勾画出人物面貌和生活场景,借“缩影”来“显示”社会生活全体。虽只是些片段,却仍能折射出人生、社会的全貌。作者通过截取人物生活的一个片段作速写性刻画,以逼视人物内心灵魂的清醒而严峻的现实主义为基调,形成其小说精确、细密,又蕴含巨大情绪力量的叙事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