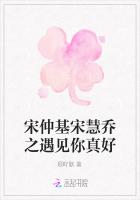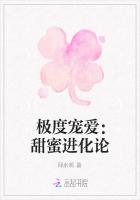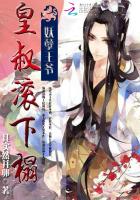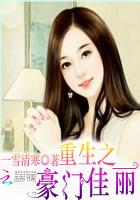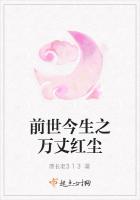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
看到这句话,相信很多人的脑海里就会出现这样的场景:
父亲是一个胖子,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色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朱自清,朱自清散文全集[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39.
这是我们所熟悉的朱自清的散文《背影》里的描述,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每每看到此,每个人的内心都会涌起一股暖流,那就是“亲情”。这篇写于1925年的文章,至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文章不过1300字左右,作者以平淡质朴的言语所勾勒出的世间最原始的父子之情,感染了无数中国人,为众人所称道。遗憾的是,如此美文,因为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一直以来引发的争议始终不断。2010年,《语文建设》第6期刊登了福建师范大学孙绍振教授的一篇文章,题为:《〈背影〉的美学问题》。孙绍振,《背影》的美学问题[J],语文建设,2010(6),文中援引了2003年武汉某校中学生认为《背影》中父亲的形象“不够潇洒”,且其穿越月台的行径“违反了交通规则”的观点,阐述了《背影》中错位的父子亲情乃是文章不朽的原因。他认为审美价值是以情感为核心的,情感丰富独特的叫做“美”。父亲为儿子买橘子,越是没有考虑到自己的人身安全、越是不顾交通规则,就越能体现一个“父亲”的情感;且他在爬月台时越是费劲,其形象越是笨拙不雅,就越能体现出父亲在面对儿子时的“无我”。这种对现代人来说毫无美感可讲的描写,其实是一种诗意,是真正的“美”。他说:“《背影》的动人之处,不仅是父子之情,还在父子之情的动态转化。文章的高潮是:一方面是强烈的转化,一方面是无所察觉,二者的对比,显出父亲的爱是无条件的爱。而儿子的爱,则是平静状态。这里就显示出了朱自清的深刻之处:他笔下的亲子之爱,是错位的,爱与被爱是有隔膜的。爱的隔膜,正是《背影》之所以不朽的原因。”不曾想,一石激起千层浪,又一次在学界掀起《背影》是否应从语文课本中删除的争论热潮。其中以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中文系老师丁启阵的文章——《我赞成把朱自清〈背影〉从语文课本中删去》丁启阵,我赞成把朱自清《背影》从语文课本中删去(博文),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00fe270100k3kd。html〉,的反响最大。
丁启阵针对孙绍振的文章从四方面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一是通过父亲穿越路轨一事来说明父亲违反了交通规则,为违法行为,而用违法行为去渲染父爱,是一种“病态”的美学;二是父亲攀爬月台时那费劲笨拙的形象为“丑”,而对于这种“丑”的赞美,实为国人的“病态的审美理论”;三是联系父亲在官纳妾、气死母亲、害苦儿子这一写作历史背景,来说明朱父的“不忠不孝不慈”,对于写这样一个男人的文章,不应成为不朽名文,从而引出朱自清表达的父爱只不过是一种意识中的“错爱”的观点;四是朱自清的文章境界不高,“不过是一个身心皆不健康的小知识分子的无病呻吟”,指出《背影》成为不朽名篇,有时代局限性,并认为其能进入新式语文教材中,不过是叶圣陶等老一辈语文教育家的推许。
同样持反对意见的还有张学君。他认为此次的《背影》争议是一个“教育事件”,而不是一个“文学事件”,并从文学的角度对《背影》这一文本进行审视。他在《走进〈背影〉解读的秋日时代》一文中,指出《背影》的真正价值,并非历来人们所认同的“父子情深”,而是两代人“情感的隔膜”,记录了父子间的一次艰难对话:父亲做法的家长制,使得儿子不满情绪日涨,由此父子关系走向僵化。多年后,父亲想念儿子,却又无奈于儿子的倔强,只得“修书以病患且忧大去之期不远”来换得儿子的回头;儿子不满虽在,但终向骨肉之情和伦理压力低头,通过《背影》一文来表示忏悔。他指出《背影》不过是一篇平常的文章,其白话水平在如今这个以白话为主体的时代,比之更胜者满目皆是,这种情况下,它的文学意义已经不大;而读者读《背影》后而来的感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文中父亲的“背影”,而是来自于读者自身的生活与记忆。他认为《背影》的地位不是绝对不可动摇的,不是删去了《背影》,国人就真的泯灭了父子之伦,也不是少了《背影》,国人的阅读就形成了审美缺憾——大可不必唯《背影》是崇。
争论自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背影》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争议一直存在。《背影》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选入高小教材,20世纪50年代因政治原因才从教材中删除的。1951年7月,黄庆生就在《人民教育》中发表过《一篇很不好教的课文——〈背影〉》一文,提出了“究竟是教材有问题呢,还是我的教学能力太差或认识上有毛病”黄庆生,一篇很不好教的课文——《背影》[J],人民教育,1951(7),的质疑,引发了一场全国性大讨论。当时,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背影》“宣扬父子间的私爱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伤感主义的情绪”人民教育编者,对《背影》的意见[J],人民教育,1951(6)。这一场大讨论,对于朱自清先生来说是一场文化浩劫。《背影》被全盘否定,被当做“毒草”彻底从语文教科书中铲除。由此,《背影》历经了30年左右的“冰封”时期,直到1982年重回语文课本后地位才蒸蒸日上。2003年,《武汉晨报》湖北学生反对《背影》作语文教材[N],武汉晨报,2003.09.13.刊登了《背影》落选新教材的消息,原因是大多数中学生很不喜欢《背影》中父亲的形象,认为“不够潇洒”且其穿越月台的行径“违反了交通规则”。这一删除行为遭到90%的家长的反对,教科书编者又出来辟谣,表示已决定将《背影》列入下一册语文课本,风波这才得以平息。而随着2010年孙绍振教授的旧话重提,丁启阵等人旗帜鲜明地反击,新一轮的笔墨大战再度打响。
显然,1951年的大多学者和丁启阵先生都从他们所处的当下时代背景来对《背影》进行了批评。前者是从“国家观”、“集体观”出发,以政治为依据,而提出其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质的批评观点;后者则以社会道德与法律为标准,提出朱父违法及三妻四妾的不忠的观点。无可否认这两者批评观点的指出都与其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思想的自由,学术上的百花争放,自然有利于学术的发展。从一个创新的角度来解读《背影》本无可厚非,但也不能脱离了文本的历史语境。我们知道,“《背影》写的是1917年的往事,对于这一时代背景根本就不存在‘法律’这一说,又何来‘违反了交通规则’?把文质兼美的文章当做‘政治读物’来挑剔,把现代‘经典’用当下的‘交通规则’来衡量,把我们民族的精华用‘时髦的洋理论’来践踏,所有这些,都是对名家名著的亵渎。”商金林,渐行渐远的背影——对《背影》的解读与感想[J],理论学刊,2011(1):115.“《背影》一篇,论行数不满50行,论字数不过千五百言,它之所以能够历久传颂而有感人至深的力量者,当然不是凭借了什么宏伟加结构和华赡的文字,而只是凭了它的老实,凭了其中所表达的真情。”李广田,哀念朱自清先生[J],文学杂志,1948(5),确实,历来对于《背影》不朽原因的解读大多都关乎“情”。孙绍振认为,“《背影》里的父子之爱是错位的,爱与被爱是有隔膜的”,《背影》中写道:“我赶紧拭干了眼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因父亲而感动得流下眼泪,却怕被自己的父亲看见。对于父亲事必躬亲的行为,儿子是抵制的,直到看到父亲给他买橘子时所无意识呈现出笨拙的背影,才使得儿子产生感动,懂得了父亲的爱,从而升腾出儿子对父亲的爱。由此可看出儿子对父亲之爱和父亲对儿子之爱的错位,二者之爱是不同步的,通过“背影”,不平衡的父子之情才走向平衡。这种爱的隔膜,爱的错位,使得《背影》不朽。孙绍振还指出,《背影》的意象不只是“父亲”,还有一个“我”的意象。文中除了“父爱”主旨外,还具有儿子的歉疚忏悔之意。通过“父亲”与“我”两个意象在动作、语言甚至服饰上(父亲的“黑布大马褂,深青色棉袍”与我的“皮大衣”)的对比,折射出儿子对父亲的歉意及忏悔,真挚而浓郁。
笔者认同孙绍振老师的观点。假设读者不看作者,不了解朱父的为人、为父、为夫、为子的品格,只看文字,这篇文章是否有感人处?最感人的地方是什么?答案是肯定的,难忘的当然是“背影”。一般写人物,多从人物的面部、肖像、语言等这些正面角度着笔,而《背影》却能通过“背影”这一角度来对“父亲”这一角色进行描写,可谓另辟蹊径,彰显出独特,这正是朱自清的巧妙之处。多少年来,就是这一蹒跚笨拙的“背影”,深深地感动了一代代人。因为从“背影”我们看到——父爱。从文章中看到父子隔阂,因背影感动而有了父子情。打动人的不是“背影”这一影像,而是从细节中传递给读者的,每个家庭最朴实、最常见、最需要的亲情。不是每段父子情都有这样的背影,但每个家庭都有诸多类似这样的细节,有孩子对父母,有父母对孩子的,所以能引发情感的共鸣——每个家庭都具有、都需要的亲情。为此,作者有意节选了平常生活中的点滴小事,把千般情感凝聚在几个焦点上。例如:父亲开始说不送,最后又亲自去送,在火车上对茶房的反复的叮咛,尤其是父亲爬上月台时“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些场景将父亲对儿子的关怀和体贴,和在艰难生活中的困顿和挣扎,都凝结在了一起;父子之间离别时那份难以割舍的情感也凝聚在这些点上,成为这篇散文的闪光点之一。这样的生活细节在普通人家都很常见,读者如同亲历一般,感情质朴而真挚,岂不动人?此其一。其二,关于有隔阂的亲情。或许正面的形象让朱自清对父亲产生隔阂,正是这背影,让他感受到父亲内心里的爱,这份爱子之心或许与很多其他成分无关。让离家在外的游子产生情感共鸣,尤其是那些涉世不深、感情单纯、与父母有隔阂的孩子的情感共鸣,也同样让历经人生风雨、与孩子有隔阂的父母产生共鸣。朱自清在这篇文章中所用的语言不像他其他的文章如:《春》、《梅雨潭的绿》和《荷塘月色》那样采用华采的语言、排比的句式,不作大幅的渲染,用最朴实的语言表达最真实的情感。
当今网络时代,以一件小事、一首歌、一篇文章打动人比比皆是,我们往往不知作者,不了解背景,之所以打动人就是因为一个“情”。人之常情、家庭亲情是不分时代、永远不过时的,如李白短短的《静夜思》。鲁迅是伟大的作家,我喜欢读他的作品,但他的那些“战斗檄文”未必都能引发所有人的情感共鸣,未必都是人所共通的,有些作品适合中学生读,有些则未必,虽经典但或许是成年后的读物,应该从中学教材删除,然而,朱自清的《背影》在中学读是再恰当不过了。
丁启阵说:“我们培养的中学毕业生,文学阅读、理解和表达能力普遍不理想,思想感情缺乏深度,语言文字苍白无力。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猜测,大家可能会想到如下一些方法:增加中学语文课程的课时,请知名作家和有关专家编写课外读物,给中学语文教师提供更多深造机会,改变高考命题方法,改革高校招生录取政策,等等。这些方法,自然会各有效果。但是,我认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弊端:隔靴搔痒。因为,它们都没有把工夫做在直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动手(包括研究和写作)能力上。”丁启阵,我国中学语文教育需要提高标准(博文),新浪博客http://blog。qq。com/qzone/120308730/1272992000.htm2010-05-05.这点笔者完全赞同,但不能怪学生,应该怪语文教学,怪应试教育,同时还应当特别强调一点,那就是缺乏情感教育。这次《背影》引发的风波,以及一直以来对经典名著的“删”与“不删”的争议就很好地证明了问题的症结所在。针对中学这个年龄段的学生,语文教学究竟要教什么、学什么?特别在当今这个时代,面对独生子女这一群体,他们或许增强了法律意识却淡薄了亲情,或许提高了外在的审美水平却忽略了人间最美的真情,这是教学、教育的引导问题。一篇文章,不可能包罗万象。最美在哪?最好在哪?应该从文学鉴赏的角度加以引导,而不应该负载太多意识形态的东西。
正如教育科学出版社总编辑杨九诠所言:“审美有各种层次,不会因为父亲背影不美,讨过小老婆,违反了交通规则,所以对儿子的感情就是虚假的。”教育专家熊丙奇在《错乱的时空穿越,错乱的教育和学术》中指出:社会风气相对浮躁,引导孩子认识经典关键在于教师要有正确的教育理念,教材不可能涵盖所有内容,只可能是引导学生的基本东西,教师需要选择辅助教学资料。作为一篇以情动人的美文,通过《背影》的教学,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引导学生对“爱”的理解:
1.细心体会无处不在的亲情
《背影》所写的不过是几件平常细微之事:抽空到车站送儿子,对车夫细细叮嘱,为儿子买橘子——但就是这些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平凡之举,却包含着一位父亲对儿子的无限体贴与关怀。是的,父爱无处不在,而我们应懂得感恩。在《背影》教学过程中,可启发学生留心观察生活,爱就在我们身边,亲人之爱、朋友之爱随处可发觉。
2.学会感恩父母
《背影》作为亲情题材的典范作品,感动了无数人。在教学之中,可就父母关怀之情来引导学生回顾父母亲对自己的疼爱方式、畅谈父母的关怀,而引向感恩的主题。父母的无声辛劳付出,我们要懂得,更应学会感恩。感恩父母,我们可以给父母捶捶背、洗洗脚等,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感恩的方式,无处不在。
3.拓宽感恩对象
理解及回报父母是我们理所当然应做的事。但在对学生的感恩教育中,不能仅限于此,在《背影》父子之爱的背后,应引导学生进一步的思考,让他们更深广地去感悟感恩的对象。若学生懂得了感恩父母,感恩朋友,感恩社会,感恩一切美好的事物……那么他们也将懂得以更广阔的心胸来对待生活的挫折,做更好的未来顶梁柱。
总之,《背影》是中国现代散文中亲情题材与主题的奠基之作,对中国现当代散文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背影》是五四新文学第一篇写父亲题材的散文,在其之后所写的亲情伦理的文章如阿城的《父亲》、汪曾祺的《多年父子城兄弟》等很多写父亲题材的作品都多多少少会受到《背影》的启示,更有甚者如三毛的《背影》、赵丽宏的《背影》等则直接借鉴朱自清的“背影”这意象来书写真情人伦。可见,朱自清的《背影》对于亲情题材散文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背影》在不断延伸的文学史上产生了另外一种文化价值,即演绎成为当代审美文化特殊精神家园的符号。在当今社会市场经济发展如此迅猛和科技信息全球化的时代,物质利益已遮蔽了大多数人的生活,人们在精神上难以寻找到一个真正的归宿,而《背影》这一人间亲情的标志,对于当今时代来说,已经超出了其纯文学的价值,成为人们审美渴求的“家”的精神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