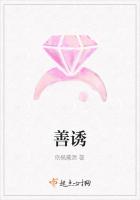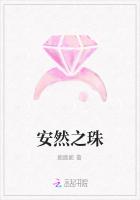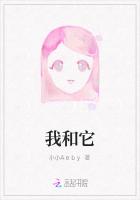吴组缃的作品是以质而不是量而著称。以少量的文学精品获得国内外文学界的普遍赞许,在为数众多的现代作家中是不多见的。吴组缃的小说创作,按其本人说法,始于1930年发表的《离家的前夜》。其实之前,在中学时代,吴组缃就有过许多试笔,只是吴组缃谦虚地以为:“像看自己流鼻涕;穿开裆裤的照片”,不能示人,勉强收在《宿草集》的附录里,如《鸢飞鱼跃》。其处女作《不幸的小草》,发表于1923年,才15岁,我以为更像一篇寓言散文。吴组缃作品不多,完成于1945年的唯一一部长篇《山洪》,成了他的封笔之作,此后他再没有写过小说。他在《吴组缃小说散文集》前记里,将其作品分为三辑:第一辑6篇小说——《离家的前夜》、《栀子花》、《卐字金银花》、《官官的补品》、《菉竹山房》、《金小姐与雪姑娘》,“思想和艺术都不很成熟;不止见解,就是表现手法,也显然在多方面摸索,多方面试练……但现在回头看起来这6篇倒写出当时自己对现实的看法和艺术思想的成长过程或发生的道路。”第二辑6篇小说——《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樊家铺》、《女人》、《某日》、《铁闷子》,“视野似乎开阔了,所处理的主题更有严肃意义了,态度也稳定明确起来了。若是我的作品也在社会上发生过一些影响,应当以这一辑为多。”第三辑6篇为散文。
以上作品可见,吴组缃的小说,除《铁闷子》作于1942年外,其余均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1932~1934年间,是怎样的动力,使得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作家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在创作上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呢?吴组缃说得很明白:“对当时剧烈变动的现实有许多感受。尤其关于我的切身境遇。我能够熟悉的人和事,那巨大深刻的变化,更使我内心震动。我努力想了解这些变化的实质,认识它的趋向,慢慢从自己的小天地探出头来,要看整个的时代和社会。”吴组缃,苑外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168.因此,关注时代与社会就成了吴组缃创作的出发点和创作源。
钱理群编选吴组缃的小说选本时,将其定名为“时代小说”,根据是吴组缃对茅盾《子夜》的一个评价:茅盾的最大特点是懂得时代与社会,能抓住巨大的题目来反映当时的时代与社会。钱理群认为,这是吴组缃夫子自道,是吴组缃与同时代作家共同创造了一种新的小说范式——“社会剖析小说”。“时代小说”的特点是从对个人价值、人生意义的思考转向对社会性质、出路、发展趋向的探索,从偏重主观抒情到客观写实,理性因素的注入,典型环境、典型性格的注重,等等。吴组缃的小说鲜明地显示了这些特征,尤其是其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在吴组缃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对鲁迅小说精神的血脉的继承,而:“丰富的生活积累,深厚的文学素养和清醒的理性判断的结合,使吴组缃的创作在继承鲁迅开拓的‘五四’新文化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作出了与新的历史条件和作家创作个性相联系的生发”,唐沅,吴组缃作品欣赏[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11.正如作者曾经说过的那样:“文学这东西对时代、对社会负有严正重大的使命,它该站在当代思潮的前面真实地反映着那个时代‘内在’和‘外在’,指导或闪示着我们该怎么做、怎么走,怎样生活。”吴组缃,苑外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13.在这里,作者非常明确地道出了文学对社会生活的重大作用及历史使命。由此出发,作者在描绘生活现象时,往往能有意识地把这些现象放在当时社会的背景下,努力去表现出这些现象所包含的深刻社会内容,因而使作品成为反映时代、切中时弊之作,表现了严肃深刻的主题,这在吴组缃小说中的反封建主题、女性主题、破产主题和抗战主题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一、反封建主题
反封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鲁迅曾旗帜鲜明地对整个封建社会和封建礼教进行抨击,深刻揭示出封建道德的“吃人”本质,表达自己对中国国民性的思考和对个性解放思想的提倡。吴组缃承继了这一主题,并在更加广阔的背景和更加深入的时代条件下,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化。当时,思想界有一些人宣扬中国已经过渡到金融资本主义统治的时代,1929年,陈独秀在《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中也说“现在农村中主要矛盾已经不是反封建斗争了”。对此,吴组缃首先通过《官官的补品》、《一千八百担》等作品对封建营垒进行无情地揭露。作家自幼生活在败落的封建宗法社会环境里,耳闻目睹了宗族亲友之间腐旧堕落的生活和下层贫苦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苦难生活,因此当他挥戈指向自己所熟悉的封建营垒的时候,他的揭露就更加锐敏而准确,他的描写也更加从容而深切。《官官的补品》通过写农民为了养家糊口,靠出卖乳汁和鲜血来补养地主家的阔少,揭示了当时农村尖锐的阶级矛盾,表现了鲜明的反封建主题,显示了作家直面现实人生的清醒而严峻的态度;《一千八百担》描写了宋氏大家族各房代表之间为瓜分义庄积谷展开的一场丑态百出的争斗,在新的深度和广度上揭露封建营垒内部的矛盾丛生、分崩离析、必然走向溃灭的趋势,揭示了反封建的意义。
二、女性主题
与鲁迅一样,吴组缃的反封建主题同样关注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的悲惨境遇,以及中国女性挣脱封建礼法的制约后的出路。因此,女性主题也就成为吴组缃创作的另一关注焦点。以往的反封建作品重在揭露封建道德对女性的戕害,吴组缃却让我们看到封建迫害下未泯灭的人性,由于人性未泯,她们所激发的对情感的渴求、对自由的向往,她们在痛苦中的挣扎与反叛和对获得生命自主的渴望与迷茫,也就更加令人心灵震撼。
吴组缃的女性系列小说,反映了女性在封建礼教制度下从惨死到挣扎,再到反叛的过程:《卐字金银花》写“我”少年时偶遇迷路的小姑娘——美丽、聪明、活泼、善良,充满童真;成年后,再次偶遇,姑娘却成了寡妇,又做了“为社会所不容的事”,有了身孕,只好逃到外婆家求救于舅舅,可舅舅是名教中人,不肯相助,导致她悲惨地死去。一个追求自由、解放的女性被“吃人”的封建礼教所吞噬;另一部《菉竹山房》写的是封建道德将“二姑姑”(与亡灵结婚)幸福的爱情和美好的青春都埋葬在古墓似的“菉竹山房”,由于她那未泯的人性,她只能靠营造一个虚幻的爱情世界度日:这里有一家之主——戴着“公子帽,宝蓝衫,常在这园里走”、“每年都会回来”的“二姑爹”,有二姑姑和兰花,还有“福公公”、“虎公公”、“青姑娘”(其实是蝙蝠、壁虎和燕子)。封建文化摧毁了她美好的爱情与人生,但未泯的人性,使她只能在这个扭曲的爱情世界里释放着自己对爱情的向往与渴求。一对新婚夫妇的到来,更加激发了她对人间情爱的复苏,忍不住偷窥一对新人的夜生活。在这里,“二姑姑”虽然没有像《卐字金银花》里的小姑娘和《金小姐与雪姑娘》里的雪姑娘那样被迫害致死,但却在寂寞凄凉的“古墓”里苦苦挣扎,她自然不会像祥林嫂那样去捐门槛,可又不知如何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那么知识能改变旧社会妇女的命运吗?吴组缃把目光落在知识女性身上,《离家的前夜》、《金小姐与雪姑娘》里的知识女性摆脱了愚昧与无知,也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她们懂得并渴望追求自己的幸福与自由。可现实呢?《离家的前夜》中的“蝶”——一个结婚生子后想要走出家庭继续求学的知识女性,却受到具有强烈的封建礼教伦理意识的婆婆的阻挠,同时,还有来自“蝶”内心深处的母爱的牵绊,表现了知识女性寻求个性解放过程中的艰辛与苦涩和其人生道路选择中的困惑。而金小姐则是出生于一个“新旧参半的家庭”的知识女性,她“从前看过些新杂志、新书报”,因此,理想着有一个自主自由的爱情,可一直拖到二十五六岁才“知道从前所怀的那理想,不是目前这个社会一个女人应该有的理想,花一般的憧憬已和那时的青春一起埋葬”。家里限定的嫁期也使她的独身主义不可能实现,只好被人介绍给了“我”,可“我”偏又是一个“给另一个女子牵拉着的心没法摆脱的人”,最后她只好回家嫁人了。事实证明,知识女性仍然摆脱不了封建礼教的束缚。鲁迅曾分析过“娜拉”出走后,这种缺少物质基础的个人反抗最终是免不了像《伤逝》中的子君式的结局的,而吴组缃进一步揭示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算有了经济上的独立,由于封建社会的余毒、封建礼教的羁绊,女性的出路仍然只能是“堕落”如“雪姑娘”或“回来”如“蝶”、如“金小姐”。可以见出,面对时代的变迁,女性的出路问题仍然是有着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所要思考的问题,反封建的任务任重而道远。吴组缃在《女人》中,通过一个目不识丁的二十几岁的“女人”给了大家希望,也为女性出路指明了方向。这个“女人”为反抗公公、婆婆和丈夫的打骂与非人的虐待而出走,她不是知识女性,但她给了得不到丈夫的爱的知识女性“太太”以震撼和勇气,让她们重新思考自己的出路。《女人》告诉人们,无论是知识女性还是普通妇女,女性出路的第一步还是要觉醒,要有勇气走出去,要摧毁旧制度,打破封建观念。可见,在新的时代,吴组缃对女性的出路问题有更深刻的思考和见解,强调了女性自身的弱点和女性意识的自省。
有的作家喜欢以女性形象结构小说,认为女性更令人关注,也因为女性身上凝聚着更多的小说因素,她们既是伟大的——母爱,又是渺小的——没有地位、没有身份、没有人格。吴组缃笔下有近一半的小说是以女性为中心的。《离家的前夜》中的蝶,《两只小麻雀》中的奶妈,《小花的生日》中的美容,《卐字金银花》中的寡妇,《菉竹山房》中的二姑姑,《樊家铺》中的线子,《金小姐与雪姑娘》中的两位姑娘,《女人》中的女人。她们中有知识分子,有劳动妇女,有家庭主妇;有城里的,有乡村的;有年长的,有年轻的;有封建时代婚姻制度的牺牲品,也有获得解放却仍走不出封建樊篱的知识女性;有无私奉献母爱乃至失去生命的奶妈,也有为救丈夫而刺死钻进钱眼的母亲的女儿……总之,她们不论处于什么时代,什么处境,什么身份,都难以逃出苦苦挣扎于不幸边缘,甚至走向死亡的悲剧命运。吴组缃通过这些女性形象,说明了虽经“五四”运动的摧陷廓清,然而封建的传统势力犹如一潭不枯的死水,紧紧地、牢固地桎梏着一代人的心灵。她们的悲剧,一方面离不开社会历史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女性自身的人性弱点。女性个性解放需要彻底摧毁旧制度,同时,更要唤醒女性的自省意识。
吴组缃在小说中关注女性命运,自然与其生活经历、社会责任、创作经历有关。吴组缃是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人性主题是他关注的焦点,而女性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更何况吴组缃一生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他的创作时期主要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旧社会,苦难的社会,他看到了太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性的悲惨命运。童年时期,他就真切目睹了坏了规矩的乡村女子被活活地沉到生石灰坑烧死的惨状,这给吴组缃幼小的心灵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他自己唯一的亲姐姐16岁开始守寡,据说《菉竹山房》中的二姑姑就是以他姐姐的原形创作的,再加上他所接受的中外文化的影响,他希望能借助作品关注女性问题,实则也是社会问题。他曾写过一篇评论《读〈歌谣与妇女〉》,说的是“妇女歌谣”,从中可以看出他写女性系列小说的出发点。摘录如下:
殊不知妇女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一样,乃至于整个的社会制度与经济背景,绝不是如编者所说的那么简单。秦汉以还,妇女所受压迫日甚,其时纵采风问俗之事未废,朝廷得洞悉民间妇女疾苦,果能予以解放援救否?妇女纵不安于命,起而反抗,而谋生无路,奔投无门,果如何反抗?民间大般男子与其妻女同为未受教育者,其知识是平等的,何以地位悬殊如此?昔之妇女亦有与男子受同等教育者,何以依然处于附庸与被压迫的地位?凡此种种,都不值得哓哓辩说。吴组缃,苑外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15.
三、农村破产主题
在20世纪的乡土中国,30年代恐怕是一个最没有亮色的时代,这段岁月积聚着太多的天灾人祸,太多的不幸与苦难。一切似乎都在表明,中国乡村的没落与衰颓,气数已定,无可挽回了。吴组缃就在这一非常时期登上文坛,他曾说他的小说“取材方面,大多写内地农村,其中又以反映农村破产时期动态的居多……”吴组缃,苑外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168.又说“我的这些作品都是我们民族社会在三座大山的重压下的时代写的,内容是写我们人民的苦难、挣扎与斗争。”吴组缃,宿草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2.这里的“破产时期”指的就是20世纪30年代前期。从1931年到1935年,国内连年的旱涝灾害,那时正值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资本主义将经济危机转嫁到中国,使得本就危机四伏的中国农村濒临彻底破产,城乡经济的衰败破产成为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社会现象。吴组缃的家乡皖南也难逃厄运,乡村破产、店铺倒闭,吴组缃也经历了一个“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过程。对经济破产的现实有切身的感受,因此“破产主题”就成了他这一时期小说的主要内容。他运用经济学知识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性质进行分析,写出破产时期乡村的经济破产状态以及由此引发的人生变动,在表现广大农村生活及农民命运的主题上产生深远的影响。
茅盾的《子夜》和“农村三部曲”对吴组缃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吴组缃的“破产小说”与茅盾的不同,茅盾强调主题的政治指向,他从政治、经济的视角反映农村破产的现实,写得气势宏阔,农民觉醒、斗争倾向鲜明,突出的是政治主题,吴组缃曾批评茅盾是“主题先行”。而吴组缃透过经济视角,看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城乡经济的普遍破产影像,通过这些影像,更深层地看到由于经济破产而带来的人生变动、人性变异。因此,就有了《官官的补品》、《樊家铺》、《黄昏》中因乡村经济破产而陷入生存困境的底层农民;农民的破产又势必动摇地主经济,所以《一千八百担》中的地主阶级的子孙们为争夺宗祠存谷而各怀鬼胎的争吵;乡村经济的破产必然造成乡镇商业经济的崩溃,于是又有了《天下太平》、《小花的生日》、《栀子花》中店铺倒闭、店员失业的情形。这些贫困的农民、尔虞我诈的地主子孙、没有活路的失业店员,构成了一幅幅乡村破产的悲剧图像。在这里,阶级之间的对立并不是他的写作重心,他要展示的是乡村各阶级在破产时期所面临的共同的经济困境。为了活路,他们离开土地与家园,或进城找活法或上山当土匪,或变卖家当吃闲饭,或挖空心思争族产。然而,离乡背井的结果却仍然逃脱不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小秃子、线子娘、王小福、祥发妻等“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在苦难和死亡之中挣扎的人们不可避免地导致人性的变异。吴组缃带领我们在《黄昏》听到本是友好乡邻之间的偷盗之事和充满仇恨和“刀板咒”;看到了衰败的《樊家铺》随着经济的匮乏导致亲情伦理关系的丧失,而出现的女儿弑母的人间惨剧;也看到了地主阶级揭去宗法社会温情脉脉的假面具,为了《一千八百担》而上演的钩心斗角的丑剧;更目睹了在《天下太平》的富足年代,丰坦村以“忠厚做人,耐劳苦,安本分”为天性的纯朴人民,在经济破产、求活无门的境况下,由偷盗穷苦邻居到偷窃人们敬畏的神庙上的宝瓶。这一切,真实地向我们证实了在经济破产的背景下,纯朴善良的天性是如何被扭曲、被毁灭,而产生人性的异化的,在这样病态的社会里,挣扎着无数病态的人们,这样的天下又怎能太平?
吴组缃不同于有些作家,仅仅局限于把一个“坟墓”似的农村带到我们面前叫我们认识,也有别于“左翼”作家带着明确的政治指向,让人物由经济上的需要变成政治上的渴求,他除了将农村破产的复杂真相透露出来,更重要的在于探究在这样的社会时代背景下所导致的人情、亲情、伦理、道德、社会秩序等的变动,将笔触探到苦难人民的心灵深处,让我们看到了由生存悲剧而演发到精神悲剧的过程,正如鲁迅所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吴组缃小说的悲剧美给了读者深深的心灵震撼,他承继了鲁迅对人性的关注。鲁迅更多地揭露民智未开时代人性的愚昧、麻木与奴性,吴组缃则是揭示在经济衰败的新时代背景下人性的变异、泯灭,从而探讨经济关系对其他社会关系的制约这一命题。这不能不说吴组缃看问题的眼光要比同时期其他许多作家深邃、高远得多,这也是他的作品之所以隽永、耐人寻味的原因。
四、抗战主题
之所以强调抗战的主题,是因为在吴组缃不多的作品中就有三篇写抗战的内容,而且都有其特殊意义:1.20世纪30年代后期不多的篇什中唯一一篇写抗战题材的散文《差船》(1938年);2.进入20世纪40年代,吴组缃仅有的一个短篇小说《铁闷子》(1942年)和一个长篇小说《鸭嘴涝》(1942年)写的都是抗战主题,《鸭嘴涝》是吴组缃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封门之作,此后他不再写小说;3.敢于在作品中(《铁闷子》、《差船》)揭露抗战阴暗面的作家。
吴组缃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爱国主义者,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前期,受鲁迅的影响,作家关注的是人性的主题,是社会的发展,那么,在日益高涨的抗战洪流面前,在关乎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吴组缃自然毫不犹豫地将手中的笔当做战斗的武器,投身于火热的抗战之中。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他与老舍共同起草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组织、领导协会工作,参与《战地》、《抗战文艺》等报刊工作,在强调“抗战中文艺工作的要点是发扬我们民族的抗战精神”时,特别指出这并不是说“对于自己只许歌功颂德,各方面的病根和缺陷、污点和错误,我们是同样的应该加以揭露与指出,但这必须是批评的,含有积极意义的”。吴组缃,苑外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32.吴组缃以一个学者的客观、冷静的态度,对一味颂扬、盲目乐观的“公式化”文风提出批评,指出抗战现实的复杂性。因为钦佩冯玉祥将军的抗日主张,吴组缃接受冯玉祥的聘请,整个8年抗战期间,他都跟随冯玉祥深入战地前线巡查,也熟悉身边的军人,他在《差船》中已经揭露了“隐藏在抗战旗影下的大小丑恶”,那么,在这“光明与黑暗的交错”的大环境下,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又该如何面对?是遮盖事实,蒙上双眼,盲目乐观,还是认识其存在,加以克服扫除?吴组缃通过《铁闷子》对此作了最好的诠释。小说写三位前线报人和勤务兵为了在两天内编辑出版供前线将士阅读的报纸,他们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为的是给前线将士送去精神食粮。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中华民族抗战的热情与昂扬的战斗意志。然而,“逃兵”的出现打破了他们的幻想,他们听到“逃兵”供认的一桩桩罪恶:抢劫、奸淫、杀人。而这种罪恶在整个部队是普遍现象,“每个驻防单位各盘踞一个村子或市镇,向老百姓肆意索诈,要什么,有什么,比封建时代的王侯还要恣纵。”老百姓“就像严严的关在铁闷子车里,漆黑一团,别想透一口气儿”。这些罪恶让他们切齿,特别是他们发现凝聚着他们心血和信念的发往前线的70多捆报纸,竟原封未动地塞在车站候车室的一排长凳下面,这一震动是巨大的,他们看到了“一方面是严肃地工作,一方面仍旧荒淫与无耻”的严峻现实,知道了逃兵所以成为逃兵、成为罪犯的背景和原因。“当了三年兵,哪个不是财迷色狂?士兵们没教育、没纪律,成天看上级胡作非为,心里火着了,胆子变大了,谁是该死的,不吃口荤儿?都是整个村子整个村子的给他们糟蹋了!说起来还不丧德怎么的!”他们发现,这个“逃兵”“敢作敢当,从容坚决,一点不是孬种。若是少许受到一点好教育的话,怎么会变成这样?我们绝对不要难过:你看我们士兵的本质多么好呀!”他身上体现了中国农民的淳朴素质和敢于献身的精神,本质是好的,是他的社会环境让他干了不少坏事。于是,在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教育与引导下觉醒,最后,在敌机空袭装满弹药的铁闷子时,“逃兵”奋不顾身救出整个列车而献出了生命。作者通过《铁闷子》高歌了全民团结抗战、英勇献身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当道者及其治下的军队的腐败。
吴组缃的另一部抗战小说《鸭嘴涝》是他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他认为是个“次品”。“所以是次品,因为对所写的内容不熟悉”,写的是山区(即家乡)人民经共产党游击队(皖南新四军)的发动逐步奋起抗战的故事。在抗战的大背景下,吴组缃还是把笔触落在了熟悉的家乡人民身上。上编以农村生活为主,一气呵成,依然保留作者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仍有可圈可点之处,下编写游击队政工干部进村发动群众,由于没有这方面的生活,概念化痕迹严重,造成上下编脱节,作品的瑕疵主要在下编。造成小说不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以下相关内容见吴组缃的《山洪》后记与《鸭嘴涝》赘言,《苑外集》P163、P170.首先,这是“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约稿,抗战急需,必须完成;其次,作者“缺乏战斗生活的锻炼”,“当时凭的是一点抗战激情和对故乡风物的怀念或回忆”(外加堂侄信中对故乡抗战动态的介绍),“勉强写下去”,在老舍的再三批评与鼓励下,最后“草草了事”;其三,当时对皖南新四军及其所犯的错误认识不够,这是文章的“不治之症”;第四,小说从1940年动笔,中间时断时续,多次搁笔,甚至一年未动,最后利用病假的工夫,一字一句的挤着,才于1942年完稿。对于一个在短短几年时间连续不断写出篇篇精品的一流作家来说,如此写作实为少见,可以想见,吴组缃着实写得很苦。但是,由于这是一部较早出现的写抗战的长篇,在当时及以后,评论界与文学史家都给予极大关注;也是最早从农民角度真实反映,在抗战背景下,农民如何逐步克服自私、保守、畏惧的心理因素,激发出高昂的爱国热情,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全民抗战的洪流中去的;还是最早描写新四军如何在农村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文学作品。因此,《鸭嘴涝》在现代文学有关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吴组缃在总结《聊斋志异》的成功之处时,概括了以下四个方面:1.站在时代前列,关心现实,向人民学习,作人民的代言人;2.对所写主题有真情或激情;3.所写题材有生活实感;4.丰富广阔的知识和文学修养,吸取了前人的好经验而有所创新。吴组缃,说稗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1.
这道出了吴组缃对创作的追求,用来评价吴组缃的创作是再合适不过了。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创作,“写真实”永远是吴组缃一贯的文学创作主张,他强调写真情实感,扭转“纤弱趣味”的文风,希望作家走出象牙塔,反映社会现实。他不拘于文体的疆界,发挥各种文体优势,游刃自如地将它们运用到散文、小说的创作中。他坚持以写人物为中心,其用小说的笔法来写人叙事的散文在现代散文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也是我们研究吴组缃散文的价值所在。在小说创作中,他又恰当地运用散文创作技巧渲染氛围,以及创作出充满神奇力量的“速写体”小说。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善于运用经济学、社会科学知识分析、观察社会,真实反映社会全貌,这使他的笔下少了乡土文学家那份伤感,多了社会分析小说家那种敏锐和深刻,比之同时代反映农村题材的作品影响更加深远。他善于“通过个别去表现整体,通过狭小去透视广大,在洋溢着浓厚生活气息的生动画面里,对由于更加殖民化而陷入严重凋敝破产的20世纪30年代的农村社会作出了深刻的剖析。揭露封建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残虐,同时写出它的腐朽和走向溃灭的趋向,在展示下层群众悲惨境遇中,更注重描写他们在苦厄中的挣扎和对命运的反抗,并对旧制度旧礼教的各种‘罪人’在正义的审判台前作出全新的道德裁判”。唐沅,吴组缃作品欣赏[M],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12.正因此,他始终坚持“写我比较熟悉的”、“写不出不勉强写”吴组缃,苑外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169.的创作原则,从中可见他严肃的创作态度,这也是他解释自己作品不多的原因之一,吴组缃也曾为此心安理得。但他后来发现,写不出“这原都为生活所限制,为认识所限制”,吴组缃,苑外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168~169.这确实是他过早停止小说创作的部分原因。他也曾不止一次说过,旧社会稿费低,不够维持家庭生活,他只能去教书,这使得他缺少足够的时间创作,更主要的是教书要理智地分析问题,影响了作为艺术家的心理状态和创作激情,这也是原因之一。但笔者以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吴组缃对故乡的关注和眷念。童年的乡村生活,身边所发生的所有人和事在他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使他的目光始终离不开家乡。而一旦生活的积累被挖掘殆尽,离开了熟悉的乡村生活,他创作的源泉也就枯竭,而坚持写真实的吴组缃自然是不愿弄虚作假、敷衍塞责的。此外,特色与局限从来都是并存的,当他熟悉的农村题材和擅长的写人技巧在他的作品中得以充分的展示,并形成鲜明的个性风格之后,往往容易走向模式化。那么,不断追求创新的吴组缃自然不愿重复自己,写不出也就不勉强了。
当然,也有论者指出,随着20世纪30年代文学创作不断走向“规范化”,“这些作品所呈现的社会背景离开了作者所熟知的人物环境(如他在《山洪》的出版后记中就承认他不熟悉当时皖南农村的抗日斗争形势),缺少了早期小说那种经得起反复品味的真正‘生活化’之感。这时,吴组缃加入到‘左翼’作家的时代大合唱,流露出鲜明的‘功利’倾向,即‘以昂扬之情歌颂了被压迫人民的崛起与胜利前途,对压迫阶级及其统治势力的走向崩溃灭亡,则投以痛快的嘲笑’。”吴组缃,苑外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168.如此,“作品的主题意识明显了,然而,就在这不知不觉的艺术合唱之中慢慢消失了自己前期小说宝贵的艺术个性。”肖向明,在个性追求中走向规范——试论吴组缃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就与局限[J],惠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26.
总之,才华横溢、精益求精的吴组缃过早地停止了创作,使中国现代文坛留下了遗憾。但由于他那求“真”的内在品格,使他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全貌,因此,吴组缃少而精的作品更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