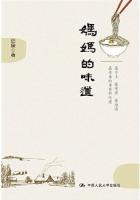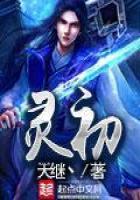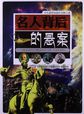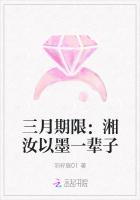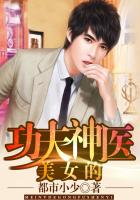相对于吴组缃的小说创作研究,他的散文创作更少人问津。其实吴组缃的散文创作从1925年的《和大家谈谈可能罢》起,一直到1993年(他去世的前一年)写的《我与二十世纪》止,其创作历程要比写小说长远得多,并形成了他自己的散文观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而一直以来评论界对吴组缃60多年的散文创作缺乏一个全面、系统的研究。可见,吴组缃的散文创作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就其散文观及艺术特征略作探讨。
一、散文文体
吴组缃作品在文体分类上常常让评论者、读者难以确定,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名篇《黄昏》,有人将它作为散文鉴赏,有人却当做小说来读,钱理群则将它编入《时代小说》,但认为既可看作小说也可视为散文,同时“本篇的叙事与描写,都集中在一个时间:‘我’归家不久的黄昏;一个地点:‘我’家的庭院;以‘我’为中心,各种人物穿插上场与下场,结构又颇似一个独幕剧”,钱理群,时代小说[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4.作者本人在《吴组缃小说散文集》中将其归入第三辑散文中,而198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吴组缃作品专集中《黄昏》却没有收入《拾荒集》(散文卷),而是列入《宿草集》(小说卷)中。他的《柴》则被日本佐藤春夫编入《世界短篇杰作全集》。《泰山风光》——吴组缃认为应该是篇游记,有时却被划入报告文学等等。当然,不管读者按哪种文体来读,吴组缃都认可。关于散文文体,吴组缃认为:“不论是外国作家还是中国作家,严格地说,对散文和小说是划不清界限的。”吴组缃,苑外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133.吴组缃深受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影响,他认为,中国的《古文观止》是最标准最好的散文,有抒情、有说理、有叙事,而外国文学家,像法国的莫泊桑、俄国的契诃夫、美国的欧亨利写的许多短篇小说都可以看作是散文。吴组缃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作家,前辈们的创作思想与风格一直影响着吴组缃的创作,在他的散文中,我们可以找到朱自清“表现自我”和周作人“人的文学”的散文理论依据,也可以看到他对鲁迅精神血脉的承继。钱理群认为:“在现代文学史上,吴先生是属于以作品的质量取胜的作家,不轻易动笔,而每有一作,必在对于生活、人生、人性的开掘与艺术形式上,都有新的探索,新的创造。在这一点上,其实是接近鲁迅的。”钱理群,时代小说[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2.袁良骏先生说得更具体:“从创作态度、艺术风格上看,二人是很有一些相似之处的。读着《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樊家铺》等吴组缃的代表作,我们是很容易想起鲁迅的《故乡》、《祝福》、《离婚》等优秀篇章的。至少,在对破产农村入微的观察、在对贫苦农民的深厚的同情、在平淡中见热烈的‘白描’手法、在人物刻画的典型化程度、在艺术描写的精雕细刻等诸多方面,我们都不难发现二者的共同点。”袁良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吴组缃小说艺术漫笔[J],北京大学学报,1982(6):57.可见,鲁迅对吴组缃的创作有极大的影响。在“五四”文体革命中,鲁迅就特别强调各文体之间的渗透、融合。在他自编的小说集里,有《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等介于小说与散文之间的作品和戏剧体的《起死》;在诗集《野草》里,也有《过客》这样的戏剧体。显然,这直接影响着吴组缃的文体观。在吴组缃看来,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是反映时代与社会,反映人生与人性,而不必囿于某种文体形式。确实如此,任何一种文体都需要“邻里”之间的学习和借鉴,淡化文体特征往往是寻求一种文学样式新发展的有利途径。吴组缃对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等各种文体都有研究,且能诗亦文还写小说,这样,各种文体在吴组缃笔下互相渗透,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这也就不难理解《黄昏》、《柴》既是吴组缃的散文代表作,又是他的小说名篇。
二、时代主题
基于文体认识,那么,吴组缃另一个重要的散文观就是关注时代主题。他认为:“文学这东西对时代、对社会负有严正重大的使命,它该站在当代思潮的前面真实地反映着那个时代‘内在’和‘外在’,指导或闪示着我们该怎么做、怎么走,怎样生活。”吴组缃,苑外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13.因此,20世纪30年代初期,面对北京清华园盛行的纤弱趣味的文风,吴组缃于1931年写出《谈谈清华的文风》一文,他反对纤弱趣味的小品散文,强调“要把世界观念,民族观念,社会观念摆在脑里,放开眼,看一看时代,看一看我们民族的地位,看一看社会的内状……我们该在现有的生活里抓住苦痛、悲慨,在我们现有的灵魂里,抓住它的矛盾处……”吴组缃,苑外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9.在20世纪的乡土中国,30年代恐怕是一个最没有亮色的时代,吴组缃就在这一非常时期登上文坛,因此,“反封建主题”、“破产主题”和“抗战主题”自然就成了他关注时代与社会的主要话题,他曾说“我的这些作品都是我们民族社会在三座大山的重压下的时代写的,内容是写我们人民的苦难、挣扎与斗争。”吴组缃,宿草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2.面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下急剧破产的现实图景,无论小说还是散文,他所关注的主题是一致的。他名重一方、为人称道的散文名篇都作于20世纪30年代。《黄昏》、《村居记事二则》、《柴》反映的是20世纪30年代农村经济的萧条,农民生活的苦难;《泰山风光》应是一篇游记,“但所分析刻画的还是社会形态,而自然景物倒被我忽略了”,吴组缃,苑外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168.描绘的是泰山特有的以乞致富的“丐官”和以敛财为能事的和尚道士的丑恶行径,把抗战前夕“连空气和阳光都变成灰黑色的”泰安城“风光”真实地展现于读者眼前;《差船》是吴组缃唯一一篇写抗战题材的散文,这是他亲历亲见的一段旅途生活的纪实,他揭露了在全民积极抗战的大好形势下,那些唯利是图,利用一切机会中饱私囊,只图个人利益的卑劣自私的小人(船老大),更令人发指的是那些打着抗战的旗号,却四处招摇撞骗,吃喝嫖赌,为图个人享乐而不顾伤兵死活的军中败类(副官及护士长)。这些令人震惊的罪恶,都是事实,吴组缃将他们公之于众,目的就是要反映抗日大环境下的“全面真实”,让人们认清“抗战的现实是光明与黑暗的交错——一方面有血淋淋的英勇斗争,同时另一方面又有荒淫无耻,自私卑劣。”(茅盾语)这正体现了他的创作初衷:“在日常见闻中,对当时剧烈变动的现实有许多感受。尤其关于我的切身境遇,我所熟悉的人和事,那巨大深刻的变化,更使我内心震动。我努力想了解这些变化的实质,认识它的趋向,慢慢从自己的小天地探出头来,要看整个的时代与社会。”吴组缃,苑外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167.
三、以写人为中心
吴组缃认为要反映时代与社会,就必须以写人为中心,因为“有些散文,或写内心的情绪,或写自己的幻觉,或写想象的东西,写来写去,写的还是人的某一方面。因为整个社会、时代、空间、时间——它的主人翁都是人。归根结底,人是一切的主人翁。文学就是人学,散文和小说本来就是写人的。”吴组缃,苑外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134.由此可见,写人物是吴组缃散文创作的中心点,他认为时代与社会的中心是人,“把人物真实地、具体地、活生生地描写了出来,时代与社会自然也就真实地具体地活生生地表现了出来”。吴组缃,苑外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34.因此,以写人物为中心就成了吴组缃散文的一个重要特征,其写作匠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故事情节的处理。有人物自然就有故事。例如《柴》中一个勤劳、忠厚的劈柴人——鹭鸶哥,从小父母被迫害致死,他只好少小离家,当长工受尽折磨,流落社会又遭抢劫;好容易成了家,又遭诬陷坐牢;出狱后,妻走子亡,孤身一人住在破庙,在半疯半痴中想念着儿子。再如《村居记事二则》,讲述了一个无依无靠的贫苦农妇秦嫂子,在痛失丈夫和小儿子的情况下,一颗痛楚的心,一半护卫着给人当童养媳的女儿,一半牵挂着到千里之外谋生的大儿子,成了一个祥林嫂式的人物;最后,为替女儿看护黄豆,在夜里被小偷活活打死。《黄昏》中,“我”回乡休假,黄昏在自家小院纳凉,却听到了左右邻舍各种不同的声音,从这些声音中,“我”知道了家乡“民不聊生”的生活境遇,每个家庭都有苦不堪言的故事,文章情节脉络清晰,故事催人泪下。但这些都是散文,不是小说。因为小说中的故事必须通过情节结构来完成,而吴组缃散文中的故事则是通过人物的自述和对话来展开情节,而不要求严谨的情节结构,因此,有小说的特点,但本体还是散文。所以吴组缃散文具有较强的故事性,从而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构成了吴组缃散文的特点之一。
二是人物形象的刻画。吴组缃的散文是以写人为中心,自然要通过对人物的肖像、外貌、神态、语言、动作进行生动传神的描写,刻画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塑造人物形象,这是吴组缃散文的又一显著特征,也成为吴组缃散文在开拓创新之路上取得的最为引人注目的艺术成就。打开他的《拾荒集》,几乎每一篇散文都离不开写人,许多散文的人物一出场,作者首先就是抓住人物的肖像、外貌、神态、语言、动作来描写的。如《扬州杂记》中热情、讨好的穷茶役:“那茶役是个中年男子,戴一顶敝旧的草帽,穿着一件卫生汗衫,腰和腿有意弯曲着,把一张黝黄多皱的瘦脸扮成一个非常亲热非常凄凉的苦笑,恨不得凑贴到我的脸上来。”简单几笔,把一个穷茶役为了挣钱生存,不得不陪着苦涩的笑脸伺候人的外貌、神态、语言、动作描写得惟妙惟肖。《村居记事二则》中秦嫂子一出场,就对她的外貌肖像作了细致的描写,她“那时门牙已经落掉四五个。黝黄的瘦脸上挤满了很深的皱褶,数茎黄茅草似的头发,远远就看得见发缝里的皮肉”,“只因她是个‘倒毛眼’,一根棉线终年扣在眉毛下,把上眼皮扣得向外翻转来,瞪出两只干枯红涩的眼睛,样子叫人看了觉得怪难受的。”作者有意将一个备受苦难折磨的、丑陋的母亲形象展现出来,深深烙印在读者的记忆里,也正是这样一位母亲,内心记挂的始终是儿子、女儿,唯独没有自己。吴组缃要歌颂的就是天下所有善良的母亲,她们都有一颗美丽、慈爱的心。《差船》中通过描写船老大和副官及护士长的丑态和言行,刻画出他们的霸道、自私、言而无信,不管伤兵死活,只图自己敛财、享乐的卑劣行径。在《泰山风光》中,作家对贫穷、木然的乡下香客和谙熟生财之道的“丐官”及道貌岸然的敛钱道士三种人物入木三分的形象刻画,更是一直为人们所称道:
狭窄的石板街路上来来往往挤满了一种乡下人。他们的样子打扮都大同小异:干枯的黑瘦的脸,敝旧的深色的棉衣。有仅仅只穿一件黑布棉袍的;有在棉袍上面再套一件庞大的黑布棉马褂的。有戴毡帽的,有戴瓜帽的。帽上,衣折上,都堆着一层灰黑色的尘土。有些没戴帽,露着一头缟色头发;间或还有拖着辫子的。有些老年的,焦黑的口唇盖着一丛蓬松黄胡子。胡子上,头发辫子上,要是仔细看,也是沾着一层灰土。有的拄着龙头木拐,手里拿着一些粗劣的玩具之类;有些肩上背着一只小小的褡裢,里面装着干粮,铜钞;有的拦腰系一根带子,背后歪插一根旱烟袋。他们的眼睛深陷,放着钝滞呆板的黯光。脸是板着的,严肃而又驯善。在街上挨挨挤挤地走着,每一个步子都跨得郑重而且认真。
……
这条古旧的大街,平常给我的印象就是个灰黑色。现在堆上这些灰黑色的人——灰黑色的皮肉,灰黑色的衣着,灰黑色的神情——使我忽然觉得连空气都变成灰黑色的了。
与以上这些乡下香客形成对比的是那些衣冠楚楚的“丐官”及道貌岸然的敛钱道士,文中有两处对道士的对比描写,生动地揭露了他们贪婪的丑恶嘴脸:
一个道士衣冠端正,眼目惺忪的坐在一条板凳上,不住打呵欠。
庙门口那位守着灵官的二当家的道士,已经不是刚才那种温文尔雅的样子。他一手握着敲磬的木槌,衣袖捋到臂膊上,敲一回磬,嚷一回,唾沫四溅,脸红耳赤:“开路第一盘,上山第一关,这是灵官爷爷啦!你们拜灵官爷爷啦!替老奶奶报信的啦!灵官爷爷不报信,老奶奶不知道呵你!开路第一盘呵!你们都有拜呵……”那些香客踉跄的走过来,都驯顺地跪下,磕头,丢钱。有一些不拜的,拜了没丢铜子的,道士就用条凳拦住他,不许过去。如此这般——又要嚷,又要敲磬,又要忙着拦阻不丢钱的香客——工作竟是十分繁重。因此忙得他脸红耳赤,丢了他温文尔雅的身份。
四、写真情实感
反映时代与社会、写人物必然讲究真实性。吴组缃曾经强调:“我们当然要美要善,真不是唯一的,却是最基本的,它是一切文艺生命之所系,离了真,美和善都无所附丽。”吴组缃,苑外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92.他这样解释他对散文真实性的看法:“我想所谓‘真意’有两条:一是真情,这是作者主观方面的。你写的内容真正使你感动了,否则不成其为动人的作品。二是要有实感,这是客观的东西为你主观所感受或认识到的。”吴组缃,苑外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91.因此,“写真情实感”成了吴组缃散文的创作宗旨。他在《西柳集》序中说过:这里收集的几篇东西,有的似乎是小说,有的其实不是,但都多少说了点故事。内容的五颜六色,正展露着现代一个知识青年如我者之真实的灵魂。”吴组缃,苑外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162.他一生的散文最可见他的这一散文观,真实地记录了作者的人生经验和见闻,字里行间蕴蓄着作者几十年的人生经验,充满作者的真情、炽情。他认为真情实感不一定就要为自然的现实情境所束缚,不仅要描写这种纯客观的“实在”,还应该将所见的“实在”通过自己的世界观、社会观,加以艺术的整理,真实地表现出来,好的散文就是要写自己的真知灼见,要写个人的思想感情。关于这一点,笔者另有拙著专论,在此不再展开。
五、语言艺术
吴组缃散文卓越的艺术成就,还得力于作家在语言上的深厚修养。他的语言朴素畅达,表达细腻,体现了现代散文语言的灵活性和丰富性,拓宽了现代散文的语言领域,为现代散文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归结起来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学者的语言
兼有作家和学者身份的吴组缃,散文的语言风格是自然与凝练美的结合,处处显示出富于感情的作家和善于思考的学者二者兼具的行文特色。读他的文章,犹如听一位学问渊博、阅历丰富的长者聊天,在轻松愉快中就能得到深刻的思想启示。他在《雁冰先生印象记》一文中回忆茅盾时说:“他的谈锋很健,是一种抽丝似的,‘娓娓’的谈法,不是那种高谈阔论;声音文静柔和,不是那种慷慨激昂的。”吴组缃,吴组缃先生纪念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345.读吴组缃的文章,得到的印象,与此相仿。这使他的散文更多地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是一种平和、淡泊、学理化的智者散文,一种在平实的生活叙述中,透露出非常透彻、非常澄明的人生智慧和理性精神的散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二)雅俗共赏的语言
在语言的运用上,吴组缃的散文是由“雅俗共赏”的白话写成。他在语言上的追求干净、利落、耐人寻味而又经得起推敲。他曾指出:“语言的美和用是分不开的,最有用、最管用、最好用的,就是最美的。”吴组缃,苑外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81.从这个原则出发,他以人民群众的口语为基础,经过提炼,形成了独特的,既保留了口语精华又不涉及粗俗的散文语言,让人读后获得一种朴素清新的美感。他善用比喻,深奥的道理通过生动明了的比喻表达出来,显得通俗易懂,耐人寻味,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如《柴》中的鹭鸶哥,“脸子干枯瘦削,有点像他用的那把斧子。个子高得有点可怕;尤其是两条腿,又细又挺直,简直像缚了高跷似的。”“他有一只阔大的嘴巴,像一只鼋鱼。那只怪样子的嘴巴,劈柴用力的时候歪斜着撕开来,只在对我作怪样子的笑的时候撕开来,平时总是抿着,现出很苦恼很严肃的样子。”
(三)文、白相融的语言
吴组缃散文中的叙述,在现代书面语言的基础上,化入古汉语中生动而有概括力的词语和句法,将文言词语巧妙地镶嵌在干净利落、纯熟自然的口语中,使读者感觉不到文言成分,在凝练细腻之中蕴含醇厚典雅。
(四)小说化的语言
吴组缃在散文中运用小说笔法塑造人物形象,自然少不了在语言上下工夫。他的散文语言也是“小说化”的,主要采用的表达方式是叙述和描写,语言平实自然。人物语言善于使用对话,通过对话推动情节发展,通过对话塑造人物形象。吴组缃曾说,写人物,对话是个巧法子,他那篇备受推崇的小说《一千八百担》就被称作“对话的艺术”。因此,他非常注重对各阶层人物口语的吸取和熔炼,刻意追求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并能通过人物的对话写出人物的个性。比如《黄昏》中不同人物的对话,就活化出不同人物的身份、地位与性格;《村居记事二则》中,没有文化、思子心切的秦嫂子的唠叨和有文化、能识文算账的失业店员三驼子羞答答的语言,都很贴合他们的身份和性格特征。特别是《柴》中“鹭鸶哥”那一字一顿的口语:
做事呀——哼!——总要小心。——哼!——小心是要紧的。——哼!——都是我不小心。——我,哼!——我和你谈呀,——哼!——做事末冒失。——哼!——我不该——哼!——不该过那桥。——哼!——他打呢,——哼!——给他打一顿。——哼!——桥是不过的。——哼!——桥是不过的。——哼!——不过桥,——哼!——我的儿子不能死。——哼!——我就为儿子。——哼!——儿子死了,——我,哼!——我就没想头了。——哼!我住破庙,——哼!——我不丑。——哼!——那娘的跟人,——哼!——跟人跑,——哼!——我丑煞。——我,哼……
这一句一顿,简洁明了,话语不多,却把“鹭鸶哥”不幸的身世与他对儿子的思念和心中的懊悔,以及对妻子跟人跑了的怨恨都表达出来了,既符合“鹭鸶哥”边劈柴边说话的情状,也符合他平时不爱说话,说得少而简洁的个性。
综观吴组缃的散文创作,写真情实感是其创作的宗旨,真实地反映时代和社会是他的创作理念,他坚持以写人物为中心的创作主张以及圆熟的写作技巧,使他跨越了文体的疆界,不因内容而拘谨于某种表现形式,从而丰富了其散文的审美张力,形成了独特的散文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