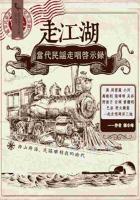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是“缘情”。“缘情”说的提出和发展与玄学是什么关系,是本节要讨论的问题。
“缘情”说的提出在魏晋。但是,问题应当追溯到先秦两汉,应该从“言志”说谈起。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情、志往往纠葛在一起,“言志”说和“缘情”说是截然不同的两派,还是并无对立的相沿相承的一说,弄清这一问题,方能弄清“缘情”说的特点地位,方能恰当地把握在这一文学观念发展过程中玄学所起的影响作用。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六志”孔颖达《正义》:“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不能简单地断言孔颖达此论反映的是唐人的认识。应该说,孔颖达“情志一也”之说在先秦两汉也是有一定根据的。他所《正义》的《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所引子太叔那段话:“子太叔见赵简子,……
简子日:‘敢问何谓礼?’对日:‘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日:民有好、恶、喜、怒、哀、乐六志,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礼记·王制》:“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弗学而能。”《左传》称为“志”的,《礼记》称为“情”。
再一个根据,是《楚辞·九章·悲回风》:“介眇志之所惑,窃赋诗之所明。”而《楚辞·九章·惜诵》则日:“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一日抒情,一日介眇志,情、志也是一致的。又一个根据,是《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在这里志和情也不可截然分开,志中确有情的成分。
志和情都属心理反映和表现,字义本来就有某些重合之处。
人们也可能渐渐认识到文学与情的关系。“言志”说在发展中,偶尔把情的因素包容进去,是并不奇怪的。
但是先秦两汉总的倾向是重“言志”,而且言志和“缘情”有别。这时也认识到文学中抒情的问题,但这时对情的认识也与后来不一样,这时的“言志”和后来的“缘情”所反映的是不同的倾向、不同的文学思想。
最早的诗歌观念,很难说是“言志”还是“缘情”。诗产生的那一天,就有了对诗的看法。为什么作诗?本身就是一种观念。“候人兮猗”(《吕氏春秋·音初》篇),算不算文学,算不算保留下来的最早的诗,又算不算抒情诗?《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所载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是对原始时代狩猎过程的回忆或记忆。朱自清说:志是记忆、记录、怀抱。这个解释应该是对的。既然如此,可不可以说,这首诗也属诗言志?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保存下来的远古歌谣,更多是图腾崇拜,巫术观念。《礼记·郊特性》所载《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是巫术咒语。《吕氏春秋·古乐》篇的“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产生于敬神祭祖的仪式中。这八阙,歌颂本民族从初始之民(载民),经过畜牧业(遂草木、总禽兽之极),到农耕生活(奋五谷)的整个历史,歌颂本民族的始祖神图腾(玄鸟),歌颂本民族建立发展过程中祖先之帝至大无极的功绩(达帝功),天神之功和土地之德(敬天常、依地德),是诗,也是史,本民族的发展史,是歌颂,也是记忆回忆。似也可看做一种诗言志。
《诗经》作者也表现了抒情的观念。三百篇有好几处提到他们作诗处于某种心情,或心伤,心悲,忧心,劳心,《魏风·园有桃》:“心之忧矣,我歌宜谣。”《小雅·四月》:“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则直接说他们因有忧情而作诗。但“言志”也是《诗经》作者的重要观念。直接谈到作诗的十几处,有几处明显是讥刺时政,而《大雅》中《大明》、《绵》、《生民》、《公刘》,《商颂》中《玄鸟》等,在敬神祭祖的仪式,用诗的形式,传诵记录下先祖创业的历史,而当时不少诗可能都是根据记忆(以口相传、以记忆相传),而把内容记录、记载下来,不论远古的历史,还是现实的事件,讥刺时政还是风俗民情。作诗的目的不是抒情、娱乐,而是以有韵、便传唱的形式,记录下某些史实。
至于采诗、献诗,更着眼于志。采诗的目的,一在于观风,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另一个目的,在为宫廷仪式需要。如《汉书·食货志》所说:“孟春之月,群聚将散,行以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天子。”就后一个目的而言,大型祭礼活动,朝会宴飨,宾射、燕射仪式,以及行师出军之日,都要奏诗。采诗是作为仪式乐歌,是服务于国家礼仪,服务于政治目的。诗被礼仪化了。典礼奏诗,诗所含的情也好,史实也好,本身的意义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象征意义。由于什么样的典礼用什么样的诗有严格规定,诗的史实、情都被淡化了,转化为礼的一种象征。它被赋予礼的严格等级的品格,诗言志被纳入礼的范围。至于前一个目的,观风实际就是观志。不过,不论原来表现的是什么,是抒情,还是讥刺,采诗者都把它作为风俗民情看,都是要从中观察政治得失。这两个目的,都已没有情的地位。
后来的赋诗言志、教诗明志以及再后来私家著述用诗,更没有情的位置。朱自清的解释是对的。志的内涵,非关治国,即关修身。春秋赋诗言志的大量例子,说明当时人们注重于诗的是其理性的内容,而非其感情的因素。赋诗言志的“志”,已不是作者之志,而是赋诗者之志。可以不顾诗的本义,可以断章取义。
赋诗者又是在礼仪外交场合,甚至作战之时,即要注意自己的身份,又要注意对方的身份,用诗来表明志意。这志意,不论是一国之志,还是一己之志,都是完全理性的。试想,作战时,部下请示是否渡河,赋诗《邶风-匏有苦叶》,取其中“深则揭,浅则厉”一句下命令,不论水深水浅,都要渡过去(见《左传》襄公十四年)。哪里顾及了诗中的恋情呢?最早提出“诗言志”的《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赵孟观七子赋诗之志,伯有赋《鹑之贲贲》,其中有“君子无良,我以为君”,影射郑伯,有怨恨之心,可以看作带感情色彩,其余六人都赋诗称美郑伯和赵孟,联络两国感情。其实,即使伯有,也主要是影射,是取理性的议论之义。
教诗与赋诗,典礼奏诗,可能是交叉为用。以《诗》为统一教本教诗,始得在典礼场合和外交场合赋诗。《周礼》的多处记载可能都与教诗有关。《周礼·春官·大师》所记载的“教六诗”,可能是教瞽嚎,而非教国子。郑玄注“六诗”: “教瞽嚎也”,《周礼·春官·瞽噱》:“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都是证明。教国子是大司乐。《周礼·春官·大司乐》载大司乐教国子乐德、乐语、乐舞:“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漠、大武。”大师教瞽朦六诗、六德、六乐。大司乐教国子是乐德、乐语、乐舞。乐德和六德留待下面论述,六诗和乐语,是风、赋、比、兴、雅、颂和兴、道、讽、诵、言、语。郑玄注“六诗”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注乐语之“兴”:“兴者,以善物喻善事。”注“六诗”之“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注乐语之“道”:“道,读日导,导者,言古以剀今也”,都是相通的。《汉书·艺文志》:“不歌而诵谓之赋”,则乐语之“诵”或者与“六诗”之“赋”相当。“风”和“讽”通假。因此我怀疑,教国子和教瞽朦都有类似或相关的内容。又《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日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又说:
“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因此,可能不仅教国子,类似的内容也教万民。教诗是当时施行礼教的一项重要内容。教诗教什么?教六诗。六诗是什么,郑玄注是一种解释。近今人从章太炎、朱自清到章必功、张震泽、王昆吾,都有自己的解释。要取得一致意见,似还需时日。但有一点似可想到,即这是诗的六种不同的语言表现形式,所以称“六诗”,一称“乐语”,并且与六德、六乐即义教、乐教相并列。这时值得注意的是教诗的同时教德。《周礼·春官·大师》称为“以六德为本”,《周礼·春官·
大司乐》称为“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教、友”。六德的内容,郑玄注为:知、仁、圣、义、忠、和。核之《周礼·
地官·大司徒》的“六德”,郑玄的注是有根据的。但六德和乐德显然也是相关的。如果说六诗(或日乐语)是言教,六乐(或称乐舞)是乐教,那么,六德(或称乐德)则是德教、义教。从语言形式上是六诗,音乐形式上是六乐,思想内容上则是六德。
诗、德、乐一体。从诗言志的发展角度看,六德就是教诗所明之志。如果这样将它们关联起来尚属可行,则可知道,教诗所明之志,即知、仁、圣、义、忠、和,或中、和、祗、庸、教、友,都是关于伦理道德,完全是政治教化的色彩,情的内容荡然无存。
教诗明志,《周礼》教六诗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孔子教授学生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诗》。他教《诗》,是教礼乐伦理,从政专对。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着眼点在礼和乐。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论语·子路》),着眼点在从政,在出使专对。他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所谓“无以言”,也是在聘问从政场合无以引诗以言对。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他说的是用《诗》,而非作诗, “兴、观、群、怨”的“兴”不当是表现手法之“比兴”,也不当是指通过形象感染、陶冶人的情感,而当是以诗引起修身学礼之事,在从政的礼仪等场合,能赋诗以起意兴志,言志陈志,完成政治外交使命。“观”也不当是审美观照,而当是聘问从政时,他人赋诗、酬答时能观其志,观他人的政治意向,观善恶是非。“怨”是刺上政。“群”则是协和群体,以诗维系贵贱等级的社会群体秩序。这些,都当是他教诗所明之志。这志,主要的是政治伦理、礼治教化的内容,没有多少情感的因素。
私家著述引《诗》,是“诗言志”的发展。朱自清《诗言志辨·诗教》已经指出,私家著述引《诗》,从《论语》开始,以后《墨子》、《孟子》也常引《诗》,而以《荀子》独多。我们先看《孟子》,孟子提出“以意逆志”,这“志”就是“诗言志”的“志”。“以意逆志”,从《万章上》的解释,是要求从诗歌整体的本来的意思推想作者之志、全篇大义。但他所阐发的也是儒家伦理道德原则。从他引《诗》解《诗》实践看,《滕文公上》
引《小雅·伐木》和《鲁颂·闷宫》说明夏变夷而非变于夏的道理,《公孙丑》引《大雅·文王有声》,说明王要以德服人,《梁惠王上》引《大雅·灵台》,说明王者当与民偕乐,注重的都是仁德孝义等伦理观念。我们再看《荀子》,荀子明确提出“《诗》
言是其志也。”《荀子》引《诗》,据罗宗强先生统计为84条,所论都是礼治教化修身奉君等内容,这应该看做他对“《诗》言是其志”中“志”的内涵的理解。他在其他地方讲到情,但对“志”的理解中,可能没有和情关联起来。
这时也提出文学与情的关系。但这时情本身的含义比较复杂。比如《荀子》说:“夫乐者,人情之所必不可免也。”(《乐论》)还说:“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正名》)
又说:“好、恶、喜、怒、哀、乐藏焉,夫是之谓天情。”(《天论》)但是荀子又说:“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性恶》)荀子是把情作为人的本性欲望。
他是性恶论者,以为人天生就有各种欲望,好利恶害,好逸恶劳,是“人性之所同欲”。他说:“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正名》)情和欲是相应的。所以他说:“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他的意思,从人的本性、欲望来说,需要文艺,就像从人的欲望需要吃饭、睡觉一样。从荀子这句话中,得不出诗歌抒情的结论。
比如《礼记·乐记》中有一段话:“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惟乐不可以为伪。”这段话,有的这样解释:“《乐记》看到了主体内在的情感精神状态直接决定着艺术创造的成败。”“所谓“隋深’,就是要有深厚的情感,有深厚的情感才能使作品获得光辉美丽的形式。”“‘气盛’指的是艺术家在创作中要有一种忘怀一切,无所畏惧的精神状态。只有这样,作品才能‘化神’,也就是具有非概念所能规定的奇妙的变化和生动的魅力。”“所谓‘和顺积中’,指的是艺术家要有一种去除了物欲私虑,爱物利人的高尚道德情操”。如李泽厚《中国美学史》。有的这样解释:“作者明白指出,‘乐’是情感的艺术,充沛深厚的真情实感,焕发了艺术的生命,任何虚伪矫饰,为文造情,都与艺术不相容。”孤立地看,这些解释都有道理,但回到《乐记》特定的环境,联系前后文,会发现这段话有其特定的含义。这段话的前面,先指出“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提出要“以道制欲”,然后指出:“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矣。”“反情以和其志”,孔颖达疏:“反己淫欲之情以谐和德义之志也。”“广乐以成其教”,孔颖达疏:“宽广乐之义理以成就其政教之事也。”“乐行而民乡方”,孔颖达疏:“方犹道也”,“君既如此正乐与行,……而民归乡(向)仁义之道也。”这样,“可以观德矣”,可以观其德行。这种仁义政教之德,表现出来,就是乐。所以《乐记》接着说:“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认为“乐”是得礼义之精华。前面那段关于“情”的话,正是针对前面的论述紧接着提出来的。这段话所谓“情深”,实际是前面所说的反淫邪之情、谐和德义之志深,并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感情深厚。这种德义之声表现于外,所以叫“文明”。所谓“气盛”,是指这种德义之志的修养意蕴积于中,并不是指什么“艺术家在创作中要有一种忘怀一切,无所畏惧的精神状态”。所谓“化神”,用孔颖达疏来说,就是《毛诗序》所说的“动天地,感鬼神,经夫妇,成孝敬”,因为德义充实于中,因此有教化之功,并不是艺术奇妙的变化和魅力。所谓“和顺积于中”,所谓“和顺”,是《乐记》
在另一处所说的“君臣上下同听之,莫不和顺”的和顺,是指礼义秩序施于人心感到和谐顺合之气,是对礼的自觉服从,内心的平和,并不是什么爱人利物的高尚情操。所谓“英华发于外”的“英华”,就是“乐者,德之华”之意,是德义礼义的英华发于外,而不是什么作品鲜花一般美丽的生命。总之,做到内心和于礼,德义谐合于心,这就是“不可以为伪”。所谓“不可以为伪”,所谓“著诚去伪”,就是《礼记》所说的“正心诚意”的意思。这段话并不是对艺术表现真情的肯定,相反,是对“情”作了极严格的限定。所谓“情深”,是以礼义修养为基础的“情深”。对礼教秩序“正心诚意”,就是情深,就是气盛。这与文学自觉以后所说的文学表现感情,意思实相距甚远。
这时所谓“情”,很多是群体性的伦理道德的情。《毛诗序》: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直接地看,这句话确是表明志和情不可分,志中含情,或者说情志为一。但接下看:“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所谓“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应该是古代举行祭礼时歌之舞之的情景。如果是这样,联系古代为祭礼而作诗的背景,那么这里所谓歌诗,应当是指祭礼中的歌诗,这里所谓“情”,实际是群体性宗教性的图腾情绪,所谓“情志一也”,志也是宗教性之意志,都与后来的抒情说之情大相异趣。与其说是以情解志,不如说是以志含情,把情统摄在志的光环之下。《毛诗序》之所谓“情”,大体可以这样理解。他是说“吟咏情性”。“吟咏情性”,虽出自个体,但并不带有个体的特点,它所表达的应该是一种群体性的情感思想。“风”是“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系一人之本”是出自个体,但表达的是“一国之事”,是一种群体性的情感思想,而不是个人的情感。“雅”是“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是一种群体性情绪。“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也应理解为一种群体性思想感情。因为是指群体性情感,所以说“发乎情,民之性也”,“民”是群体性的概念,人之群体才称为“民”。“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国史是个体,他负责采诗,但诗并不是他个人所作,只不过“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而已,这“系一人之本”,就应该是系于国史之本,因此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是代一国之群体而“吟咏情性,以风其上”,因此,这所谓“吟咏情性”,应该是吟咏群体性之情性,而非国史个体之情性。所有这些,都与后来抒情说之情大相异趣。
《礼记·乐记》所说的“情”也当作如是解。《乐记》是说: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乐记》反复讲到“凡音之起,由人心也”。“人心”,在《乐记》中,是艺术一切问题的中心环节。音之起,由人心生。
“人心”的各种变化也都会反映于“乐”中。有喜怒哀乐的情绪,音乐就会有与之相应的声音。这就是《乐记》所说的“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哗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这里的“情”也好,“人心”也好,都是作为一种社会群体性的情绪。所谓哀心、怒心感者,讲的实际是社会心理反应。《乐记》说:“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倡和有应,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也。”世乱之奸声或治世之正声感人,故社会的逆气或顺气应之,于是或者淫乐兴,或者和乐兴。这是从人心以类相感的角度,强调淫乐或和乐形成中,社会心理反应的作用。
社会心理反应,是大而言之的“人心”,是整个社会的“人心”。
“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是世之音,形成此音的情绪当然是社会群体性的情绪。“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忧,咩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僻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讲的也是社会心理反应,而不是个体情绪的抒发和反应。正因为是社会群体性的心理反应,所以才“声音之道与政通”。乐才能通伦理,才“知乐则几于礼矣”,政、伦理、礼,都是社会群体性的行为。
更为重要的,是《毛诗序》等说情,是服从礼治要求的。
《礼记·乐记》说,人心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因此“先王慎其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看到音者生人心,所以要用礼来引导,要“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毛诗序》则说吟咏情性的目的,是“以风其上”,是为了讽喻在上的执政者,以正得失,厚人伦。其次,是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义”。抒情咏诗,不能越过礼义规范。
这时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诗的抒情性质,前面提到的《诗经》
作者因忧愤而作诗是例子。《楚辞·九章·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也是例子。但这在当时似并非普遍的认识。这种认识完全被“言志”说淡化了,抑制了。主要的倾向,是重功利、重教化的“言志”说。即使言情,也是社会群体性伦理道德层面的情,可以看做“言志”说的另一种形式的表现。
这是先秦、两汉情志观的大致情况。
用这样多的篇幅追溯先秦、两汉的言志观念,是为了说明到了魏晋提出“缘情”说,从此缘情观念得以发展,是一个多么大的文学观念的变化。
“诗言志”的观念仍然在长时间为人们所接受。但是不与政教功利相联系,注重抒发个人一己之情的“缘情”说起来了,并且自魏晋以后不断发展,形成为与“言志”说相对的文学思潮。
情被看做诗的本质,甚至就是诗的一切。晋陆机《文赋》
说:“诗缘情而绮靡。”关于诗的特质,他提出两点:一是绮靡。
罗宗强先生的意见是对的,结合创作倾向看,结合刘勰“结藻清英,流韵绮靡”的评价,所谓“绮靡”是指情思的绮丽,文字的华美和技巧的细腻。另一点就是缘情。陆机论述了十种文体,每种文体的特征都有两个词概括,而诗是“缘情”和“绮靡”,陆机是把“缘情”作为诗的最基本的特质。诗是古代文学创作最基本的文体,而且,从《文赋》的论述看,“缘情”不仅对诗,也是对其他类作品的共同要求。“诗缘情”的提出,便标志一个新的文学观念的提出。
梁刘勰《文心雕龙·情采》说:“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文心雕龙》中“情”的含义是多方面的。与“采”相对,它可能泛指内容,但这里明确说是“五情”,可见这“情”就指具体的感情。他说“五情发而为辞章”,是以为文章组成以情感抒发为基础,或者说,感情抒发就是文章。
唐皎然《诗式·重意诗例》说:“但见情性,不睹文字。”这是要求情在言外,在直接可感的语言形象之外,蕴含着多重言外之意。所谓“情性”,指可以反复体味的情趣韵味。这种情趣韵味的最根本的基础,是情性。但是他说: “但见情性,不睹文字”,是说诗的全部韵味,全部艺术魅力,在情性,不在文字。
这是对谢灵运诗的评价。皎然和他同时的人非常推崇谢灵运。评价谢诗,是借此提出对诗的本质的看法。他的看法,诗就是情性,情性就是诗的全部。
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说:“诗者,吟咏情性。”《毛诗序》说:“吟咏情性,以讽其上”,又说:“发乎情,止乎礼义”。
严羽取“吟咏情性”之语,不再说“以讽其上”、“止乎礼义”,就是说,他所谓“吟咏情性”没有任何功利性的目的,没有任何限制。吟咏情性就是诗。严羽是这样理解唐诗的,唐诗的全部价值,就是“惟在兴趣”,而兴趣的基础,在吟咏情性。严羽是把吟咏情性作为诗的根本特质。
明袁宏道《序小修诗》说:“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他明白提出了公安派的两个主要观念,自由的表达,无拘无碍,和抒发性灵。而自由表达的基础在抒发性灵。所谓“独抒性灵”,指作诗的灵动才气,指表现个性,更指坦露真实的情感。诗的灵机又基于作者的感情,江盈科为袁宏道《敝箧集》作叙,称引袁宏的韵话说:“要以出自性灵者为真诗尔。”袁宏道又说:“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传也。”有真情就有真诗,无真情则无真诗,这是袁宏道和以他为代表的公安派的看法。
清袁枚《答蕺园论诗书》说:“且夫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他又说:“提笔先须问性情。”(《答曾南村论诗》)袁枚是清代性灵派的代表,清性灵派的很多文学观念是从公安派那里来的。在重性灵、重情性这一点上,似乎比公安派走得更远。袁枚反复地说这一点,他说:“诗歌以咏情也”(《瞻园诗集小序》),又说:“诗写性情,惟吾所适”(《随园诗话》卷一)。他说:“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随园诗话》卷五)
王国维也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人间词话·删稿》)
他是从情景交融的角度讲的。凡写景必蕴含情感,没有单纯的不蕴含情感的写景。而其实,他谈的也是诗的本质问题。他在《文学小言》四中说:“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日景,日情。”景和情这二原质,文以情为基础。他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说:“诗歌者,描写人生者也。今更广之日‘描写自然及人生’,可乎?然人类之兴味,实先人生,而后自然,故纯粹之模山范水,留连光景之作,自建安以前,殆未之见。而诗歌之题目,皆以描写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主。其写景物也,亦必以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始得于特别之境遇中,用特别之眼观之。”以感情为之素地,就是以感情为基础,就是以情为文学的最基本的原质。
提出这么些例子,是要说明,从魏晋直至清末,把情看做诗的本质,是怎样深深地影响着一些文学家的观念,这种观念是怎样历久弥新,千年相承。
文学各方面的问题都和情联系起来考察。我们先看陆机。他谈创作缘起,以为创作缘起于情。陆机在创作具体作品时这样认识。他在《与弟清河云诗序》中说:“凡厥同生,凋落殆半。收迹之日,感物兴哀。……衔痛东徂,遗情西慕,故作是诗,以寄其哀苦焉。”诗作之动机在感物兴哀,有此哀情始有此诗之作。
这是一种创作缘起于情的认识。他在不少地方都谈到这种认识。
《叹逝赋》说:“顾旧要于遗存,得十一于千百,乐隋心其如忘,哀缘情而来宅。”《思归赋》说:“彼离思之在人,恒戚戚而无欢。
悲缘情以自诱,忧触物而生端。”在《文赋》,陆机有更为集中的理论表述。他论创作缘起,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
悲落叶于劲秋,嘉柔条于芳春。”情注于万物之中,物悲则悲,物喜则喜,有这种感物而生之情,则“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他论艺术想像,“其致也,情瞳咙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以为艺术想像的过程也就是情感表达、提炼的过程,因提炼而使需表达的感情愈来愈鲜明。他论文病,以为“言寡情而鲜爱”是重要的文病,能否以情动人,被作为衡量作品优劣的标准。他论灵感,以为没有奔涌的情思,就没有灵感,他说:“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揽茕魂以探赜,顿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逾伏,思轧轧其若抽。”
我们再看刘勰。刘勰是折中论者。他既讲“言志”,也讲“缘情”,《文心雕龙》中的许多问题都从“情”的角度立论。他高度评价楚辞,之所以高度评价,重要的一点,就是楚辞作品情思浓烈。“《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又说楚辞作品“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所谓“气”,是感情气势。他论文体,处处以情为衡量作品优劣的标准。《明诗》篇论诗自不必说,古诗“怊怅切情”,建安诗“慷慨以任气”,历代优秀诗作都是情切气盛。赋是体物的,但“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这是“立赋之大体”(《诠赋》篇)。颂赞的写作原则,是“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颂赞》篇)。祝盟则须“感激以立诚,切至以敷辞”(《祝盟》篇)。诔碑须“观风似面,听辞如泣”。哀吊“必使情往会悲,文来引泣,乃其贵耳”(《哀吊》
篇)。他论神思,说神思方运之时,“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神思》篇)。神思的过程就是感情兴发流动的过程。
他论风格,以为风格就是作家情性的外在表现,所谓“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所谓“吐纳英华,莫非情性”(《体性》篇)。
风骨是他提出的理想文风,所谓“风”,就是感情的激动人心的力量,他说:“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深乎风者,述情必显”(《风骨》篇)。他论通变,以为掌握通变规律,重要的一点是依凭自己的情思,“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通变》篇)。论定势,是“因情立体,即体成势”(《定势》篇)。论情采,以为当“为情而造文”,不可“为文而造情”,说“繁采寡情,味之必厌”(《情采》篇)。论熔裁,提出三准,第一点就是“设情以位体”(《熔裁》篇)。论比兴,以为比兴二者都是抒情的需要,兴是起情,“起情者依微以拟议”,比是畜愤,“比则畜愤以斥言”(《比兴》篇)。夸饰,是为了更强烈的抒情,“谈欢,则字与笑并,论戚,则声共泣偕”(《夸饰》
篇)。论附辞会义,首先要“以情志为神明”(《附会》篇)。论总术,以为写作的基本原理,在于如何与情相会,所谓“按部整伍,以结情会”(《总术》篇)。论物色写景,以为重要的在“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做到“物色尽而情有余”(《物色》篇)。
论鉴赏,以为当“披文以人情”(《知音》篇)。在刘勰看来,情是文章写作的灵魂,而如何表现感情,也是刘勰《文心雕龙》五十篇讨论的核心问题。
再看钟嵘的《诗品》。他论诗的创作缘起,提出“物感”说,感物动情,因而形诸于诗。《诗品序》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感物动情的不仅有自然景物,更有社会生活:“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他说,社会生活感荡心灵,突出的是一个“怨”字,“诗可以群,可以怨”,是孔子诗说的内容,本来的意思是怨刺上政,是用诗之法。钟嵘接过这一说法,改造为创作缘情之说,以为诗之创作,盖缘起于社会生活中的种种悲愤之情、悲怨之情。正是为抒发这种种怨思幽愤之情的需要,有了创作动机,有了创作激情,也就有了诗。他分三品论五言诗,强调的也是怨情的有无,情思是否浓烈。《古诗》为上品,其特点是“意悲而远,惊心动魄”,是以怨情动人,以至于令人惊心动魄。他说汉都尉李陵诗“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李陵因战事失利,身陷匈奴,被迫屈辱受降,身败名裂,抱愧终身。钟嵘以为正是这样的生活经历,形成了他的凄怨诗风。李陵诗的动人之处,正在于他的深切的凄怨之情。他说班姬诗“怨深文绮”,曹植诗“情兼雅怨”,王粲诗“发愀怆之辞”,左思“文典以怨”。上品的多数诗人,都以怨情评之。中品的不少诗人亦然。评秦嘉、徐淑夫妻“文亦凄怨”,评刘琨、卢谌“其源出于王粲,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
我们这里只举魏晋南北朝的几个例子,只举了陆机、刘勰、钟嵘。仅从这廖廖数例即已可看出,情在文论家那里,在他们讨论的文学的各方面的问题里占有何等的地位。从创作缘起到艺术想像和灵感,从文体到风格,从创作到鉴赏,缘情是成为了认识文学的普遍性的观念。
三
魏晋以后,文学“缘情”说愈来愈走向自然。人们讨论文学缘情,强调的是真情自然。
我们说过刘勰是讲自然之道的。自然之道反映在缘情问题上,就是主张自然情性。《文心雕龙·明诗》:“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是这一思想的明白表述。钟嵘在这一点上更为突出。钟嵘《诗品》提出“直寻”和“自然英旨”说。本书下面有关审美情趣一章我们将要谈到,“直寻”和“自然英旨”主要是讲表现方法和审美情趣,它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主张感情的自然。钟嵘是反对用事的,理由就是诗是吟咏情性的。钟嵘说:“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用事是造作,而诗的本质在抒情,因此应当自然。
唐、宋两代,很多作者在创作实践中事实上是任情自然的。
比如盛唐的一些诗人,特别是李白。又比如宋代苏轼。理论上也有人提出这一问题,比如中唐皎然。皎然论诗歌创作是重苦思,他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但苦思并不意味着丧自然之质。他说:“成篇之后,观其风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诗式》卷一“取境”章)他评苏、李诗:“其五言诗周时已见滥觞,及乎成篇,则始于李陵、苏武二子,天予真性,发言自高,未有作用。”天予真性,是主张真情自然。他评谢灵运诗:“曩者尝与诸公论谢康乐为文,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诗式·文章宗旨》)他是既重苦思,又重真情自然。比如北宋初的田锡。田锡是古文家,北宋初年古文家是重道统文统的,而他进一步提出文章写作要任情自然。田锡《贻宋小著书》说:“禀于天而工拙者,性也;感于物而驰骛者,情也。研《系辞》之大旨,极《中庸》之微言,道者,任运用而自然者也。若使援毫之际,属思之时,以情合于性,以性合于道。”“道”是自然之道,“性”是天然之性,“以情合于性,以性合于道”就是任随感情自由发抒。他以为:“随其运用而得性,任其方圆而寓理,亦犹微风动水,了无定文,太虚浮云,莫有常态,则文章之有声气也,不亦宜哉!”
主“任情自然”,典型的当然是明清主“童心”、主“性灵”的一批论家。李贽的“童心”说,核心是真诚自然。他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
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是人的本然之心,而人的本然的童子之心是纯真自然、毫无伪饰的。这是为人的根本,也是为文的基础。为文要有情,而情要真诚自然。“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焚书》卷三《读律肤说》)因此要反对虚伪造作。“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焚书》卷三《忠义水浒传序》)他说:“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语告之处,蓄积既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焚书》卷三《杂说》)他是把情感的自然浓烈提到文学创作十分重要的位置上。这在明代中晚期是一种思潮。李贽同时的焦兹也如此主张。他说:“诗非他,人之性灵之所寄也。荀其感不至,则情不深,情不深则无以惊心而动魄,垂世而行远。”(《澹园集》卷十五《雅娱阁集序》)又说:“诗也者,率其自道所欲言而已,以彼体物指事,发乎自然,悼逝伤离,本之襟度,盖悲喜在内,啸歌以宣,非强而自鸣也。”(《澹园续集》卷二《竹浪斋诗集序》)他是把文学作品的动人力量全归之于感情之充沛自然。艺术的力量就是真诚自然的感情的力量。徐渭提出要写“真我”,“真我”是自然无拘的,“真我”则主张真情,反对伪饰之情。他说:“古人之诗本乎情,非设以为之者也,是以有诗而无诗人。”(《肖甫诗序》)所谓“设情”,就是伪饰之情。无真情,伪饰情,只有求之于文词技巧,这实际不能称之为诗。徐渭的意思,诗就是真情。汤显祖分析《牡丹亭》女主人公杜丽娘的形象,说:“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牡丹亭题词》)她的形象特点就是一往情深。如她在后花园《醉扶归》中所唱道的:“一生儿爱好是天然。”为真情而生,为真情而死,这是她的性格特点,也是这个形象乃至整个《牡丹亭》最感人之处。汤显祖所要着力刻画、强调的就是这一点。公安“三袁”也处处讲真。所谓“独抒性灵”,实质就是主真情。“大抵物真则贵,真则我面不能同君面”(袁宏道《与丘长孺》)。袁宏道说:“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识张幼于箴铭后》)袁宏道说,民间不拘旧有格套,自抒真情的方为真声。他说:“今闾阎妇人孺子所《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
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序小修诗》)。
还可以提出清代袁枚、金圣叹和清末王国维。袁枚在《再答李少鹤》中说:“神韵是先天真性情,不可强而至。”他强调的是真性情。《随园诗话》卷一:“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之外。《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而言情之事,谁为之格,谁为之律?”“率意而言情”,是说感情的率真自然,而格律是人为的。人为须建立在自然性情基础之上。袁枚是反复强调这一点。《答尹相国》说:“情以真而愈笃。”《随园诗话》卷三说:
“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赤子之心,就是孩童的纯真本然的感情。他的“性灵”说,是主真诚自然的。金圣叹则说:“诗者,人之心头忽然之一声耳。不问妇人孺子,晨朝夜半,莫不有之。今之新生之孩,其目未之晌也,其拳未之能舒也,而手支足屈,口中哑然,此固诗也。”(《与许青屿之渐》)他是认为,诗是人的真情真心话,所谓“人之心头忽然之一声”。金圣叹说:“作诗最要真心实意,若果真心实意,便使他人读之,油然无不感叹,不然,即更无一人能读也。”(《唐才子诗》评羊士谔《郡中言怀寄西川萧员外》)金圣叹又说:“作诗须说其心中之所诚然者,须说其心中之所同然者。说心中之所诚然,故能应笔滴泪;
说心中之所同然,故能使读我诗者应声滴泪也。”(《答沈匡来元鼎》)心中之诚然,就是自然之真情。王国维论诗词,强调的也是真情。王国维说:“诗人体物之妙,侔于造化,然皆出于离人孽子征夫之口。感情真者,其观物亦真。”(《文学小言》八)一些作家如欧阳修、秦观等,诗词兼擅,但诗都不如词,为什么呢?王国维说:“与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于词者之真也。”(《文学小言》十三)他提出“境界”说,境界的重要基础是真感情。
王国维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人间词话》六)王国维提出客观诗人和主观诗人之说,客观诗人是写实的,如《水浒》《红楼》;主观诗人是抒情的,他说:“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j”(《人间词话》十七)王国维以为,大家之作就是写真情,“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人间词话》五十六)从写真情出发,王国维提出“隔”与“不隔”之说,所谓“不隔”,就是写景写情真切自然鲜明。王国维提出“赤子之心”之说,他最推崇的词人李后主就是写赤子之心者。王国维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人间词话》十六)他甚至说,诗要用血书。他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人间词话》十八)他是把写真情看做诗词艺术极高的境界。
与强调真情自然相联系的,是主张情的不拘礼义。这里要说到梁代萧纲、萧绎他们的文论。他们是主娱乐、主抒情的。他们的娱乐、抒情,常常是不拘礼义的。萧绎《金楼子·立言》:“至如文者,惟须绮觳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萧纲《诫当阳公大心书》说:“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所谓“放荡”,有不受束缚,不拘成法之意,指诗文创作。但也当包括内容上的放荡。从内容考虑,放荡的“荡”,和“情灵摇荡”的“荡”意思相通。放荡的“放”,和魏征《隋书·文学传序》
说的“简文、湘东,启其淫放”的“放”意思也是相通的。文章放荡,是和立身谨重相对的。立身谨重,是要遵于礼义;文章放荡,则意味着可以不拘礼义。事实上,他们立身也未必完全遵礼义,而文章则真的走向放荡。从内容上说,儒道礼义已经束缚不住他们。所以《隋书·文学传序》说:“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所谓“雅道”,就是礼义之道;所谓“驰新巧”,从内容上说,就是求放荡,求淫放。所以萧纲《与湘东王书》反对京师文体,便说:“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
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
湛湛江水,遂同《大传》。”他是反对模仿儒家经书风格,其实也不愿为儒家经典的礼义思想所束缚。正因为这样,才有他们的被史所批评的“伤于轻艳”(《梁书·简文纪》)的宫体诗。而他们所谓情灵摇荡,文章放荡,不专指宫体,但包含允许诗歌描写男女放荡之情的意思。他们大量的宫体诗创作是证明,他们的理论也可证明。萧纲《答新渝侯和诗书》说:“复有影里细腰,今与真类,镜中好面,还将画等。此皆性情卓绝,新致英奇。”所谓“性情卓绝”,就是情灵摇荡,而这情性,分明指寄情于影里细腰镜中好面之中。他们是把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变成了不拘礼义,情灵摇荡。
自然还要说到明代中晚期的言情的文学思潮。晚明言情思潮,本来就有强烈的反理学倾向。反理学也就包含反礼教、不拘礼义的倾向。汤显祖《牡丹亭》写的就是反对封建礼教的爱情故事。他所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重情理论,显然是针对礼教的。李贽的“童心”说,更具有反传统的精神。绝假纯真的童心,为什么会失去?因为有闻见、道理。“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
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人,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李贽《童心说》)道理闻见又多自读书识义理而来,当时所识之义理,就是居于正统地位的理学。读书闻道理,求明道载道,代古人古道立言,于是“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因此,要保持童心,就要去除理学传统的道理闻见。“荀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李贽《童心说》)。
李贽认为,礼义不应是情性之外的东西。他在《焚书·读律肤说》中说:“故自然发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情性内自有礼义,因此可以任情性任自然,不必拘于隋性之外的礼义。公安派也表现出这一倾向。袁宏道提出“趣”。趣,完全是自然之趣,他在《叙陈正甫会心集》中说:
“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所谓“趣”,就是自然之情性,而趣是与理相对的。袁宏道说:“迨夫年渐长,官渐高,品渐大,有身如梏,有肉如棘,俱为闻见知识所缚,然其去趣愈远矣。”(《叙陈正甫会心集》)
还要说到清代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派。袁枚他们也有反叛传统的思想。这一点和李贽一致,虽然不如李氏强烈。袁枚在《邛州知州杨君笠湖传》中比较自己和杨笠湖的个性特点时说:“余狂,君狷,余疏俊,君笃诚。”狂是他的个性的一大特点。狂,就是不拘礼法。思想上他怀疑《六经》,说:“六经虽读不全信”(袁枚《子才子歌示念农》),说:“《六经》中维《论语》、《周易》
可信,其他经多疑”(袁枚《答定宇第二书》)。生活上,袁枚纵情任性,不讳言好色贪财,“千金买尽群花笑”,娶妾六七人之外,还狎妓寻春,怜爱美貌女性。年逾七十,而多招名媛闺秀为女弟子。文学上更是如此。袁枚说: “诗写性情,惟我所适。”(《随园诗话》卷一)所谓“惟我所适”,就是只要个人情性所欲,一切无所顾忌。袁枚和他的性灵派其他成员们,因此有大量艳情诗。袁枚《姑苏纪事》其五:“但逢胜景须勾留,锦帐香灯汗漫游。何处有花何处宿,果然蝴蝶胜庄周。”是大胆放荡。他的第一门生孙原湘自言:“性为不淫能好色”(孙原湘《早春杂兴》其二),宣称:“人心好色真成例,装点山灵要美人”(孙原湘《真女墓》)。孙原湘的《消夏词》写女性的体态肌肤:“翠纱衫子雪玲珑,坐背风前意态慵。犹恐玉肌人不见,轻绡一尺抹当胸”;“细喘娇吁出浴初,云鬟依旧似新梳。香融汗粉罗巾拭,越显肌肤雪不如”。这是一种玩赏女性的心态。袁枚的堂弟袁树更着眼于性感的女性容貌、肉体,写香肩、玉肌、体滑、香消,暗示云雨之欢,甚至直接写偷情交欢时男女的性心理。袁树的《效(疑雨集)体十三首》,写“脂含垂熟樱桃颗,香解垂襟豆蔻梢”,“羞闻软语情犹浅,许看香肌爱始深”。因此袁枚说:“情之所先,莫如男女。”(《答蕺园论诗书》)袁枚高度评价历代宫体艳诗,说写艳诗者未必人品不行:“以人品论,徐搞善工(当作宫)体,能挫侯景之威;上官仪词多浮艳,尽忠唐室;致光香奁,杨、刘昆体,赵清献、文潞公亦仿为之,皆正人也。”袁枚从经典中为艳诗找根据,说:“缘情之作,纵有非是,亦不过《三百篇》中‘有女同车,伊其相谑’之类,仆心已安矣,圣人复生,必不取其已安之心而掉磬之也。宋儒责白傅杭州诗忆妓者多,忆民者少,然则文王‘寤寐求之’至于‘展转反侧’,何以不忆王季、太王而忆淑女耶?”甚至“《易》始乾坤,亦阴阳夫妇之义”(《答蕺园论诗书》)。他们是全然不顾礼义法度,在情的问题走出彳畏远。
以上只是举了一些较为明显、典型的例子。我们还没有说到宋词。诗庄词媚,词为艳科是传统的说法。所谓艳科,是写男女艳情。我们还没有说到明清大量的言情小说,还没有说到其他大量例子。仅就以上粗略涉及,可以看出,缘情是怎样地形成为历久不衰文学思潮,很多时候甚至是主潮。
文学“缘情”说的提出、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陆机提出“诗缘情”之前,曹丕已经提出了“文气”说。“文气”说的实质是重抒情、重感情气势在文学中表现。“文气”说的提出,主要是经学束缚解除,感情复苏,人的觉醒思潮的产物。后来一些文人自认为他们主言情,是继承“诗言志”的传统,如袁枚。就晚明李贽等人的言情思潮而言,所受到的直接影响是阳明心学,还有禅宗。至于王国维,除传统影响留下印迹外,还吸收了西学。“缘情”思想的具体走向也很复杂,有的主情思潮并不直接带玄学情趣。如主娱乐、倡宫体的萧纲、萧绎他们。
但是,在诸多复杂的因素中,不可忽视玄学及其思想基础老庄的影响。
陆机提出“诗缘情”之前,虽然曹丕的“文气”说其实质也是主缘情,但“文气”毕竟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它流着“情”的血液,也洋溢着汉代“元气”说的风采,而汉代人“元气”说是讲天地并气。即使从作家之气来说,也包含气质、个性、习染、志趣等主观方面的多种因素。它不纯是情的问题。一个事实是,“诗缘情”由陆机在西晋正式明确提出,正刚刚经历了正始玄学的洗礼,正处于玄学风气的笼罩之下。玄学思潮下士人任性纵情正在发展。何晏、王弼、嵇康、阮籍他们正用玄学理论对情、礼关系问题进行讨论。他们都极力用自然去说明情的合理性,如我们在第一章所分析的一样。应该说,玄学的作用不在于一般的启迪人们认识生活和文学中的感情世界,而在于当人们感情复苏之后,从哲理上加深、升华这一认识,使之进一步摆脱政教功利的束缚。它造成一种思想氛围,即情是合理的,文学上的抒情是合于自然的。它使情的发展进一步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因而拓开了更为广阔的天地,为缘情思潮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缘情思潮有不同的走向,有的走向并不直接带玄学情趣,如倡宫体的人们。但有的主抒情,在不拘礼法这一点上,却与玄学思潮相通。玄学时期人们重情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受礼法束缚,“礼岂为我设邪”是很多人的共同观念。关锁感情浪潮的传统礼法大门,是玄学从理论上,玄学名士们从生活上猛烈地把它撞开的。有了这一次冲击,便有了后来情的潮流的不拘礼法的发展。
后来主情的人们,强调的是情的真诚自然。所谓“童心”,所谓“赤子之心”,除了其他因素之外(如“赤子之心”与孟子之说有关),就与老庄玄学有关。《庄子·渔父》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又说:“圣人法天贵真。”从这段话看,庄子是主真情的。庄子有无情的一面,但他主要否定世俗人为之情,而崇尚受之于天的真情。《老子》五十五章也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老子》十章说:“抟气至柔,能如婴儿乎?”王弼注:“言任自然之气,致至柔之和,能若婴儿之无所欲乎?”任情率真,也正是一些玄学名士的性格特点。有了任自然、主真情,便有了阮籍、嵇康,有了陶渊明,也就有了李白、苏轼,有了晚明李贽他们的“童心”说,有了袁枚性灵派的言真情,有了王国维的以真感情为有境界,有了他的不失赤子之心,以血书的词学。
后代一些主情的人们,也可看出他们明显接受老庄玄学的思想。李贽是一个例子。李贽“童心”说无疑是从阳明心学来的。
但他也接受老庄玄学。他作《老子解》、《庄子解》,还有其他文章,都发挥着老庄思想。李贽以“自适逍遥”解《庄》。他解《逍遥游》许由拒绝尧让天下,说:“此言至人无待也,夫尧舜欲让位而许由不受者,使必待于治天下而后足以乐其心,则天下固大于许由矣,许由亦有待之人耳,何足以治天下,故证以接舆之言,然后知尧舜者枇糠也。安有至人而肯以枇糠为事乎哉!”(《庄子解·逍遥解》)无待,故不以天下为累,个体的逍遥自由是最要紧的,而治天下是不屑一谈的。《焚书》其五《孔子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说:“顾后患者必不肯成天下之大功,庄周之徒是已。是以宁为曳尾之龟,而不肯受千金之币;宁为濠上之乐,而不肯任楚之忧。”又是不以天下为累,又是任性逍遥。李贽解《老》,讲见素抱朴。《老子》二十八章:“复归于婴儿”,李贽解道:“夫婴儿百无一知也,而其气至专,百无一能,而其气至柔。专气致柔能如婴儿,则可为抱一矣。”(李贽《老子解》)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贽的“童心”说又是发展了老子的“婴儿”说。
公安派也是例子。袁宏道《途中怀大兄诗》说袁宗道:“《蒙庄》不离手,卓有出尘志。”袁中道《感怀诗》五十八首之十自述:“右手持《净名》,左手持《庄周》。”这是公安“三袁”的共同倾向,可以看出庄子在他们生活、思想上的位置。他们看重老庄的自适。袁中道《导庄·人间世》说:“老庄自适自得,乡愿适人得人。”(《珂雪斋集》卷二十一)“适人得人”则为人所拘束,“自适自得”则逍遥自由。这是老庄,也是“三袁”的生活情趣、思想特色。
一些主情的文人的生活,也可看到玄学下人们任情放达的生活情趣的影子。公安派仍是典型。袁宏道概括他们的五种人生之乐:“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问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见识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名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竞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袁宏道《龚惟长先生》)
重享乐,纵情欲,让人想到玄学下晋代以人世享乐为超俗的那些人们的生活情状。试想东晋毕卓说:“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晋书·毕卓传》),纵情享乐,不正有些相似么!
老庄玄学,玄学思潮,是在后代从生活到文学重情的人们那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