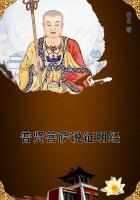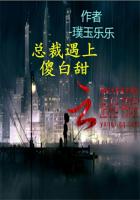在博尔赫斯眼中玫瑰是不可企及的,他曾经将其比喻为“年轻的柏拉图式花朵”。与玫瑰的物质形式相比,他似乎更看重其精神内容:
“通过炼金术从细小的灰烬里再生的玫瑰,永远是玫瑰中的玫瑰。”
这肯定是最后的玫瑰,它已摆脱了众多花朵的状态而获得了灵魂。经历过脱胎换骨的美,才有望构成美的核心。博尔赫斯的一首以《玫瑰》
命名的诗篇,使植物学的玫瑰演变为文学的玫瑰,这是我作为读者的发现。他臆造的玫瑰究竟意味着什么:一种美的更新,一次精神恋爱抑或一件虚无的容器?我却无法猜测。玫瑰自从诞生之初,便与人类所苦苦祈求的美结缘,并一度成为最通俗的审美符号。世界上的玫瑰可以有无数朵,但对玫瑰的热爱却只有一种。它与玫瑰同时诞生,如影随形。跟博尔赫斯一样,我也是这种柏拉图式花朵的信徒。我热爱的玫瑰是所有玫瑰的总和,或者说是其中的皇帝。它是抽象的。
具体的玫瑰,不过是它的化身,并非创造,而是模仿。真正的玫瑰只有一朵:要么是最初的,要么则是最后的。玫瑰的形象在这座星球上的各个国家、各个角落不断地生长着,也不断地重复着,诗人尤其是最热衷的赞美者,乐此不疲地重温着它的投影。所以博尔赫斯在另一篇叫做《黄玫瑰》的随笔中虚构了一个垂危的诗人:“马里诺看见那玫瑰,如同亚当在乐园里初次看见它,并且感到它是在它的永恒之中,而不是在他的词语里,感到我们只能够提及或暗示而不能够表达……这启示之光在马里诺死去的前夜照临了他,或许也曾照临过荷马和但丁。”我们视野里作为个体的玫瑰永远是瞬间的产物、瞬间的造化,而玫瑰的集体,或者说玫瑰的魂魄,则是永恒的。玫瑰的目击者会受到生死的制约(可见审美活动也是瞬间的),而玫瑰本身堪称美的无期徒刑,此起彼落地展览着、宣判着、重复着,令人望而生畏。美的无限总是唤醒我对生命之有限的遗憾乃至对死亡的恐惧。
至少,拥有视觉是美好而宝贵的,玫瑰给我带来了一场视觉中的革命。人与玫瑰的距离,也就是与世界的距离。博尔赫斯在自己的赞美诗中把玫瑰形容为“炽热而盲目的”,莫非因为它的光芒太刺激了,
一种触目惊心的美?不谋而合,他本人也于56岁就任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之际失明。这位追随荷马而去的盲目的大师在自传中写道:
“上帝赐给我80万册书,同时也使我失去光明,这真是妙不可言的嘲弄。”实际上比书籍更重要的是玫瑰。或者说,书籍本身已构成人类文明的玫瑰。80万册书相当于80万朵玫瑰,在世界的一隅同时开放,只是不管是知识抑或花朵,在获得的同时又失去,没能给博尔赫斯重新带来惊喜。从此他再也无法看见玫瑰与书了,如果它们都能被称为世界的象征的话。
博尔赫斯被尊崇为“作家们的作家”这是一种很高明的赞扬,有点“王中王”的意思。与之相比,其他作家只能算是诸侯了。这个称谓,除了表明博尔赫斯是世界文坛的核心人物(至少,他改变了二十世纪文学的面貌)之外,是否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理解:他对作家们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属于小圈子里的知名人士,他的写作对象乃至最重要的读者,是与他同时代的以及未来的作家们。
这样理解是有道理的。博尔赫斯的书很明显是写给作家们看的,或者说,也只有内行才能看得懂。让老百姓读博尔赫斯,不仅无法了解其蕴藏的无穷玄妙,而且肯定会不耐烦的。这不等于是暴殄天物吗?也只有具备较高文化修养和鉴赏能力的作家们(包括想当作家的文学青年),才能细心地并且耐心地品味着博尔赫斯那迷宫一样的境界。跟这位老先生捉迷藏,也是需要机缘与福气的。又有几个人真正摸到过他云里雾里的山羊胡子?在每个国家,包括他的祖国,博尔赫斯的书发行量估计都不会特别大。他恐怕永远也成不了畅销作家。拿版税的话,多多少少要吃点亏。在他有生之年,一些比他功底浅的人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他偏偏落选了。有什么办法呢?谁叫他属于孤芳自赏的那一类人呢。然而他还是赢得了比诺贝尔文学奖更崇高的荣誉,“作家们的作家”。这只属于他一个人。用句俗话说,这就是师傅,在作家们中间,他属于师傅一级的。哪怕他带过的徒弟获得诺贝尔奖了,还得尊称他为师傅。当然,博尔赫斯从没有正经收过徒弟,但确实有不少作家,从博尔赫斯那儿偷学过一两手。
我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听说博尔赫斯的。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引进了一大批外国大师的作品,令人眼花缭乱。我作为众多的文学青年之一,得知博尔赫斯是“作家们的作家”,不禁对他刮目相看。应该说,是这个称号首先把我打动了,使我意识到一种超凡脱俗的写作方式:为作家们而写作,是多么让人羡慕的一件事。当然,博尔赫斯的作品也一点没让我失望,真是名不虚传啊。而今,似乎已非文学的时代,文学青年是越来越少了,大师与经典也备受冷落。但在我这个老了的文学青年眼里,博尔赫斯依然是最耐读的。在我的藏书中,他的书要比别的大师的作品磨损得更厉害一些。别瞧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普鲁斯特、乔伊斯什么的,名气挺大,他们的书很难让人读到一遍以上。而我写这篇文章之前,已把博尔赫斯的书整整读了七遍。以后空闲时肯定还会有兴趣再翻一翻。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博尔赫斯与众不同。大多数小说家的才能,仅限于讲故事,哪怕讲得天花乱坠,听完一遍也就完了,他随着你阅读过程的结束而贬值了。博尔赫斯的才能,则是教你怎样讲故事。他是教师爷。他的书是小说创作的辅导教材,内部发行。
我知道有个作家叫马原的,被一些同行称为“中国的博尔赫斯”,既指他深受博氏影响,又指他影响了一代本国的小说家。他对此称号有点受宠若惊,但又表示很惭愧:“我哪能跟他比呀。他是我最崇敬的大师了。是博尔赫斯引导我重视小说的方法论,他是这方面的革命家。而我,顶多只算个改良主义者。”(大意如此)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博尔赫斯首创了小说的方法论,至少,是他强调了方法论的重要性。从博尔赫斯开始,小说的文体产生了一部分的哗变:“怎样写”似乎比“写什么”更为重要,更为显示作者的价值。你能说这不是一场革命吗?
博尔赫斯,应该属于书斋式作家吧,或者说经院派作家。但是他丰富了作家们的书斋,他本身也已成为作家们的学院。包括在中国,都有了他的传人,甚至传人都有了传人。譬如我前面提到的马原。他那富于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西藏小说,很明显有博尔赫斯的影子。
我想,作家可以分为两种:为多数人而写作的,和为少数人而写作的,博尔赫斯无疑属于后者。同样,文学也可据此划分为两类。中国还有个诗人,王家新,写过一篇文章叫《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纯粹的文学,是应该献给无限的少数人。无限的少数人,只要大于一就可以。哪怕仅仅献给自己。
认识博尔赫斯之后,我倾向于这样的文学观:宁愿自己的作品只被一个人读一千遍,也不愿意它被一千个人只读一遍。前者其实比后者困难得多,也伟大得多。你能说这种追求不是很有意义吗?
博尔赫斯的第一部书《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热情》,是自费出版的,只印了三百本。他知道搁在世俗的书摊上是不会有多少人理会的,他却寻找到了散发书的一种办法。他发现《我们》(那个时代最古老、最有名的文学杂志之一)编辑部的许多人都把大衣挂在衣帽间里。于是他带着五十或一百本书去找某位熟识的编辑。编辑开心地望着他说:“你是想要我替你卖书吗?”博尔赫斯回答:“不,我虽然写了这本书,但我不是精神失常的人。我想我可以求你把一些书悄悄塞到那些挂在那儿的大衣兜里。”编辑照办了。等博尔赫斯再去那儿时,发现一些大衣的主人已经读了他的诗,甚至有人还写了评论。用博尔赫斯自己的话来说:“我就是这样获得了一点诗名。”恐怕正是从那时起,博尔赫斯就开始选择自己的读者群了,或者说给自己的读者定位了。《我们》编辑部里的主人抑或宾客,必定都是文学爱好者,起码具备鉴赏的素质,不至于给《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热情》泼去一盆冷水,这无形中鼓励博尔赫斯走上了“为作家们写作”的道路。世界虽然很大,但对于博尔赫斯来说,能拥有那些温暖的大衣兜就足够了。
我的朋友潘向黎,听了这个故事后做过精彩的点评:“不论以何种方式写作,做三件事也许是明智的:说自己想说的话,找到自己的声音,然后找到那些大衣口袋。不过,《我们》编辑部的衣帽间充满了高尚的暗示:关心文学,有真正的品位与鉴赏力。而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到哪儿找到这样充满可能的大衣口袋呢?不过我不认为作家应该放弃寻找。”
博尔赫斯是成功的。他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大衣口袋,已经不仅限于《我们》编辑部的衣帽间了,而且也不仅限于他的祖国,他给世界各地的无数作家的衣兜里,都递送了一份丰厚的礼物。想到这里,我下意识地差点把手塞进自己的衣兜,摸一摸吧,真希望那里面,会奇迹般地出现一本博尔赫斯偷偷塞进来的新书,可惜这位“作家们的作家”已经死了,他再也不能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惊喜了。我的心,空落落的。博尔赫斯是作家们的师傅,他其实也是有师傅的。还有一个人,似乎比他更有资格称为“作家们的作家”那就是卡夫卡。因为卡夫卡甚至影响过我们这位“作家们的作家”。按道理说,该算是“作家们的作家的作家”了,虽然这有点拗口。换用民间的说法:师傅的师傅,就是祖师爷了。这并不夸张。卡夫卡是公认的二十世纪现代派文学的鼻祖。在现代派文学里,他至今仍坐着第一把交椅,博尔赫斯不仅出道比他晚,排名也在他的后面,他们都属于特立独行的那类作家,博尔赫斯并不掩饰自己对卡夫卡的关注与崇敬:他还专门写过一篇《卡夫卡及其先驱者》,提到“作家的劳动改变了我们对过去的概念,也必将改变未来”。不知他是否意识到:卡夫卡也正是他本人的先驱?
卡夫卡生前比博尔赫斯还要寂寞,甚至不可能拥有编辑部衣帽间里的那些大衣口袋。他相当于文学界的梵高,属于死后成名一类,他立下的遗嘱里,要求将自己的全部手稿焚之一炬:幸好这遗嘱被背叛了,才使得今天我们许多作家的书架上,都能够陈列着一套卡夫卡的著述。是的,他并没有刻意寻找那些大衣口袋,却照样在文学史上获得了不可或缺的位置。这是一位终生生活在不幸之中的幸运儿!
在所有的作家里,我觉得博尔赫斯与卡夫卡靠得最近;他们的作品都带有最鲜明的个性。当然,他们也有区别;如果说博尔赫斯是为作家而写作,卡夫卡则表现得更为彻底,他纯粹是为自己而写作——甚至不曾寄希望于额外的读者;读者这个概念对于他都是多余的,所以,卡夫卡也是博尔赫斯无法逾越的。他已不可能走得更远了。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分别都为中国的长城写过文章,卡夫卡写的是《万里长城建造时》,在这篇未完成的小说中,他将长城与巴比塔相提并论,表达了“永远不能达到目的地”的思想;博尔赫斯写的是《长城和书》。不知他是怎么产生灵感的?是很自然或很偶然地想起中国的长城,还是受卡夫卡那篇文章的启发?他们二位不约而同地赋予了长城以迷宫的特性。应该说,卡夫卡和博尔赫斯,都属于那种在迷宫里跋涉并且流连忘返的大师。“如果拿《杜撰集》中的某些迷宫同卡夫卡的迷宫比较,就会发现这样的区别:博尔赫斯的迷宫属于几何类型或国际象棋类型,像芝诺提出的问题一样会引起某种精神上的痛苦。这种痛苦产生于游戏因素的完全明了。卡夫卡的迷宫却相反,它们是黑暗的走廊,既没有尽头也无法探知。痛苦是噩梦般的痛苦,产生于对游戏力量的绝对无知。在前者的迷宫中存在着非人类的因素,而在后者的迷宫中的因素完全,也许,是人类的。”这是阿根廷作家埃内斯托·萨瓦托所作的评判。他在比较卡夫卡和博尔赫斯的区别之时,无形中又肯定了他们的共性:这二位都比其他作家更痴迷于迷宫的设计乃至破译;他们掌握着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的秘密。他们的作品,也真正是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的。
为作家而写作的博尔赫斯,多多少少有点匠人的习气,哪怕他已跻身于巨匠的行列,我们仍然能够发现其对手艺的炫耀。为自己而写作的卡夫卡,则更像个圣人,甚至摆脱了一般作家难以避免的职业性或行业性。卡夫卡的生平更像是一个文学神话,死后成名的卡夫卡本人也几乎被今人神化了。如米兰·昆德拉所说:“创造卡夫卡的形象和他的作品的形象,同时创造了卡夫卡学。卡夫卡学是为了把卡夫卡加以卡夫卡学化的论说;用卡夫卡学化的卡夫卡代替卡夫卡,在卡夫卡学者笔下,卡夫卡传记成为了圣徒传记。”博尔赫斯把文学视为技艺,他成了作家们的师傅,至少我是以某种学徒的心理读博尔赫斯的,他真不愧为一代名师啊!卡夫卡则把文学当作宗教、当作真理,他以神父的形象成为离上帝最近的人。博尔赫斯与卡夫卡的区别,其实相当于图书馆馆长与修道院院长的区别。所以博尔赫斯会努力寻找高明的读者,那些敞开的大衣口袋,自我封闭的卡夫卡则紧紧捂住自己的衣兜(那里面揣着零乱的手稿),生怕在别人面前暴露内心的秘密。卡夫卡式的拒绝比博尔赫斯要彻底得多,不仅拒绝平庸,而且拒绝世俗,他的作品在对读者的拒绝中成为了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