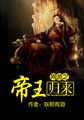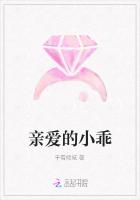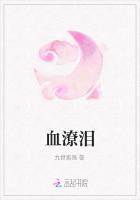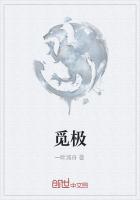我作为一个外省青年携带着自己的文学梦想投奔京城,是一九八九年;在北京火车站顶着烈日搬运行李的时候,突然想到了沈从文。
我想到大半个世纪以前湘西人沈从文第一次来北京,几乎和我现在的年龄相当,也就二十岁出头,莫非我又在无意识地重复他的经历?于是我开始关心:一九二三年沈从文挟着铺盖在前门车站下火车的那一瞬间会想些什么,是否会想到前辈抑或后人?他的心情被公开过,据传说月台上的沈从文对眼前豁然敞开的这座古老城市表达了铮铮誓言:“我是来征服你的。”
半个多世纪以后,这句话依然炙手可热。从此沈从文这个名字便向湘西风景如画、民俗敦朴的边城作永远的告别,而进入了北京城的记忆。
后来我把这种想法跟先于我两年毕业分配到京城的武汉大学校友汪立波说起过,他惊喜地睁圆眼睛:“我们居然不谋而合!”原来他在火车停靠北京站之时,也想到了沈从文,他除了跟我同样热爱沈从文及其作品之外,还有个更为自然的理由:与沈从文同是湖南人,他在追随这位著名的乡贤的足迹。在此情此景下会想到沈从文的,又岂止我和汪立波两人呢。
20世纪以来自外省迁徒至北京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数目,是无法计算了,他们都拥有相似的命运轨迹。北京在他们的印象中,都曾经是一座全新的城市,他们会永远保持这第一印象。虽然许多人初来北京时的经历与心情,已经失传了。
我肯定不会忘却自身进京的旅程,而沈从文前辈那遥远的经历仍然被我关注着:他刚来北平的那年冬天,困顿在湖南会馆一间没生火炉的小屋,弹尽粮绝,连棉袄都买不起,幸而郁达夫根据一封信冒着鹅毛大雪找到了这位陌生的文学青年,发现他在用冻僵了的双手伏案写稿,于是立即解下自己的围巾替他围上,然后领他出去吃饭,并把衣兜里剩下的几块钱全给了他。
这是一段脍炙人口的文坛佳话,只是有点过于冷冽而已,但这冷冽中亦包涵着人情的温暖,让听众既感到心酸又不无安慰。
沈从文在二十岁以前长期在湘西一带小码头流浪,如他自己所说,“我的青年人生教育恰如在这条水上(沅水流域)毕的业。”北平对于他,不过是一座继续流浪的城市,乡村流浪汉变成了城市流浪汉。
青年沈从文的性格魅力完全是流浪造成的,包括他大多数作品的素材,都取之于早期流浪的阅历。我以为他代表了中国式的流浪汉文学,在路上,永远在路上,从旧中国农村的水路、陆路直到都市的柏油马路,流浪汉的心永葆青春……
青年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著名的流浪汉(有人曾拿他跟马克·吐温相比,根据两人年轻时相似的经历,但我觉得也有高尔基“在人间”及“我的大学”时期的影子)。
我来北京,在不同的时间与相同的地点,体验了当初折磨过沈从文的那种流浪的感觉。我也曾经囊中羞涩、捉襟见肘,曾经在没有暖气的平房里过冬,曾经饥寒交迫地写作,构筑纸上的风景,我甚至还曾经在他府右街达子营故居附近租过房子,感觉到离他或他的青年时代越来越近了。虽然我无法遇见郁达夫了,但可以把周围关照过我(譬如有过一饭之恩)的朋友想象成郁达夫。
继续流浪,在沈从文的身影后面,我继续流浪。我吟咏的诗篇相当于流浪的记录。继续流浪,直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可以给沈从文前辈平静地写一篇文章了。同时纪念自己的青春。我们都曾经从千里之外把青春作为唯一的礼物奉献给北京这座伟大的城市。
这是我与沈从文之间最明显的缘份,因为我只是个迟到者,只能通过他的文字揣测、认识其音容笑貌。但我相信,流浪者的品质是能够通过特殊的方式得以感化并遗传的。
沈从文之于北京城曾几进几出。施蛰存回忆:“为新文学运动和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潮所感召,从文于一九二三年来到北平,没有熟人,没有亲戚,孤家奋斗。一九二四年,已在《现代评论》和《京报副刊》上发表创作,大约此时已受知于胡适。以后,逐渐认识了徐志摩、郁达夫、杨振声、朱光潜、梁实秋、朱自清等人……”寥寥数语,勾勒出他初初安营扎寨的轮廊。
然而四年未满,就因军阀张作霖在北方制造白色恐怖,而随同冯雪峰、丁玲、胡也频等一批青年文人南下,移居上海。三年后又返回北平,在中国公学任教,因胡适的推荐。一九三七年因芦沟桥事变缘故随同清华、北大师生(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南迁昆明。两度离开北京城皆为避难(战难与国难)。
一九四六年沈从文携带家眷绕着上海回到光复后的北平,他的后半生便完整地属于北京城了。
这就是沈从文三进北京城的故事。沈从文最终回到北京,是颇受欢迎的,子冈当即在《大公报》上写了篇《沈从文在北平》:“在一个茶会里听到说沈从文在八月二十七日到了北平,正像其他万千读者一样,虽然只能从幻想中画出化的轮廊,却感到亲切的喜悦。最近他发表了《忆北平》,不想他马上到了北平。我经过景山前街的红墙,在洋槐树下走过,寻找沙滩的北大教职员宿舍,原来就在红楼的贴隔壁。”
在该文结尾他兴高采烈地告诉读者,“如果你在北平的庙会或小胡同碰见一位提了网线袋,穿着一件灰色或淡褐色的羊质长衫、身材矮小瘦弱、一脸书卷气、眯着眼睛在书摊子上找旧书或是在找门牌号数,说一口湖南、北平、云南杂糅的普通话,那便是沈从文。你可以告诉他,他该去理发店理发啦。”
在他眼中,刚刚从沦陷的历史中挣脱的焕然一新的北京城,亦将因沈从文的重新出现而增添那么一丝光彩。
夸张地说,我觉得沈从文有两个,一个是湘西人沈从文,一个是北京人沈从文,他们共同组合成20世纪一位文学大师完整的人生历程。
沈从文生长于苗汉杂居的湘西,未曾受过正规的中学和大学教育,他的文风与人格都带有蛮荒之地所孕育的淳朴与野性,如施蛰存所说:“在他的早年,中国文化传统给他的影响不大。这就是他的大部分作品的题材、故事和人物理解的基础。各式各样单纯、质朴、粗野、愚昧的人与事,用一种直率而古拙、简净而俚俗的语言文字勾勒出来。他的文体,没有学院气,或书生气,不是语文修养的产物,而是他早年的生活经验的录音,这是一个苗汉混血青年的某种潜在意识的偶然奔放。”
沈从文一贯自称是永远的乡下人,甚至在向张兆和求爱时也诗意地表达“让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兆和心有灵犀地给他回了电报:“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弄得发报员好生奇怪,猜不出是什么暗号。
这不是一般的乡下人的爱情,这简直是乡下的诗人的爱情。他移居北京后,接受了城市文明,跟知识分子中的绅士派广泛交往,沾染了不少绅士气,但仍然带有乡村绅士的倾向:“早年为了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革命而投奔北平的英俊之气,似乎已消磨了不少,他在绅士们中间,还不是一个洋绅士,而是一个土绅士。”(施蛰存语)
他成为北京人后,由于血统与身世的缘故,依然是一个复杂的北京人,或者说是一个复杂的北京文人。
当然沈从文自己意识不到这点,1933年他发表《文学者的态度》,把南北作家划分为“海派”和“京派”,褒扬京派而贬低海派,并自居于京派之列,诱发了一场轰动南北文坛的大争论。沈从文作为“海派”“京派”之争的始作俑者,对自己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京派文人而不无自豪。
李辉转述过陈思和在《巴金传》中对三十年代包括沈从文在内的京派文人的评价:“这些以清华、燕京大学为中心的几代由作家、理论家组成的文人,是在‘五四’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中形成的。他们于朴实中见开放,对外来思潮也不保守,受到的压迫与政治干扰暂时还不大,正是新文学发展的理想时机”。他进而联想到“这种自由主义传统,是否也包含着这样一层含意:像沈从文这样的作家,作为一个个体,在构造自己的文学理想的同时,将一颗不安分的灵魂,同源自湘西山水的性格结为一体,该是同样的美妙。这种不安分,后来被以寂寞表现出来的一种平和所湮没了。人们更多地看到的,只是他并非出本意的与文学的疏远,以及久久的沉默。”
李辉把沈从文身上的这种不安分称为“极为难得的‘五四’传统”,这自然与沈从文生活在爆发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北京城、以及他个人努力弘扬京派文人的精神不无潜在关系。
虽然沈从文的后半生属于北京城,但解放以后由于一言难尽的原因,他出人意料地告别了自己的文学时代。用黄苗子的说法就是“我们这位‘五四’以来具有影响的作家,由于从事‘文物’,便没有生产‘文章’。”
他改行美术考古学,在故宫博物馆的青灯黄卷中浮沉,由文学转向学术,另一个沈从文出现了,并推翻了自己的前身。
黄苗子还辛酸地描绘过浩劫期间的沈从文:“天安门城楼上的男女厕所,沈从文认认真真地天天去打扫(后人如写‘天安门史’,应该补这一笔),他像摩挲一件青铜器那样摩挲每一座马桶。”
沈从文后半生是寂寞的,简直跟他的前半生判若两人,北京给过他辉煌,也给过他萧瑟。
他的得意门生汪曾祺说:“沈先生五十年代后放下写小说散文的笔,改业钻研文物,而且钻出了很大的名堂,不少中国人、外国人都很奇怪。实不奇怪。”
而常风则说:“沈从文先生的后半生的贡献是大家不会想到的,也是他本人始料所不及。他的古文物学者、专家的声誉三十年来让人忘记原来是小说家了。他在知命之年,不得不离开他原来的文学专业,改行重起炉灶。”
据说他的葬礼遵其遗嘱未放哀乐,而改放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他生前最喜爱的音乐。莫非是有原因的?悲怆啊悲怆,老人的悲怆正是中国的悲怆,今天夜里,我在纸上欲为之一哭。
沈从文后半生在北京城里,像任何一位平凡的北京人一样生活,默默经历着岁月的流逝,对于我们国家的文学来说这是多么巨大的损失。今人与后人所能读到的,都只能是他前半生的作品了。以《边城》为代表的沈从文,是属于北京城的,又是永远属于湘西的边城的。他永远是边城的哨兵。
幸好他后半生撰写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被称为“前无古人的巨著”。他不再剖析今人的灵魂,改而研究古人的服饰。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他在北京城里一段人生的结晶,可算献给这座作为其生命归宿的城市的一份厚礼。
我在北京,觉得最值得反复玩味的名胜古迹乃是故宫博物馆,这是令人百读不厌的一部传世经卷。每次游览故宫博物馆,就要像当初刚来北京下火车时一样,想到沈从文。这里是他工作过的地方。
如果说我在北京火车站想到的是一位遥远的青年,在故宫博物馆想到的则是一位遥远的老人。他们是同一个人吗?
他们确实是同一个人。只不过我的心情有所不同罢了。
我不禁胡乱猜测: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是否也曾经伴随沈从文经历过一次沉重的脱轨,或者说,沈从文后期的沉寂是否贯彻了一个时代的缩影?否则为什么每当想到沈从文,我就一阵心疼?
对于一位作家而言,我既是其作品的读者又是其命运的目击者,我借助历史的潜望镜目睹了作家本人无法控制的一次脱轨与转折(或用史料中“改行”的说法)。
也许我所关注的这趟火车并未脱离这个时代的轨道,但是上帝以扳道工的面貌出现,用一个隐秘的手势,就不易察觉地改变了它的运行方向。火车依然在行驶,只不过是在与自身的惯性相反的方向行驶,它所体验到的割舍灵魂的疼痛,已不可言传了。
最终,一切个人的疼痛会被世界的麻木所取代。这是一次没有事故现场的脱轨,没有预谋与记载的寂灭,对于其承受者而言,似乎也没有怨悔。哀莫大于心死,或许选择遗忘正是尊重记忆的最佳方式。
在浩劫期间,沈先生留存的自己著述的样本被全部销毁,他好像并未感到可惜,更不加以回忆。
云开雾散之后,沈先生的传记作者凌宇前去采访,惊讶地发现:“时间过去了三十年乃至半个世纪,许多作品及一些笔名连沈先生自己也忘却了,我偶有所得——那些以沈先生忘却的笔名发表的作品,便请沈先生加以验证。”
据说常常出现类似的情形,凌宇说出一篇待验证的作品名称,沈从文摇摇头:“记不得了。”于是凌宇便复述作品的内容。还不等他说完,沈先生老人便孩子一样天真地拍起手来:“是我的,是我的!”他笑着,眼里有了泪花,似乎很高兴。
凌宇描述的这个细节我总是忘不掉,仿佛亲眼目睹了老人捕捞到失去的记忆时那挂着泪花的笑脸。
想到沈从文的晚年,我脑海便浮现出这么一张笑脸,内心总要一阵痉挛。我不再怀疑,在特定的背景与压力下,沈先生曾忍住疼痛亲手掩埋了自己的一段文学记忆,或者说得更悲怆点:亲手掩埋了自己,把自己曾珍视的精神建筑一举夷为废墟。他并非患有先天性的失忆症。
沈先生的后半生,是在自己的文学废墟中凄凉地度过的。当然,他也在废墟中一砖一瓦地堆砌起另一座全新的宫殿:《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所以说他并不是完全的失败者。
黄苗子曾评价过沈先生后半生在文学上的荒芜(即作家身份的过早终结):“可是沈先生对于这一点,他并没有介意,至少在表面上。他永远兴致极高地谈他的美术考古,沈先生是否就永远忘记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了呢?并不。最近我同沈先生谈起,在国外,有一位研究他的文艺作品的学者得到了博士学位。沈先生羞涩地笑了一笑,大拇指按着小指伸出手来,轻声地更正说‘三位了’。”
沈从文的故乡是湖南的凤凰,被新西兰老人艾黎称为“中国最美的两个小城之一”。他本人就是一只凤凰,一只能在烈火与灰烬中获得新生的神话之鸟。沈从文是在类似于凤凰涅槃的痛苦与幸福中送别旧我而迎接新我的。
沈从文自称乡下人,他从蛮荒的湘西第一次来北平时,肯定有一种“进城”的感觉。他相当一部分作品都是来到城市后通过回忆写下的,主题依然是魂索梦绕的乡情民俗。因而获得了双重身份:既是一个生活在城里的乡下人,又是一个不断怀念着乡土的城里人。
他即使在干燥寒冷的北方城市,文笔仍然凝注着旧中国南方农村河流与泥土的气息乃至巫鬼诗情,仿佛刻意要为城市读者创造一个乡村的神话。沈从文不曾割舍自己灵魂的根须与远方广袤原野潜在的联系,他的乡土情感是真正的城里人(或城市文人)无法想象与比拟的。
他既为旧中国古老的农业文明吟唱了一曲划时代的挽歌,又为缺乏想象力的现代城市生活馈赠一首天外来音般的田园诗,炊烟弥漫的乡愁因为都市背景的烘托而愈显缠绵悱恻。
他不仅是乡下人,更是乡下的诗人(农民式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不仅是城里人,更是一个反复咏诵着“归去来兮、田园将芜”的城里的隐士(用古人的说法,大隐隐于市)。至于他的后半生,又做了北京城里的文学隐士,告别文学而归逸,隐逸于秦砖汉瓦、青灯黄卷。就像徐志摩再别康桥一样,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沈从文曾于四十年代写下自我预言:“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者命定的悲剧性”。
我估计,随着现代大工业文明对乡村精神的蚕食与消化,又有谁敢于把乡土情感视若至高无上的精神财富,至少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它已接近于没有传人的遗产了。
所以,沈从文,也将是中国文坛上的最后一个乡下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