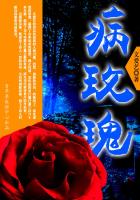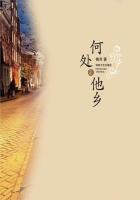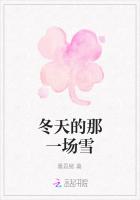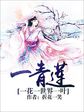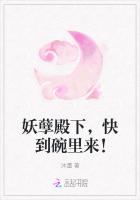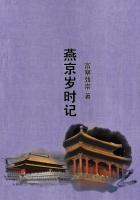北仑博物馆展厅里陈列着几个陶罐,它们不是整个的完整的罐,是考古专家根据出土的零碎陶片用黏土拼接、补充、复原而成。这些陶片出自沙溪新石器时代遗址。
20世纪80年代,北仑柴桥沙溪村办起砖瓦厂,村民在村外一个叫蛇山的土丘旁取土,挖开土层,出现了陶片,越往下挖碎陶片越多。这是什么年代的?有什么来历?村里没人知道。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了上级的重视,1987年宁波市考古研究所专家对那个地块作试探性挖掘,确认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址在浙江省内发现不多,在人类学研究领域,新石器时代遗址对探究文明起源具有重要意义。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仑区博物馆组成考古小组,于1994年和1997年两次对遗址进行发掘,取得了丰富的考古发掘成果。
1994年初冬,经当时北仑博物馆馆长陈美丽老师介绍,我到沙溪采访。考古小组住在村大会堂里,他们自己买菜做饭,条件比较艰苦。那个时节西风凛冽、天气阴冷,专家每天都在遗址现场布探方、去表土、取遗物,工作强度很大,又很细致。我在大会堂看到的出土遗物被分门别类摆放在碗里,有石器、陶片、橡子、苇席状编织物,橡子和编织物已经发黑。那片编织物面积约50平方厘米,编织纹理十分清晰,专家对此十分欣赏,认为其工艺水准一点不逊色于今人产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块石锛,它的材质呈淡绿色,那种很纯净的淡淡的绿,非常赏心悦目,以至于多年之后我回忆起这块石锛,仿佛依然历历在目,这种颜色的石块现在很少见了。石锛的形状是不规则的长方形,长约10厘米,宽约5厘米,一边厚约3厘米,一边厚约2厘米,各个磨面的交棱均光滑平直,有一个长方形面打磨成弧面。我很惊讶那个弧面的加工水准,因为从工艺上说,打磨平面是容易的,而打磨弧面有一定难度,加工者按压石块时除了要在垂直方向均匀用力,手腕还要在一个相对小的角度范围内徐徐转动,这样弧面才能够形成。那个石锛的弧面线条是完整、清晰的,弧线没有断裂,可见弧面是一气呵成的,这更显示出加工者娴熟的技巧和丰富的经验。
当时我曾向专家讨教沙溪遗址的人类学意义,专家审慎地说挖掘还没结束,下结论为时尚早,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沙溪遗址与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基本属于同一时期,这一片土地同样是古老的。
沙溪遗址两次发掘总计面积370平方米,出土遗物大量是陶片,有近两万件,专家认定器型是罐、鼎、釜、盘、盆、豆等。石器数量很少,器型有锛、镞、砺石几种。专家发掘出两个坑,一个是橡子储藏坑,边长1.4米,坑中套坑,内坑深40厘米,里面有很多橡子,坑口的三面罩着木条捆扎成的覆斗状顶,一面开口,供人出入;还有一个是普通的储物坑,长一米多,宽70厘米,坑口覆盖木排连接成的盖,坑底覆盖树皮。
沙溪遗址的主体是多层灰面,它的现象十分特殊:底部是一层厚薄不等的草木灰,灰层中夹杂陶片,还有少量动物骨、鱼骨、木条等,这层灰面的上部覆盖一层普通的青灰泥土,覆土上部又是另一层灰面,如此反复,最多处叠压了十多层灰面。多层灰面遗迹的面积超过2800平方米,范围相对较广。
发掘结束后,专家又经过多年的研究,于2005年发布了发掘报告。专家结论:沙溪遗址的内涵由三种成分构成。第一种是河姆渡文化的传统因素,沙溪陶釜的形态、绳纹在河姆渡遗址已经出现,有些陶釜的中腹以下胎壁极薄,这是制陶工艺进步的表现。第二种是良渚文化因素,这从沙溪遗址的鱼鳍足鼎、竹节把豆、圈足盘等器型可以看出。沙溪遗址的粗泥陶器广泛分布于舟山群岛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因此沙溪遗址与浙东沿海岛屿同属一个经济文化区,这是它的第三种文化因素。
沙溪遗址特殊的面积如此之广的“多层灰面”曾使专家困惑,因为这一现象偏离了专家以往的思维定势,经过比对、甄别,最终专家推测,“多层灰面”遗迹是因某种宗教性的仪式造成的。由此我大胆猜想:先民在每一次出海捕鱼之前,都要在这片宽敞、平坦的区域焚火祭祀,祈求风平浪静,祈求满舱而归。下一次祭祀仪式开始前要覆土整理场地,以示每一次出海都是新的开头,都有全新的结果。
不论古今,人民对于生活的期待总是相同的、朴素的。太阳从东海升起,每一天太阳都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