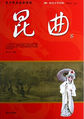1.崇高—优美式艺术
这是ROUGE DIOR化妆品“烈艳最新呈现”篇的广告画面,运用朱红、黑、白涌动的涡旋状造型,渲染唇膏造成的唇红与齿白的美丽。
这幅抽象绘画通过色彩形式对视觉的刺激,突出口红之艳丽。高级唇膏的颜料,在制作工艺的精细上已达到极端,纯净度也达到了视觉经验的顶点。不过,以往的广告与现实一样,只是将口红涂在美女的口唇上来展示它们的美艳。口红涂上美女的口唇时,即会成为美貌的一部分,融汇在漂亮的面容之中。当受众被美貌吸引时,无论口红多么艳丽,也难以引起单独的注视,唇膏只能是成就女性魅力的无名英雄。而本画却让这种极端纯净饱满的口红离开女性口唇,单独大面积地展示出来。由于面积与双唇相比极端的大,再加上没有女人美貌与口唇性感的干扰,人们就会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口红上,从而被烈火般的红艳所灼烧震撼。口红色彩面积极端大造成的罕有与陌生,是本作吸引无意注意的原因。
画中的黑色、红色、白色,是对口唇、牙齿及脸部阴影色彩的抽象概括。在黑、红、白各色线条旋涡般的巨大涌动中,黑、白色的陪衬使红色达到了艳丽妖冶的顶点,而黑、红色的反比,又使白色上升到皓朗洁净的极端,从而对视觉形成震撼惊异的强势张力刺激。这是此画的崇高。
画中各色,线条柔曲飘逸,状如旋涡与木纹。三种色彩虽有重叠,但每种自保纯净,决无浑浊,这些协调气氛的营造,使画面产生了雅致和谐的优美。画面再现了唇膏的色相,纯度与亮度,这是画中的真。画的形状与实际上的口唇貌相相去甚远,是抽象的写意之假。这件作品的崇高、优美、真、假带来的快感体验,引起读者的浓厚兴趣。
2.崇高—悲剧式新异艺术
波兰作家伏尼契的《牛虻》是这种艺术的杰出代表。“牛虻”名叫亚瑟,是贵族寡妻与主教的私生子。母亲死后,亚瑟视这位神父为良师慈父,在忏悔中将自己参加的反奥地利侵略的秘密组织情况和盘托出。当他的战友遭到逮捕,他的女友骂他是叛徒并打了他耳光时,他这才省悟是教父告了密。他只身流浪到南美13年,满身伤病并瘸了一条腿,回到意大利后继续同侵略者进行斗争。在同敌人的一次交火中,由于神父突然用身体挡住了他的枪口,在片刻的犹豫中他垂下了手枪被敌人逮捕。他被处死后,神父也因精神分裂而亡。小说中最为震撼的描写是亚瑟刑场上的从容就义:
执行枪决的六名士兵扛着短筒马枪,靠着长满常青藤的墙壁站成一排。……牛虻回过头来,露出最灿烂的笑容。……他再次要求不要蒙住他的眼睛,他那傲气凛然的面庞迫使上校不情愿地表示同意。他们俩都忘记了他们是在折磨那些士兵。他笑盈盈地面对他们站着,短筒马枪在他们手中抖动。“我已经准备好了。”他说。中尉跨步向前……“预备—举枪—射击!”牛虻晃了几下,随即恢复了平衡。一颗子弹打偏了,擦破了他的面颊,几滴鲜血落到白色的围巾上。另一颗子弹打在膝盖的上部。烟雾散去以后,士兵们看见他仍在微笑,正用那只残疾的手擦拭面颊上的鲜血。
“伙计们,打得太差了!”他说。他的声音清晰而又响亮,那些可怜的士兵目瞪口呆。“再来一次。”
这排马枪兵发出一片呻吟声,他们瑟瑟发抖。每一个人都往一边瞄准,私下希望致命的子弹是他旁边的人射出,而不是他射出。牛虻站在那里,冲着他们微笑。……突然之间,他们失魂落魄。他们放下短筒马枪,无奈地听着军官愤怒的咒骂和训斥,惊恐万状地瞪着已被他们枪决但却没被杀死的人。
统领冲着他们的脸晃动他的拳头,恶狠狠地喝令他们各就各位并且举枪,快点结束这件事情。他和他们一样心慌意乱,不敢去看站着不倒的那个可怕的形象。……
“上校,你带来了一支蹩脚的行刑队!我来看看能否把他们调理好些。好了,伙计们!把你的工具举高一些,你往左一点。打起精神来,伙计,你拿的是马枪,不是煎锅!你们全都准备好啦?那么来吧!预备—举枪—”“射击!”上校冲上前来抢先喊道。这个家伙居然下令执行自己的死刑,真是让人受不了。
又一阵杂乱无章的齐射。随后队形就打散了,瑟瑟发抖的士兵挤成了一团,瞪大眼睛向前张望。有个士兵甚至没有开枪,他丢下了马枪,蹲下身体呻吟:“我不能—我不能!”
烟雾慢慢散去,然后冉冉上升,融入到晨曦之中。他们看见牛虻已经倒下,他们看见他还没有死。霎时间,士兵和军官站在那里,仿佛变成了石头。他们望着那个可怕的东西在地上扭动挣扎。接着医生和上校跑上前去,惊叫一声,因为他支着一只膝盖撑起自己,仍旧面对士兵,仍旧放声大笑。“又没打中!再—一次,小伙子们—看看—如果你们不能—”他突然摇晃起来,然后就往一侧倒在草上。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人在死亡前夕都会陷入极度的恐怖。达尔文曾举例证实这一点:一个犯人从牢狱走到刑场的路上,满头乌发全都变白。“文革”中几个高中生恶搞,将一个同学绑牢,用衣服包了头放在铁轨上,等火车从另一条轨道上驰过后,这个孩子已经被吓死。80年代我国严打刑事犯罪,被游街的死刑犯处决前吓成了烂泥。小说中的亚瑟面对着枪杀自己的6名刽子手,竟然当起了指挥官,命令他们重新瞄准重新开枪。面对死亡,他不但没有被吓倒,反而和枪手开起了玩笑。这在现实生活中与艺术描绘中,都是极其罕有陌生的事情。
被杀是人生中最恐惧、最紧张、最严肃的时刻,而开玩笑是人生中最马虎、最放松、最愉快的时候,一个被处决的人与刽子手开玩笑,这实际上是将人生中最严肃的时刻换成了最放松的时刻,会因为极端反常罕有引起读者的惊骇、惊异、惊赞。一篇外国小说写刑场上死刑犯看到大家都在等着他的到来,就高兴地喊:你们哪,离了我什么事都办不成。阿Q在刑场上画押,因画圈画不圆就气愤地骂:孙子才画得圆哪!这些人的这些话之所以受到特别注意,也是因为他们在最严肃的场合说了最放松的话。最严肃的人生处境中的行为与最轻松的人生处境中的行为的互换,使“牛虻”刑场就义成为极端罕有陌生新异变化。
牛虻为了民族大义视死如归的坚强英勇是崇高。他与侵略者及其帮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惨遭杀害是悲剧。枪手面对气贯长虹的民族英雄不敢正视、枪法失准,是心理活动规律之真。牛虻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斗争是善,侵略者枪杀正义爱国志士是恶。这部小说1897年在英国首版时默默无闻,半个世纪后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时却能受到特别注意,发行100万册,与刑场就义描写的崇高、悲剧、真、善、恶、滑稽密切相关。
3.崇高—滑稽式艺术
鲁迅先生的小说《铸剑》描写的是宴之敖者替眉间尺报杀父之仇。他把自杀的眉间尺的脑袋丢进烧沸的大鼎中,跳舞唱歌诱骗其杀父仇人大王上前观赏,趁机砍掉大王的脑袋后又砍下自己的脑袋。三个鲜血淋淋的人头在沸水中撕咬打斗起来:
他的头一入水,即刻直奔王头,一口咬住了王的鼻子,几乎要咬下来。王忍不住叫一声“阿唷”,将嘴一张,眉间尺的头就乘机挣脱了,一转脸倒将王的下巴下死劲咬住。他们不但都不放,还用全力上下一撕,撕得……王头眼歪鼻塌,满脸鳞伤。
这篇小说吸引读者无意注意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将恶的形貌极端化。我国古人常以自杀的方式报仇报恩,《史记》的“列传”中就有多处记载。小说中的三个主要人物,脑袋均被砍掉,在烈焰煮沸的大锅内用牙齿继续拼杀。这种景象即使置于野蛮的古代也是一种极恶。形貌极恶有强劲的震撼吸引功能。二是人头离开人体自主独立活动的极端陌生。人的头颅离开身体很快就会断血缺氧死亡,小说中的三个人头离开人体不仅继续存活,而且还能在开水中唱歌跳舞撕咬,显然是与锅中被煮之肉进行了互换,这在现实和艺术中都没有出现过,因而以极端神奇陌生产生震撼吸引。
眉间尺的父亲是铸剑高手,大王令他铸剑,剑成后将其杀掉。但他早有预防,铸成的是两把剑,私留一把让儿子替他报仇。儿子眉间尺虽然胆小,但为了诱骗仇人却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头砍下来交给宴之敖者。为完成眉的重托,宴之敖者也义无反顾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两人诱杀仇敌英勇赴义是崇高。三个人头在水中像鸡斗架啄叨、狗打仗撕咬般,是荒唐可笑的滑稽。三人中两人自杀一人他杀,杀己是手段、杀他是目的,己为正义、他为邪恶,所以杀己为恶、杀他为善。这是作品中的恶与善。人头在沸水中打斗,是想象虚构的假。其可怕可笑的景象是怪诞。
小说的这些构成元素为读者带来丰富的快感体验。
4.崇高—怪诞式艺术
纳兰霍的《蒙面人与靴子》中出现了人头和鞋子的组合。人头被蒙上白色衬衣,已经离开了人体,却还在自主活动。靴子异常破旧,上面搭挂着一条项链,系着耶稣受难十字架,没有人踩穿却自己在拼命扭动。
在马格里特的画作《情人》中,头上包住厚布的男女在接吻。他们头上为何包布,既然包了布,为何隔着厚布徒劳接吻,由于画面对这一切没作任何解释,因而就产生了强烈的神秘色彩。
纳兰霍的这幅画显然受到了马格里特的影响,他画中的布包里是一个没有身体的断头,却活着向前张望、向前冲击。这个断头是什么人的,他为何被人砍掉脑袋,离身之后为何还能飞行?
这一切在画中也得不到任何解释,比马格里特的包布脑袋更加神秘恐怖。凡·高曾画过一双歪歪扭扭、呲牙咧嘴的旧鞋,由于一贯的画风所致,凡·高的鞋子也像他笔下的其他形象一样充满张力和动感,在我们的视觉中莫名其妙地活动着。
纳兰霍的这双靴子则更进了一步,不仅充满了张力和动感,简直就是有人穿着它在活动。
鞋子为何会无缘无故地自己行动,画中也没有给出任何答案,也走向了神秘化的极点。
这件作品效法马格里特与凡·高的神秘化创意,将布包人头与破烂旧鞋自主疯狂的无因神秘发挥到了极致。形貌神秘的极端化,使这个作品成为罕有陌生对象。
这似乎是一个牺牲了的勇士形象,尽管身体已经倒下,但头部还在奋勇向前,速度快得将包在头上的衬衣甩得老远;虽然两脚已经消亡,但鞋子还在奔突,英魂不散、忠烈永存是崇高,恐怖可怕、反常好笑混杂是怪诞。这双鞋子不仅破旧而且是两种款式,此人虽然在向前张望冲击,可脑袋眼睛却包得严严实实,让人觉得怪异幽默是滑稽。画中人的头部以及鞋子,衬衣都描绘得栩栩如生,是真。脑袋离开身体能够飞行,鞋子自己可以走动,这是画家虚构的假。作品的这些构成元素带来的快感体验,使起读者不愿离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