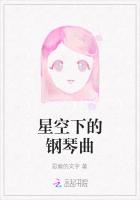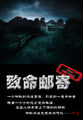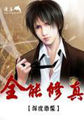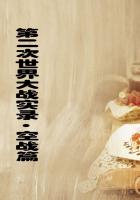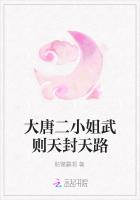在中国人的传统里面,总是有很多的“权威”,而中国人对权威的理论,记得尤其清楚。然而,这些权威的理论,到底是不是对的?这就不是中国人关心的问题了。
这,其实就是中国人的“唯权威论”思维。这种思维方式,是把某些出色的人物所做出的结论当做一种牢不可破的真理,自己不加鉴别地使用,这固然是尊重长者的劳动成果,但同时也抹煞了自己的创新潜能。
著名的哲学家罗素就曾经给中国人上过这样一课:
罗素来到中国讲学,当时来听讲座的,大多数是社会科学方面的教师和学生。罗素登上讲台之后,首先在黑板上写下了“2 2=?”这样一个题目,然后就让来听讲座的人回答,答案是什么。当然,2 2=4是一个常识,可是,席间诸位却不敢如此回答,因为他们觉得,罗素这样的世界顶级哲学家,在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肯定有深意,所以,2 2就必然不会等于4.大家都觉得,罗素要通过这样一个题目,讲述他的哲学主张和理论,所以谁都不敢回答,唯恐答错了。
出现了这样冷场的局面,罗素只好亲自点将,让台下的一位听众回答这个问题。这位先生站起来之后,不知道如何作答,只好支支吾吾,不敢说出一个结论。罗素见到这种情况,会心一笑,说,这题目有什么难的,2 2当然是等于4啊。
这个题目,可以看做是罗素对中国听众的一场考试,虽然题目简单,但是因为出题者的身份特殊,所以没有一位听众敢于作出回答。这恰恰暴露出了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毛病:过分迷信权威,过分崇尚权威,以至于被权威的气焰压迫,失去了自己的思想。而罗素正是以这样戏剧性的方式告诉中国人,不要管你面前的人是不是权威,是不是名人,你只要去看题目本身就好,权威不应该成为阻挡你思维的障碍。
俄国的科学家门捷列夫发明“元素周期表”的经历,正是在权威面前,敢于发表自己见解的例子。在他之前,很多化学家都对元素的周期排列提出了自己的见解。1865年,英国化学家纽兰兹则按原子量递增顺序,将已知元素作了排列。他发现,无论从哪一个元素开始算起,每到第八个元素,就与第一个元素性质相似,亦即元素的排列每逢八就出现周期性。纽兰兹从小受母亲的影响,爱好音乐,觉得这好像音乐上的八个音阶一样重复出现,于是自己把它称为“八音律”,画出了“八音律”表。1866年3月当他在伦敦化学学会发表这一观点时,得到的却是嘲笑和讽刺;他的有关论文也被退稿。
当时,人们嘲笑和讥讽纽兰兹,就是因为他的想法被认为过于荒诞,而且和当时的化学界权威说法完全不同。而门捷列夫并没有因为纽兰兹的遭遇放弃自己的研究,相反,他在纽兰兹“八音律”的基础上,通过更为细致的计算和巧妙的观察,再次朝着化学界的权威发起了冲击。
终于,经过不断的思索和验证,门捷列夫排出了初步的元素周期表,并且宣称,把元素按照原子量的大小排列起来,在物质上会出现明显的周期性,原子量的大小决定着元素的性质,可以根据元素周期律来对已知元素的原子量进行修正,并且对人类未发现的元素性质与原子量进行推测。
假如,门捷列夫看到纽兰兹所受的冷遇,从此放弃自己的研究;假如,门捷列夫在化学界“权威”的结论面前毫不怀疑,不进行自己的观察与研究,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元素周期表,也不会有根据门捷列夫理论发现的新元素。他的成功,是对权威的挑战,也是对“唯权威论”的思维方式的挑战。
“唯权威论”的阴影,笼罩着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如果要有所创新,有个性化的发展,就要抛开对权威的迷信,打破自己与权威之间的心理差距。这是在心理上应该做的第一步工作,也是在思维方式上所要作的第一步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