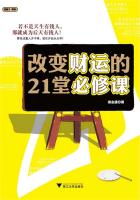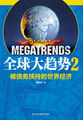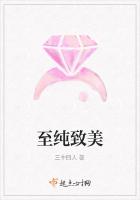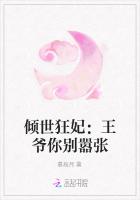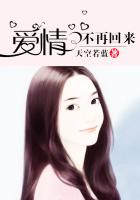通过总供给与总需求来分析说明经济波动,是新古典周期学说的基本思路。刘树成、樊明太的“中国经济波动分析”一文,以总需求─总供给分析框架,对我国“软着陆”之后经济增长率连续下滑的原因做了剖析。
从总需求来说,投资增长率的波动仍然是主导中国经济增长率波动的主要因素。固定资产投资总需求是在一定的金融约束条件下,资本租用成本、预期(或计划)产量、预期收益率等变量的函数。据此分析,近年来投资增长率的持续下滑,主要原因有三:其一,体制变革的冲击,这种冲击改变着投资需求的金融约束条件,因此是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包括计划、财政、金融,特别是投融资等体制的转轨进入深化期的必然结果;其二,结构调整的冲击,产业结构的调整,压缩重复建设项目,淘汰资源高消耗、高污染项目,会通过预期或计划产量的改变,通过投资加速原理的负向传导,而影响投资增长;其三,市场环境变动的冲击,买方市场形成以后,预期收益率下降,低收益率预期反过来也制约着投资的增长。消费需求增长迟缓,也是软着陆后增长迟缓的因素。根据现代消费理论,消费总需求是在流动性约束下即期收入、实际财富、边际消费倾向和预期的函数。所谓流动性约束,是指消费者无法充分借款来维持持久收入水平上的消费。
据此分析,当期的消费需求不足,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收入和财富增长放缓,相应的边际消费倾向减弱;其二,居民关于未来收入不确定以及支出上升的预期增强,居民消费的跨时期配置倾向提高;其三,流动性约束以及抑制消费的规制和政策的限制。外需方面,亚洲金融危机引发了外需下降,而且一些面向国际市场的生产能力转向国内也进一步使内需呈现不足。
从总供给来说,供给方面的总量过剩,是指多年来在粗放增长方式下形成的低水平过剩生产能力、无效供给和结构扭曲。由于存量调整缺乏产权变革条件,市场缺乏淘汰机制,企业缺乏创新和并购能力,这种供给总量过剩以及结构刚性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矫正。供给方面的结构刚性,是指供给结构相对于需求结构的调整缓慢,具有粘性。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1997年应急课题研究中,张立群研究员认为,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是社会总需求的快速扩张与社会总供给的增长间存在较大矛盾,因而经常引起社会总供求的失衡,但这种矛盾的程度是在不断减弱的。改革开放以后需求的决定模式转为以市场为主,少数人主观意志对需求决定的影响消失了。由于供求平衡情况此时可以通过市场价格迅速表现出来,因此政府对供求运动的调控就比较客观和正确了。在改革开放之初,随着放权让利为主的改革进程的加快,经济活力增加,居民收入以及消费和投资需求都在迅速增加,因而引起了社会总需求的迅速扩张,而此时社会供给能力还不能很快地跟进,同时对社会总需求的调控也还缺少经验和手段,因此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虽然较之改革开放前有所减小,但幅度仍然较大。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需求的迅速增长也带动了供给的提高,供求间的差距随时间推移迅速缩小。同时,严重的通货膨胀使社会各界对加强宏观调控的认识统一了,政府对总需求的调控加强了,经验和手段日益趋于完善,因此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开始不断减小了。当然也要看到,当期我国的需求决定机制还缺少内在责任和风险的约束,而需求总量的调控则还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应该说,总量运动仍存在着出现较大波动的可能。
宏观波动与微观波动的相互传递也是导致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先胀后缩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樊纲在枟经济研究枠1996年第3、4期连续发表了“企业间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上)(下)”的文章,文中分析了宏观经济波动可能给企业间债务增长带来的影响。他认为,企业债务一般来说是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信用化程度的提高而增长,在企业预算软约束的特殊体制下,企业债务的规模和比重会更大一些。但企业债务的突发性大幅度增长,主要是宏观经济方面的原因,取决于宏观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状况。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波动,而企业拖欠债务的两次突发性大幅度增长,都发生在经济过热之后的两次“宏观调控”的初期。一次是1988年中期,6月份的企业名义债务同比增长率,一下子从 5 月份的 27%增至38 。8%,然后继续攀升,12月份达到80 。2%。第二次是在1993年7月,中央政府实行宏观调控政策之后,8月份的企业债务名义增长率,一下子从7月的11 。76%猛增至104 。9%,然后继续攀升,12月底达到214 。5%,1994年6月份最高达到241 。8%。紧缩时期企业间债务猛增的基本原因是货币供给量的突然紧缩而企业的经济活动没有相应地减少。货币量减少导致企业支付手段紧缺,大量原先在高涨时期预期可以还上的债务现在因资金紧张而无法偿还,已经上马的项目还想继续进行下去,于是又欠下大量新债。这些企业债务导致企业复苏的迟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