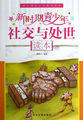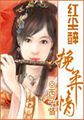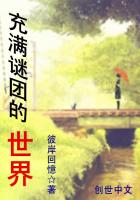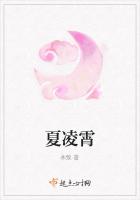关于自1997年以来的通货收缩的定义和治理对策,刘树成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关于通缩主要有以下六种观点:(1)并未出现通货紧缩(于祖尧,1999年);(2)仅出现了通货紧缩的压力,或苗头、迹象(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年;易纲,1999年);(3)出现了轻度通货紧缩(刘国光、刘树成,1998年);(4)出现了严重通货紧缩(谢平、沈炳熙,1999年),并且通货紧缩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大敌”(胡鞍钢,1999年);(5)出现了通货紧缩,但未表示其严重程度(余永定,1999年;李扬,1999年;李晓西,1999年);(6)鉴于对“通货紧缩”一词尚没有规范提法,故改用“经济紧缩”一词来概括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黄达,1999年)。之所以有这些不同的看法,首先是因为对“通货紧缩”一词的理解不同,或者说,各自使用了不同的定义或标准。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定义:一是“三要素”定义。通货紧缩应包括价格水平的持续下降、货币供应量的持续下降与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下降。二是“两要素”定义。通货紧缩包括价格水平的持续下降和货币供应量的持续下降。三是“单要素”定义。通货紧缩就是指价格水平普遍而持续的下降,特点在于:其一,它是轻度的;其二,它具有一定的矫正性;其三,与它伴随的不是经济衰退或萧条,而是较快的经济增长;其四,它是在我国经济转轨中市场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情况下出现的;其五,它也受到国际价格水平的影响。
关于治理通缩的对策,刘树成认为,1998年推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已发展为一整套综合性的政策措施。它包括:(1)既要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又要加强技术改造投资;(2)既要增加中央政府投资,更要推动社会与民间投资;(3)既要扩大投资需求,又要鼓励消费需求;(4)既要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现期收入,更要稳定居民的收支预期;(5)既要坚持立足内需为主,又要千方百计开拓国际市场,积极扩大外需;(6)既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又要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采取多种方式适当扩大货币供应;(7)既要解决需求不足问题,又要解决供给刚性和结构问题。刘树成进一步指出,单靠宏观政策的调控是不够的,还要加强体制创新,继续推进财政、金融、流通、科技、教育、住房、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等各项改革。
张国忠于2003年12月提出要解决需求不足问题,关键是要解决收入分配和不确定性问题,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治本的方法。具体地说,在中国,需要:(1)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强人们的经济安全感;(2)健全法律体系,明确产权、交易和竞争规则,严格执法,加大经济生活的透明度,减少不确定性;(3)在经济活动中,坚决反对垄断、行政腐败和暗箱操作,努力实现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以充分发挥各经济活动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创新来启动和发展经济;(4)健全风险投资机制,建立投资保险制度;(5)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从多方面、多角度扶助弱势群体,解决其学习、就业和生活上的困难,增强其挣得收入的能力,并使这些措施长期化、制度化;(6)运用财政税收手段改善收入分配,使之既无损于效率又不至于妨碍社会消费的增长;(7)完善市场体系,活化市场主体,强化市场对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简单地说,就是改善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健全游戏规则,扶助弱势群体,增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改善其预期,为消费和投资的增加提供一个制度和心理基础,或如刘福垣先生所说,政府要做的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当然也有治标的方法,那就是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辅之以稳健的货币政策。这可以在较短的时期内见效,但不宜长期使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要“适可而止”。
在流动性滞存、总需求不足作为基本状态的情况下,张国忠认为政府最好采用治本的方法,辅之以治标的方法。在治本的方法上要多用心,在治标的方法上,要“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为对抗通货紧缩,扩张总需求,政府实施以增加投资为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并以稳健的货币政策相配合。现在看来,这一政策实施的时间有些过长,规模、范围有些过大。这似乎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周期状态:通货紧缩—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产能过剩—需求不足—通货紧缩。改变这种状况的办法有:第一,采用前述治本的方法,从根本上增加消费和民间投资,实现总需求以自然的方式增长,以消费为动力,实现总需求的合理内部结构。第二,为增加总需求而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一要适度,二要依据消费规模和生产规模的实际情况,按使二者相互协调的原则,合理确定消费和投资的增加比例。财政政策既可以扩张投资,又可以扩张消费,不要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仅与投资等同起来。
著者2000 年撰文认为治理“滞缩型”萧条需要中期政策配合。国家1997年以来采取的宏观刺激政策包括降低利率、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扩大政府投资、增加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增发国债等等,这些主要都是扩张总需求的政策,这些政策又主要是短期调节。刺激总需求,对于遏制一般经济衰退和启动投资是有效的。但是,对于今天这种“滞缩型”经济衰退和萧条就显得仅为治标之举,力度有限。当年西方国家为了治理“滞胀”的局面,西方经济学界就提出过各种对策,其中包括单纯的货币主义理论、供应学派理论以及合理预期学派的理论。应当说,西方经济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走出长期“滞胀”的盘局,应当归功于各种学派理论的综合运用。为此,我们应当明确以下几点:
首先,鉴于“滞缩型”衰退的原因既有总量失衡的因素,也有结构性因素,还存在着体制矛盾,并且,“滞缩型”衰退并非一时形成,而是多年经济矛盾积累的产物,因此,此次“滞缩型”萧条不可能很快复苏,治理这种萧条也不可能很快见效,起码需要2~3年的中期调整。
其次,治理“滞缩型”特种萧条,刺激总需求应当和供给政策和结构调整相结合。因为总量过剩只是经济疲软的直接原因,总量过剩的背后是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的不协调。现阶段的需求结构发生了较大改变。就投资需求结构来说,在生产过剩和有限投资渠道的压迫下,回报率较高的投资项目不多,周期短、投资回报率高的一般家电业、餐饮业、娱乐业进入过度,而高新技术产业投资风险较大、投资周期较长,投资规模不够。国家现有的手段如增加政府基础设施投资、通过降低利率推动民间资金向实业投资和向证券市场投资,固然有一定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加快新技术、新项目的开发投产,因为只有这些新项目才可能更多地享有市场或创造市场。
第三,从根本上摆脱“滞缩型”萧条,还需要适应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要求,通过中长期产业政策,将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的均衡推上一个新的台阶。总量失衡乃至背后的结构性矛盾归根到底产生于现阶段我国经济成长阶段的经济创造能力。经济创造能力包括技术创新能力、生产能力、财富创造能力。目前,制约我国经济结构升级的因素有:一是创新主体———企业的创新能量不足,尤其中试阶段投入不足,仅为新技术孵化阶段投入的0.7倍(通常应当为10倍);二是由于人口众多,人均国民收入较低(1998年仅为868美元),使得居民对于新兴产业购买力不足,也使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不快,综合劳动生产率上不去,拖了产业高级化的后腿。现在高级化的产业政策应当考虑:(1)加快技术入股、转制民营等改制措施,探索将融资、技术创新、市场开发、项目管理融为一体的新型企业技术创新模式,加快企业群体的创新力度;(2)通过加快装备工业的进口替代,促使装备工业首先现代化;(3)通过BOT等项目融资方式,加快引进国外先进和适用技术;(4)加快教育产业化进程,推动科研院所改组改制,在基础研究国家保障的前提下,加快科研机构研制项目的商品化和产业化;(5)通过调整产业组织政策,推动风险投资基金加快扶植科技型中小企业,同时注重发挥大型企业的技术开发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