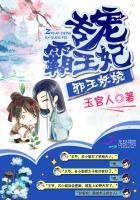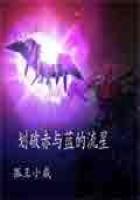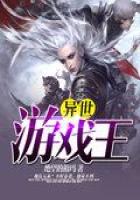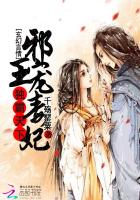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所撰写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一文,提出应当从发展和改革的角度理解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其中,应该遵循两个原则:一是政策选择的体制一致性原则;二是政策选择的发展一致性原则。
所谓政策选择的体制一致性原则,是指宏观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出台应当与体制伸缩相配合。在市场化过程中,政策效应的发挥往往离不开体制上的相应变革。如果说在宏观紧缩时,体制上某些方面的暂时退缩有利于政策效应的实现,只要不是根本性和持久性倒退即可,1993年整顿金融秩序就是如此,那么,在宏观扩张时,体制上的推进就成为政策效应实现的保证,1992年就是最好的例证,这时体制上的收缩就是致命性的,不仅会使政策的扩张效应无法实现,而且有可能破坏体制一致性原则。1998年发行国债目的在于实施扩张,但是如果简单地定位于启动经济,那么,其效应必然受到限制,也很难长期支撑,弄得不好,很容易陷入债务危机;如果在实施扩张的同时,着眼于赢得时间和空间,使资本市场得以发育成长,那么,其结果就不仅是当前的经济增长,而且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制度支持和资金保证。再比如,鉴于当时阻碍经济复苏的关键在于预期看淡,而预期不稳又与大批职工下岗待业、收入预期降低,社会保障和医疗制度改革、支出预期增大有关。当时,1998年发行国债6850亿元,1999年计划增发3165亿元,如果把发行国债筹集的资金除增加投资外,拿出一部分用于解决社会保障问题,或者再增发一部分社会保障特别国债,就可通过稳定预期,启动消费,进而带动民间投资。这样既可活跃经济,又可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宏观政策选择应当坚持发展一致性原则。宏观政策主要是一种短期政策,但对长期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在经济发达国家,由于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任务已经完成,经济结构的同质基础已经奠定,因而,宏观政策短期作用和长期影响的一致性也就易于实现。而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二元经济结构的基础还很强大,城市化的进程又大大滞后,宏观政策不仅不能仅仅着眼于短期效应,而且要考虑长期发展,至少不能为长期发展设置新的障碍,同时要从二元经济结构的实际出发,坚持发展一致性的原则,大力推进城市化的进程,这就增加了政策操作的难度。
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必须解决体制效率问题。在政策主张上,樊纲教授是力主实施宏观政策尤其是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总需求的学者。而茅于轼先生对宏观调控中的扩张性政策持保留态度。茅于轼认为,扩张性经济政策是对付经济周期波动的良策。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率在不同年份里有高有低,低谷时就用扩张性经济政策,通过增大政府开支刺激消费需求增长,从而带动经济复苏。像凯恩斯当年建议美国政府那样,甚至可以由政府出钱“雇人挖沟再雇人填沟”。可是中国的问题不是经济增长率有高有低波动,而是连续7年一路下滑,这说明中国在制度上有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政府不再是投资主体。
樊纲倡导财政政策,也是认为在没有其他政策比扩张性财政政策更好情况下的一种“次优”(Second Best)选择;而茅于轼更强调财政投资效率低下的弊端。办法就是通过资本市场,通过企业家的投资行为,他一直坚持认为“储蓄比消费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茅于轼认为通货紧缩本身不是病。物价水平降低,通货紧缩,已经成为我国宏观经济中最被大家关注的问题。有人称它为我国经济的第一号问题,但茅于轼认为,通货紧缩本身不是毛病,它只是宏观上总供给超过总需求所造成的结果,病根子在宏观上供需的不均衡。如果宏观的供求形势未变而通货开始膨胀,这不但不是好消息,可能还是社会经济效率降低造成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连续三十年因劳动生产率提高而物价水平降低的事例,此事发生在19世纪的美国和欧洲,这种通货紧缩并没有对经济产生坏作用。反过来也一样,温和的通货膨胀如果伴随着经济增长,这种膨胀也不产生坏作用,至少正作用和负作用抵消后没有明显的危害,所以只看通货紧缩或膨胀,并不能说明经济形势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