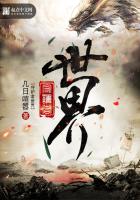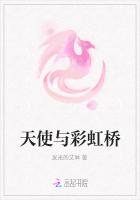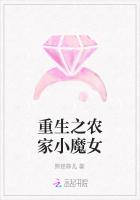2003年第3期枟经济研究枠刊登了刘树成的“中国经济波动的新轨迹”一文,其中明确提出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超前把握、因势利导、实现波幅小又较快增长的思想。文章对1998~2002年中国经济运行所出现的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既稳定又较快增长的新轨迹进行了考察,提出欲在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中走出一条在8%~10%的区间内平稳运行的新轨迹,积极的方略就是在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上,增强预见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在此之前,刘树成还于2002年底~2003年初撰写一篇题为枟中国经济增长的新轨迹及其未来趋势枠的文章,提出要“努力延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以此设想为标志,我国经济周期研究的重心开始逐步转向能动地、积极地寻求利用经济周期的发展轨迹,将经济周期研究与经济增长研究相结合,以平滑波动换取持续高速增长。
根据国外学者的分析,一些能够保持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的国家,大都出现了产出波动性显著降低的现象,由此可以推断经济周期稳定性的增加是导致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条件。2003年第10期枟经济研究枠刊载了吉林大学的刘金全和张鹤的关于“经济增长风险的冲击传导和经济周期波动的‘溢出效应’”的文章。文章利用经济增长率的绝对离差、条件标准差和风险增长水平等三种方法度量了经济增长风险和条件波动性。检验结果表明,经济风险性和波动性与经济增长水平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由此可以推断经济周期波动性对于经济增长水平存在“溢出效应”。2005年第3期枟经济研究枠刊载了刘金全、刘志钢等人的关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中实际产出波动性的动态模式与成因分析”的文章。其中通过固定时窗长度滚动标准差度量的产出波动性,发现我国产出波动性呈现明显的“凸型”波动模式。这种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相互推动态势能够使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和稳定增长趋势,这对我国力争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文章作者提出应该继续以需求管理政策(具有积极色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来刺激总需求,以供给管理政策(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产品成本)改善供给,这样可以充分发挥价格波动性和产出波动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溢出”作用,继续保持我国快速稳定增长的经济发展格局。
延长经济周期的上升段,取决于防止大起大落。自2002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一轮经济周期到2003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再次出现“前峰型”的高位增长。第一季度增长率上升到9.9%左右。刘金全认为,从1999年以来的第4次经济周期上升阶段,呈现出一种“软着陆”后的“软扩张”态势。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名义增长率26 。7%,实际增长24 。5%,已经接近1992年的水平。但是全社会总体价格水平却远远低于1992年。2003年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2.3%,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2.2%,居民消费价格上升1 。2%。2004年1月也不过3 。2%。
国内经济学界再次出现是否过热的争论。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经济运行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2002年党的十六大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既然是市场经济就不存在过热的问题。对此,刘树成在枟经济研究枠2004年第3期发表了题为“新一轮经济周期的背景特点”的文章,文中指出无论是计划体制还是市场体制,经济周期波动的机理都是相同的,扩张冲动是普遍存在的。只不过,在市场经济下,市场主体———企业由于追求利润的内在动力和市场激烈竞争的外在压力而产生扩张冲动;而另一方面,我们的政府职能转变还正在进行之中,地方政府的扩张冲动仍很强烈。如有的地方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城市建设规模过大、标准过高,乱批乱建开发区等。无论是市场经济下企业的扩张冲动,还是计划经济下中央政府的扩张冲动,或是我国现行体制下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扩张冲动,都会导致经济过热。刘树成认为,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看,根据经验数据,潜在经济增长率约为9%左右,适度经济增长区间为8%-10%。当经济增长达到潜在经济增长率时,就会出现局部过热;当经济增长超过10%时,就会出现总体过热。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为9 。1%,正好达到潜在经济增长率,这是一个重要关口。这意味着,如果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得当,适时适度,就可以延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使经济增长的良好态势保持下去。
如何有预见性地防止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也是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方面。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的樊纲在枟经济研究枠2003年第7期发表了一篇题为“通货紧缩、有效降价与经济波动”的文章。樊纲认为,2001年到2002年的中国物价水平的下降,不同于1997年以来的物价下降,因而不是典型意义上的通货紧缩,而是由效率提高、成本下降所引起的价格总水平的下降,可以称之为“效率改进型物价下降”,简称为“有效降价”(Efficiency Price唱falling)。然而,这种“微观效率”的改进,却会引起宏观经济的新问题,那就是,供给增长速度快于需求增长速度的情况,会产生以生产能力过剩和供大于求为主要特点的周期性经济波动。这种波动,其特点也将是由生产能力过剩为起点、以通货紧缩为起点,而政府采取扩张性的宏观政策来弥补总需求的不足,把经济拉出低谷,实现经济的正常增长。这将是未来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形态。
为了实现小幅波动、较快增长,学者们各有侧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李建伟主张短期内政府可以因应现实需要适度扩大财政支出,应对2003年的“SARS”对短期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但从中长期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应以中性调控政策为主,防止扩张性政策的滞后作用引发未来经济过热。樊纲认为,宏观政策的基本作用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拾遗补缺”、“多退少补”———当民间投资少的时候,政府就多投一点;当民间投资多的时候,政府就少投一点,以保持总供求之间的平衡。政策的相机抉择,同时意味着:某一种宏观政策可以“淡出”,但宏观政策本身应该永远存在,随时准备采用。
简短地说,经济学世界中实际理论是一个描述或模拟在某种经济政策下行得通的任何经济社会的理论。所以被动描述我们目前看到的周围的东西是不够的。根据人的福利的观点,经济计量学的任务是设法从过去的数据提取有用的信息,是为了到达被发现的任何好的经济社会。
198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挪威]奥斯陆大学教授:特里夫·哈维莫
经济周期的数量分析是经济周期研究的必备方法和科学方法,国外使用经济数学方法分析经济景气已经比较成熟。到目前为止,国内使用的数量经济学方法大多属于引进和运用。国内学者运用经济周期的数量分析方法,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常采取的方法包括线性回归分析、线性规划、均衡分析、扰动因素分析等。这些分析方法的采用标志着中国经济周期的研究走向科学化。
纵观国内运用经济数量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周期,比较早和比较成熟的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所、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所等单位。包括乌家培、刘树成、张守一、董文泉、高铁梅等在内的学者们,长期从事数量经济和经济周期预测系统的研制工作,对应用数量经济方法分析中国经济周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88年两次全国经济周期研讨会的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所和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所就是重要的发起单位和参加单位。
数量经济学方法在经济周期中的应用,不仅有助于经济周期研究的深化,也使得周期研究显得更具美感。总体上讲,经济数量方法的应用,一是推动了周期研究精细化、精确化,使人们对周期波动的把握从经验上升为科学;二是作为经济数量研究的重要领域,经济周期研究成为引进和应用经济数学和计量模型的重要平台,大大推动了我国经济数量方法的应用和发展;三是帮助决策部门更为准确地预测和应对经济周期,以便有效地制定和采取平滑周期波动的宏观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