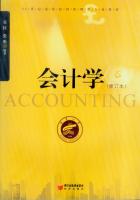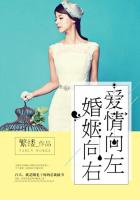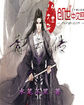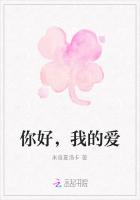2003年5月30日,我国有学者撰文讨论了经济周期以人名命名的问题。据该文章讲,报刊上登载的许多研究经济周期的文章,在介绍西方国家为“发现”平均经济周期长度的专家命名时,不仅没有说是谁进行的命名,而且对为什么命名也众说纷纭。
1939年,约瑟夫·A·熊彼特在美国纽约出版了他撰写的第二本知名著作枟经济周期枠,书中对3位专家进行了“命名”。因为这3位专家各自收集了几个国家一定年代的统计资料,并按自己的计算标准,计算出了也称为“发现了”这些国家一定时期内的平均经济周期长度。这3个专家及其命名是:
(1)基钦周期。英国专家基钦在1923年发表的枟经济因素中的周期与趋势枠一书中,分析了1890年至1922年间英、美两国的物价、银行结算和利率等统计资料,计算出这两个国家在这一段时期内存在着大周期和小周期,一个大周期包括2至3个小周期,一个小周期平均为3.5年。这个小周期被熊彼特“命名”为基钦周期,并指出是一种短周期。
(2)朱格拉周期。法国专家朱格拉原为医生,后改为研究经济周期。他在1860年发表的枟论德、英、美三国经济危机及其发展周期枠一书中,根据他搜集的统计资料,计算出平均9至11年发生一次经济周期。这个周期被熊彼特“命名”为朱格拉周期,并指出是一种中周期。后来英国专家汉森用朱格拉的计算方法,使用英国1795年至1937年的统计资料,计算出了平均周期长度为8 。35年,从而把朱格拉周期修正为8至11年。
(3)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俄国专家康德拉季耶夫在1925年发表的枟经济生活中的长波周期枠中,对1789年以来英、美、法、德等国的各种统计数据,包括批发价格水平、利率、工资、外贸以及煤炭、生铁等的产量进行分析,认为存在着50年长波周期循环。这个周期被熊彼特“命名”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并指出是一种长周期。
这里要指出的是,熊彼特在书中第一次提出了短、中、长周期的概念,但没有加以具体的量化。后来有的专家按他的概念加以具体的量化,提出经济周期的短周期为3至7年,中周期为8至25年,长周期为26至50年的划分意见。
熊彼特在书中没有提到另一位曾经计算过平均周期长度的专家,就是美国专家库兹涅茨。库兹涅茨在1930年发表的枟生产和价格的长期变动枠中,分析了英、美、德、法、比等国1866年至1925年53种商品的统计资料,计算出了15至25年不等的周期波动数据。库兹涅茨在分析时,使用了大量美国建筑业的统计资料,并认为在美国建筑业中15至25年的周期波动表现得特别明显。除建筑业的资料外,库兹涅茨还分析了人口、资本形成、居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等资料。后来有的作者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指出,库兹涅茨计算平均周期长度的方法,与另外三个被熊彼特命名专家的计算是同水平的,因而,应补充“命名”为库兹涅茨周期。由于库兹涅茨的计算使用了大量建筑业的统计资料,还应命名为建筑业周期。
同时,有的专家以库兹涅茨周期为据,主张将熊彼特提出的短、中、长三种周期,发展成为短、中、中长、长四种周期,其中的中周期为8至14年,中长周期为15至25年。这里要说明的是,熊彼特对经济周期的短、中、长划分及其后增加的四种周期划分,并不能准确地说明不同长度周期存在着质的区别,人们在分析有关问题时无法参用它,故未得到广泛承认和应用。
国内有学者对四个以专家命名周期的基本评价:
一是以上四个专家命名,有三个是熊彼特个人行为的命名,有一个是报刊作者的命名。均不是由具有权威性组织作出的命名,因而缺乏权威性;
二是以上四位专家,仅是依据自己选择的一定时期的统计资料计算出了平均周期长度,属于一种统计分析数据,既不是“主张”,更不是“立论”。
三是由于四位专家的计算,依据的是不同的划分标准,口径不统一,使得各自计算出的周期长度缺乏规范性和科学性。如果统一采用后来取得人们共识的经济周期四阶段的标准来计算,可能这四个专家计算出的平均周期长度都要作修改。特别是经济周期四阶段中包括了危机阶段,由于经济危机造成国民经济的“重创”,必然会出现较长的萧条期和恢复期。例如,1927年至1929年发生的波及全世界的经济危机,危害十分严重,直至1940年“二战”爆发时,美国还没有走出恢复期。如果计算经济危机的影响,当时就不大可能出现3年短周期,基钦周期就不能成立。
该学者指出,为什么“二战”后不再进行专家命名?世界上坚持对发现者命名的是天文学界。众所周知,发现新星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全世界广大的天文工作者和天文爱好者,每天都在监视和观察星空,但发现新星的人却凤毛麟角。因而这种为发现新星者的命名既是鼓励和推动,又是一种崇高的荣誉。有些研究经济周期的人曾据此发表议论,认为研究经济周期如果有组织牵头,这种为发现平均周期长度的命名活动就有可能继续下去。
其实,有没有组织并不是决定性原因。问题关键在于,这种平均经济周期长度,仅仅是用一定时期的统计资料平均计算出来的,是一项比较简单的统计分析工作,而不是重大的发现。有人说,在“二战”以前靠专家们“单打独斗”地去搜集统计资料,是比较费劲的。这种说法虽然有点“理由”,但因为比较费劲就给以崇高荣誉的命名,理由也不充分。“二战”以后,各国和各城市都建立了强有力的统计机构,信息工作水平也大大提高了。如果需要某国某一时间段的平均经济周期长度数据,统计机构就能很快地为你提供,或者由你“上网”就可以查到需要的数据。何况许多国家规定,只有由统计机构发布的统计数字才具有权威性,所以,在“二战”以后,再为某人计算出了某几个国家一段时期的平均经济周期长度命名,就毫无道理了。这就是西方国家对计算出了平均周期长度的专家“命名”,只在“二战”前出现过四个不具权威性和不具规范性的,而其后就不再进行的原因。
作者指出,以专家命名周期可能造成误传误导。作者与西方国家专家探讨时,曾提出过西方国家是否还另有为持单一周期长度论的专家命名。得到的答复是,仅有“二战”前由熊彼特及舆论界提出的四个命名,是因为这4个专家计算出了某些国家一定时间的平均周期长度,而不是他们持单一周期论。如果现在有个单位委托某经济学家对今后10年某国或某城市的经济周期进行预测,他会预测出一个单一的周期长度,但仅仅是短期预测。如果要请某专家“立论”,因为“立论”应该达到覆盖广阔时间和空间的要求,面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存在着多元化周期长度的实际,这个专家只会持多元化周期长度论。如果有人一定要为单一周期长度“立论”,肯定经不起广阔时间和空间的实践考验,只能成为机械论或形而上学论。
我国舆论界在介绍国外为“发现”周期长度专家命名情况时,不仅没有说清来龙去脉,反而加以“渲染”和想当然的推论。有些文章把“发现”的平均周期长度说成是某某专家的“主张”,有的文章则进一步说成是“立论”。这就使人误认为西方国家一直在进行为单一周期长度“发现者”或“立论者”命名的活动。还有的人据此进一步发挥,认为既然西方国家能命名一批单一周期长度论者,我国也应推出一批单一周期长度论者,这样才能与“国际接轨”。这些不准确的误传,在我国产生了明显的“误导”作用。例如有的专家按自己的计算标准,计算出建国以来平均5年左右发生一次周期,然后对今后20年进行预测;有的专家认为今后20年不会有太多变化,预测会围绕5年作正负1年的波动;有的专家认为我国宏观调控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周期长度将有3年左右的增加。这种统计分析和短期预测,也符合我国经济周期研究工作处于初期阶段水平不高的实际,但经过舆论界的“渲染”,却变成了根据西方国家的“理论”,某某专家持5±1周期长度论,某某专家持5 3周期长度论。舆论界根据误传的“理论”,硬把几个专家的预测“拔高”到“立论”的高度,让它去接受广阔空间和时间的检验,必然会在实践中碰壁。更令人忧虑的是,很有可能把我国方兴未艾的经济周期研究工作,引上浮夸和形而上学的歧途。
实际上不准确的误传,基本上不是西方专家原有的提法,而是我们一些学者在收集或翻译外国资料不全不准的情况下,通过拍脑袋和随意渲染而“蒙”出来的。为此,著者建议研究经济周期的同仁们,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兴调查研究和务实之风,让经济周期研究工作扎扎实实地迈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