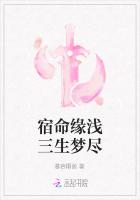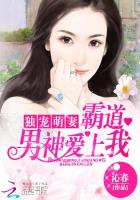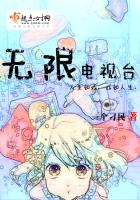读书与写作
张宗刚(以下简称“张”):你的读书观是什么?
苏童(以下简称“苏”):为功利而读书。要读你需要读的书,其他与自己创作无关的书没工夫看。书读多了难免入乎其内不能自拔,这是一种悲剧。
张:谁的书给你印象较深?
苏:英国人伯林。他对自由的理解有两种,一种是我们说的传统意义上的自由,另外一种是可以放弃什么、拒绝什么、排斥什么、逃避什么的自由。这种更适合我。伯林划分出了积极自由、消极自由、勇敢自由、主动自由等,他的自由包括这么多意思。伯林还对知识分子作出了“刺猬型”与“狐狸型”的划分,我应该属于后者。对于世界,对于生活,我常常持逃避、拒绝和放弃态度,不喜欢主动出击。对于我,世界永远是个庞然大物,只能局部地感知,不能理性地条分缕析。
张:你读金庸吗?
苏:我不读金庸,我知道读金庸会入迷。再说我与金庸走的不是同一条路子。我第一喜欢的类型,是短篇小说。除此之外,也了解一些我应该了解的东西。中国是个出版大国,现在的出版物太多,时间有限,应当合理分配。我身边几乎所有的人都读金庸,叶兆言也在读,但我不。我是个比较功利的人,与自己创作无关的书不读,大家都认为好看好读的书不读,真正对我的创作状态有所帮助的才去读。我充电的方式主要是靠阅读经典。我的书架上找不到黑格尔康德叔本华萨特,我从不读太过艰深的书。
张:剑走偏锋,剑走空灵。你的读书观,正符合你的创作路数。创作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事。金庸说过他之所以能成为作家,主要靠的是一种天赋的结构小说的能力。
苏:尽管我很少看武侠,却赞同他的观点。创作确是这么一回事,只能意会不可言传。正如鲁迅讲过的,你不说我还明白,你一说我倒糊涂了。人的心灵是一个黑洞,一片源源不断的强力磁场。某种意义上,创作是一种完全源自心海发自性灵的东西,一切的言语表达都是一种渐近线,无限接近,却也永远无法到达本体。就像小孩子练琴,有的孩子,让父母掐死了练,都练不好;有的一坐下,如同见到亲人,得心应手。后一种琴童他面对钢琴,像摸到一个开关,一下就打开了;前一种琴童他练一辈子,刻苦了,努力了,却总是摸不到开关。作家也是如此。所谓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并非耳提面命可以做到。一个作家的才情即性情。性情是好作家的标志。比如经常受到误解的贾平凹,就是一个有性情的人。他忠实于他的性情。
张:你觉得一个作家的学历,或者说受教育的程度与他的创作状况成正比吗?
苏:学历对作家来说无关紧要,有时也许是一种损害。
张:你怎样看待人性?
苏:关于人性,抱悲观的态度看它,比抱乐观的态度看它更科学一点。
张:你的作品里,非常态的、丑恶的东西表现得比较多。
苏:我从不觉得小说家有这么一个任务:告诉别人世界是美好的。小说家能够做的,是聚焦你生活范围中所有的东西,尤其是那些对你冲击最强烈、记忆最深刻的世界的某个角落的某一种人;你要叙述这些人,以便造成强烈的冲击力。这当然跟美学评判和道德评判有直接关系,但不要坏的、好的搅在一起,搞一些审美平衡。我不希望出现这种平衡。大家都见到过、写到过、想到结局的,我去写干什么?要写就写和别人不一样的。我喜欢关注别人不关注的东西,冷门的东西,有空白点的东西。不喜欢表现所谓美德、气节、贞操等,我笔下的一些东西,跟传统是有距离的。对此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正常。我的笔下常常是精神残缺的世界,精神残缺的人;关注他们对于我来说产生意义。罗伯·格里耶说,作家不是一个现实的人,也不是一个虚构的人。我笔下所写,大都是超验的东西。许多作家的作品,带有很强的自传成分,但我的不是。
张:现实人格与艺术人格、世俗人格与文化人格往往相映成趣。如你,在现实世界里羞涩内向,腼腆胆小,在艺术王国里却排空驭气,骋神驰思。你笔下写的,分明是一个非现实的、心理的、意象的、感觉的时空。但不少读者为文本所迷,对你本人存有误解。他们不知道生活中真实的你,耽于幻想而天性本分,从不张牙舞爪,更不蜂狂蝶浪。
苏:小说跟心灵有关系,而跟作家的日常生活形态毫无关系。托尔斯泰一生无趣无味至极,很多人却认为他丰富多彩。这种错觉,是将艺术与现实混为一谈导致的。托尔斯泰一生有悖于常人的唯一一次出格行为表现于晚年的出走,在一个小车站几乎冻僵。但就是这样一个单调得好玩的人,心灵却至为丰富。从他身上考察,作家与作品本身是悬而未决的关系。比如托翁一生生活在庄园里,锦衣玉食,有女仆伺候,几乎足不出户,但他对身外的世界予以极大关注:战争、和平、社会变革、政治体制等,以包罗万象的热情投入,并有自己的形象阐述,其作品被公推为“十九世纪的社会发展史”。总之,他的一生,基本上是呆在庄园里。他的创作,按世俗的说法,整个儿是在闭门造车。还有福克纳,美国小镇上一个脏不拉几的小老头,一个孤独自闭的乡巴佬,终生都没有离开他那片“邮票般大小”的地方,但却写出了最为神圣的东西。
我一直不太相信今人所参与的种种社会生活:工厂、部队、农村等,这样的生活,是否可以直接提供东西?从这样的生活获得的一些东西的数量,跟写作能否成正比?归根结底,心灵的过滤是最重要的,要有心灵的存在。心灵,这个词汇听上去很玄,实则不然。心灵不是一个可以看透的东西,心灵是人类的内宇宙,有着取之不尽的巨大能量,这种能量甚至连作家本人也不能充分发掘。我们无法估计心灵的长度、宽度,探测心灵的深度、厚度。
张:你描摹女性公推为文坛一绝,为什么会写得这么好?
苏:我写女性是比较擅长。为什么男性写女性反而写得比较好?想当然罢了。在创作的过程中,如不调换位置,仍站在男性角度上设想女性的语言反应,放不下架子,这样写出来的女性形象一般是失败的。同理,如果照这个样子站在女性角度写男性,也免不了要失败。我在创作中写女性时,常设身处地,站在女性角度运思,不断琢磨揣测,就像置身戏台,男扮女装反串演一回戏,演完便卸妆,轻松潇洒。这样创造出来的人物,能够得到大家认可。
张:能谈谈你对诺贝尔奖的看法吗?
苏:鼓吹诺贝尔文学奖是比较可笑的,因为诺贝尔奖操持在瑞典人手里,是瑞典式、西方式的。西方话语霸权的存在毋庸置疑。那些评委,他们看日本文学还好,因为体制相近;看中国文学,首先定义在中国是非主流的,视社会主义为异类。所以中国作家最好不要谈这个话题,往往在我们这里是鲜花,到了他们那儿就是粪土了。像中国人津津乐道的《小兵张嘎》,西方人就认为非常残忍:一个孩子,怎么可以加入到战争游戏中去?但这却是我们津津乐道的儿童团呀。
张:你如何看待新生代作家的创作?
苏:新生代有他们的锐气和特色。新生代的弊端在于每个人都很相近,看一个就等于把所有人都看了。
批评的缺席
张:作为一名活跃的作家,你对当今的文学批评怎么看?
苏:总的说来不满意。现在都感慨大陆文学批评是缺席的,不是在场的,我看这话很到位。所谓批评的缺席,是指缺乏这么一个群体,一种状态,本质上指的是一种精神匮乏,一种主体性灵的缺席。
张:近年美籍评论家王德威携带一组有关当代汉语作家——包括你、叶兆言、余华、莫言在内的作品研究的文本在《读书》杂志闪亮登场后,光芒四射,令大陆评论界惊呼“他是谁”,可算一景。
苏:大陆不少搞评论的,总喜欢先入为主,拿作品文本来套他的观念。王德威是性灵派,他的评论我读过,很合胃口。王德威下笔精彩绝艳,气象伟丽,时有过人之论。他那些纵横飞动的文字,与我们读惯了的笔法不同。
张:从当代文学评论的斜阳旧影里,走出这样一匹神骏的赤兔马,确实令人击节。
苏:他的评论跟文本贴得比较近,外师造化,内师心灵,行文活色生香,既保持了汉语的纯洁性,又与西方文化背景相通。王德威搞的是一种追踪研究,他对作品本体的关注,做出的就是一种在场的反映。他们搞研究的路数,是先读作品,感受作家气味,然后再说事,没有一个固定目标;不急于像我们那样从社会学层面切入,先发现社会学意义,表现为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再找一种急功近利的解读方式。应该说,国外的汉学研究是有中文背景的,他们看你的作品比国内人看得要多,不受国内文坛一些喧嚣浮躁的东西影响,能够取一种比较纯净和相对独立的视角。
张:如今国内一些文学评论,常被讥为“半死不活”,圈内人看了发笑,圈外人看了发蒙。
苏:评论完全应该是自发的。首先评论者要被打动,自己发现了一些东西才好。但现在评论却必须被组织了,这就不正常了。远离大众的自闭式评论正越来越多。现在报刊充斥的多是组织过的评论,我就懒得看。其实我对评论并非不屑一顾,凡写到我的评论,我都会认真仔细地看,有的好,有的坏,有的认同,有的不认同,但多多少少总会对我有益。
张:当前文学评论界的不景气与污浊,已成公认。现在搞评论,在高校好多是为了评职称,当导师,拿学位;在高校之外,则往往是为了拉关系,搞帮派,图一点现实的好处。
苏:评论成了地道的为稻粱谋。当然,图一点实利,也可以理解。但评论不能成为鬼火,把人引向坟场导入混沌。
张:文学评论,从20世纪80年代的举足轻重到今天的无人喝彩无人理睬,出现了巨大落差。造成落差的原因很多,如商潮的汹涌,人心的浮躁,传媒的勃兴等,更多的是评论自身品格的失落。如果说现在的文学没劲,文学批评更加没劲,成了影子的影子,附庸的附庸。
苏:许多评论者喜欢玩弄一套别人不懂自己也未必真懂的批评话语,满足于痴人说梦的把戏,结果是言者昏昏,听者沉沉。
张:评论前辈李健吾们那种恢弘细腻富于才情的美文式印象式批评,已难得看到了。应该说,王德威的评论有意无意师承了李健吾的风格套路,感悟与理性交织,写来神采奕奕,青出于蓝。
苏:不少评论家往往不读作品而空发议论,贩卖自个肚子里早已内存好了的那点不变的货色。反倒是无名的学生,读作品读得很多,但缺陷在于没有能力对作品理出一个脉络,作出理想的反应、过滤和梳理,从而上升到一种高度。有能力的恰恰相反。这就是尴尬的批评和批评的尴尬。久而久之,文学批评成了二流以下的东西。
张:评论家要是完全看脸色和红包行事,就真成了“食腐肉者”。朱文们那份不无偏激的《断裂》问卷调查显示,当代文学批评因为对创作无补早已乏人关注,失去了基本的指导意义。这是可以说明问题的。
苏:其实许多评论者的功底修养可圈可点,只是用歪了地方。北大一位学者说他从不研究活着的作家,耐人寻味。文学评论不应受到与作者关系的限制。从这意义上,作者与评论者最好两不相识,否则无法站在一个纯客观的视角思考评判。
张:评论需要一颗正直公道之心。目前,不少评论文章尽管洋洋洒洒却不着边际,在一种机械的操作中失落了心智性灵。更有甚者,不但流于职业吹鼓手的媚俗,更沦为长舌妇式的挑衅,小痞子式的叫阵,没事找事的恶毒;在一片虚假的众声喧哗中走火入魔。
苏:评论者利用作者获利,作者利用评论者成名;评论者与作者同床异梦,心照不宣,成为一种赤裸裸的投桃报李,成为功利主义的联盟。这似乎就是当前评论的现状。
张:好多评论者和作者称兄道弟,卿卿我我,令人发腻。当然一味指责,也不现实。想想看,写几千字的评论,须看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字的作品;写作难,发表更难,发表后稿费又低得让人心寒。在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还能坚持搞评论,已经不易。因此,不好空谈坚守。当代文学评论暴露出的种种弊端,有赖于今后社会体制和文学机制的完善来解决。
危机与困惑
张:你这两年的文风有了变化。从前,你的文风绚丽感伤,浪漫浮华,浓得化不开,那种独特的文体,诗化的风韵,令人惊艳。现在,你的文风是趋于明白如话朴实无华了,原本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和恣肆笔法渐渐转为平和。你近期发表的《驯子记》《桂花连锁集团》《白杨和白杨》等作尤其如此。
苏:我的文风,前几年跟这两年确实不太一样。有些变化连自己都不知道。现在的我,喜欢上了朴素、简单的叙述手法。这种变化蛮玄的,涉及到别人怎么看你的问题。《我的帝王生涯》的想像力,一旦丧失,可能要出麻烦。大家会有两种猜测:一种是既有的风格丧失了,你完了;另一种是承认你的改变,但不接受你的价值。这样一旦失去,将是可悲的。作家历来所谓的“求变”是最不好变的,是危险系数最大的。而不变是死路一条。你可以永远写你25岁的作品,但不能永远以25岁的态度对待文学。
张:你如何看待作家创造力的衰竭?
苏:作家创造力的衰竭是个问题,谁都怕才尽。真要衰竭了,也没办法。
张:在创作生涯中,你有没有一种无时不在的危机感,如同死神不断扇动且迫近的翅膀?
苏:有,一直有。除了没脑子的作家,每个作家都伴随这种危机感。什么样的人能没有危机感?在他写作发表都成问题、文坛不予认同时,恰恰没有危机感。一旦别人认识你熟悉你,危机感也便有了。一个作家的折腾与变化,都是危机感在起作用。
危机感人人都有,大师也难幸免。鲁迅晚年,小说创作出师不利,内心焦灼,免不了有一种危机感。这一点上,西方的一些高龄作家,在60、70岁时,仍然有很好的状态和心态来创作,让人羡慕。像约瑟夫·海勒的《最后一幕》,是他70岁时写的,非常令人喜欢。很难想像一个70岁的作家能写得跟他30岁时一样好,可海勒做到了。这就是一个创作生命力的问题。一个作家成功不成功,老了,仍然是一个标志。
张:中国作家很容易出现创造力枯竭的现象,这可能跟心灵受到较多的外界干扰有关系。
苏:中国作家一旦德高望重,甚至稍有名气,牵涉你精力的职务、会议、事情就多了,很难全身心投入地写作。在西方,作家就是作家,不会因为写作而出人头地。但在我们这里,还存在着得了全国奖当省作协副主席、得了省级奖当地区作协副主席的说法,文人被硬生生地纳入仕途。这是很要命的,它不断牵涉着作家的精力,使一个好端端的原本前途无量的作家的心态被莫名其妙地扭曲;更要命的是它已成为不少文人的人格支柱。这实际也是科举制度以文取仕的潜在反映。在这方面,我们是太形而下了。西方人就比较形而上,没有文人因为成功地搞了文学便可以在仕途发展的先例。
张:这跟中国社会的文化历史传统有极大关系。
苏:不错。唐以诗取仕,宋以文取仕,都不好。科举是很怪的,皇帝老儿亲自主持殿试,文章写得好,就能把国家交给你掌管。我们知道,现在,经常有文章写得好的人人不好。过去就有,像宋之问、秦桧、徐阶、严嵩、阮大铖都这样。文如其人,这是一般规律,但并非绝对正确。文不如其人的情况也经常见到。总之,科举制度是很奇怪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人的文章把社稷江山交给这个人,但他能不能把国家治理好呢?反过来,文人才华不好,国家治理得好的也有,如张居正。我觉得文章是文章,作家是作家,最好不要混为一谈。
张:你当年出道时红透半边天,迄今一直活跃于文坛。俗话说早熟的果子先烂、早开的花朵先谢,你是如何避免这种状态,并使自己在创作中保持不下坠的?
苏:既然下坠是一个必然的轨迹,那么想躲也躲不了。一个作家,想永远保持高峰不可能,唯一可做的是尽量延续你的创作生命。重视心灵的力量,放飞心灵的力量,这就是我保持不下坠的策略。我所能做到的,是使下坠的幅度小一点,下坠的弧线延长一点,或再创一个高峰,让奇迹出现。事实证明也未尝不可,文坛常青树是有的。我希望自己的创作生命中会出现几个高峰。我愿意永远保持在创作抛物线的顶点,并尽己所能多向探索,把单一的抛物线化为多重的抛物线,呈波浪式前进。必要时,我也会休养生息。比如我最近正在阅读中国古代散文,读福楼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我可以连续两个月不动笔,不过超过两个月不写也难受。这点叶兆言跟我很不一样。叶兆言一天不写就痛苦万状。
张:你对自己的创作状态满意吗?
苏:我一直对自己的创作状态不甚满意。我对自己任何阶段的创作,始终都怀有意见。可以说,除了对短篇情有独钟外,对中长篇都有不满。我觉得自己的作品,中长篇有问题,短篇也有为赋新辞强说愁的。根据以往经验,大凡想不到控制,状态良好情绪饱满写出来的东西,往往很满意;刻苦、用功,结结巴巴才能写出一点来的,最后仍然会不满意。一般而言,一气呵成的、三两天时间写完的最好。创作状态对于一个作家,是没法把握和抗拒的。它直接决定着作品的水准。我的创作,从不刻意摆高姿态,那样太累。我只喜欢用语言来讲述故事,讲述一个个好看、好读、打动人的故事。别无他求。
张:现在的作家,真正要养活自己也不容易。难怪好多人要“下海”。对此你怎么看?
苏:目前的稿费制度确实不尽如人意。在港台可以拿到千字千元,大陆就差多了。像我发表的小说,一般是千字60到80元。一些纯文学刊物,比如《收获》《大家》还可以,给我开过千字百元。其他刊物就难达到了。在中国,靠写小说当百万富翁,一般来说是比较可笑的。作家要养活自己不容易。真要逼急了,也没办法,只好触电。《妻妾成群》拍成电影时,版权费只给了5000元。后来《红粉》多一些了,《米》就更多了。目前我的生活状态,养活自己还可以。不然,这15元一包的香烟,我又怎能抽得起。
张:你现在还触电吗?
苏:偶尔为之,也是迫不得已。我老是被人理解为跟影视关系密切,太冤枉了。其实仅仅是出卖版权,整个都没参与。有些影视确实署了我的名字,那是碍不过朋友面子才挂了个策划人。我一般不写剧本。影视剧这玩意儿,也就是客串客串,写多了会把手写坏。这不光是我一个人的看法。一个作家在文学圈内的知名度和他的社会知名度不同。身为作家,还是要坚守纯文学阵地,准确看待自己,看待这种成名的成分的复杂性。
张:最后,我要问的是,你对自己选择的职业满意吗?
苏:既然我已把自己绑在了文学的花车上,就无法终止文字的舞蹈。不太做作地说,写作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作家这一称谓,意味着把我的一生变成文字,把文字变成我的一生。我写作,所以我快乐;我快乐,是因为我写作。
2001年2月28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