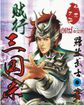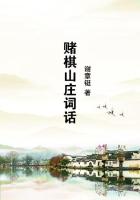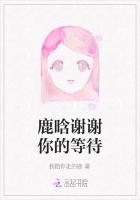英方外交当局和社会舆论都认为,端纳是沟通南京与西安联系的最佳人选。因而,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建议,由端纳飞抵西安,查明蒋介石的人身安全问题。在端纳访问西安的时候,上海英侨所办的《字林西报》有意透露出端纳此行有代表英、美等国探路和调停的信息。它说:“引人特别注意的是端纳先生的调停,将有助于澄清这种局势,并给这次事变带来现实感。”(21)端纳果然不负众望,带回了西安事变的真实消息,对和平解决事变立下了首功。
蒋介石被扣于西安,直接受冲击的是中国的金融市场。而在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民党的法币制度,它是英国人李滋罗斯帮助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外汇本位制”,与英镑直接发生联系。法币对内对外能否稳定,主要取决于英国的态度。当蒋氏被扣于西安的消息传出,法币出现浮动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马上想到了最能帮助他的国家——英国。这时,英政府伸出了援助之手,它指令在上海的汇丰银行,抛出大批外汇,支持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三大银行无限制兑换黄金、外汇,使人们坚定了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信心,从而稳定了上海金融市场。蒋氏被扣的半月中,市价一直保持在事变前一天的水平上,这应当归功于英国方面的支持。
15日,当端纳自西安飞往洛阳,之后又飞往南京的时候,替张学良管理财产的英国人爱尔德亦加入到端纳的斡旋之旅,他们一起面见了中国的第一夫人宋美龄。宋夫人再一次巧妙地使用了英国牌,她嘱咐爱尔德把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在京所谈的敦促张学良和平解决事变的意见电告张学良。就此,许阁森大使说了这样的话:
我不能不感到张的行动只能造成损害,外面世界对他的行动只能解释为一种对他国家的阴谋,即正当团结与进步看来可能实现之际,他在背上给插了一刀。与一个被拘禁的人进行谈判或协定只能是无效的,张学良如果相信他的所作所为是正义的,他就不应怕在自由的氛围中讨论。拒绝这样做,先已宣告了自己有罪。(22)张学良正如宋夫人所希望的那样,在第一时间里看到了上面这些话。对此,张学良为之一震,从事态发展的情况看,他是读懂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些思想的。
西安事变爆发时,美国国务卿赫尔正在南美出席国际会议。代理国务卿穆尔在了解情况后,于14日下午致电驻华大使詹森,详细阐述了美国政府的态度。穆尔宣称:虽然“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不干涉或不介入外国的内部事务”,但是,“如果任何地方的事态发展将危及真正寻求政治和经济稳定的国家的利益,并且会对已经十分微妙的国际局势带来新的危难时,我们都不能漠然处之。”
穆尔指出:西安事变不仅干扰破坏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日常职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带来新的困难,“一般说来还将对在华外国人士、财产和事业带来新的威胁,并将给远东国际纷争带来危险。因此,现在的局势对世界具有利害关系”。
他指示詹森:“目前,我们并不准备宣称或建议与此时局有关的这个或那个政府宜采取任何合适的行动;但是,我们将认真观察那里的发展、并研究有益行动的可能性问题。”(23)美国的上述态度,显然是站在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立场上的。它虽然对西安事变给中国政局和远东地区的影响给予了正确预见,并为随后的干预埋下伏笔,提前告之国际社会特别是中日双方,但对张、杨发动事变的积极因素没有给予正面回应。这是它不了解事变真相的结果。
随后,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在发给国务院的电报中,谈及他对张发动西安事变动机的判断时,再一次因不了解真相而出现误判。他认为,“由于缺乏来自西安方面关于张学良动机的消息”,估计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不外经济或政治的两种:“1.张学良被其东北军中不满的叛乱军官们所控制,他扣留了蒋介石及其下属,目的是迫使中央政府满足其军费要求并对日本采取更强硬的态度。2.张学良同他的部队已经同共产党合作,因而扣留蒋介石及其下属,目的是迫使中央政府停止进攻共产党并采纳共产党方面最近宣布的更积极地反对日本的方针、恢复政府的革命政策,以及对苏俄采取更友好的政策。”(24)随着真相逐渐曝光,美国政府和舆论界对西安事变的估计逐渐变得客观。美侨在上海所办的英文周刊《密勒氏评论报》,在19日的社论中赞同张学良提出的八项主张,但认为“可以采取体面的办法,但扣蒋是严重错误的”。《字林西报》主张国民党可与共产党联合,以保持国民政府不落人亲日派手中。美国政府认为,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是由于“许多中国人恐怕蒋介石将军保存国家实力,为个人统治计,而不用去对日本的侵略抗争。同时也有可能是张学良愿望把远东烽火勃发的可能性,明白指示日本,指示西方。”(25)美方在评价中国发生的西安事变时,始终与可能对太平洋地区均势构成的影响,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相联系。特别担心由此引发日本侵略中国而危及世界及远东均势。《纽约先锋论坛》这样写道:“南京国民政府若依从张学良的要求,承认共产党,日本便要解释为对于日本武力干涉的恳挚的陈情”。而“蒋介石将军所采取的态度是尽可能不给日本以侵略的口实。张将军的政变只能害中国,并引起西方人对远东权益的焦虑”。(26)《民声讲坛报》也发表评论,认为“张学良此次行为,适足以肇害中国,而西方各国在远东保有利益者,亦为之感觉不安矣”。(27)因而,美国政府对西安事变的公开表态,采取的是避免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的做法,即奉行“不干涉他国事务之政策”。而实际上,却采取了与英国政府一致的立场,反对中国内战,主张和平解决。并与英国一起,维护上海金融市场的稳定,赞成英国驻华大使提出的和解建议,并将此建议提交给国民政府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
苏联:被日本列为“北进目标”,担心事变成为对日开战的借口,又面临德、意法西斯威胁,在自身利益驱使下苏方奉行谴责西安事变,主张“和解放蒋”的策略西安事变发生时,苏联正处于险恶的国际环境之中。
美、英在几年前就开始奉行“祸水东引”战略,他们对德国在欧洲的侵略活动,采取绥靖政策,对日本在亚洲的侵略采取纵容政策。这一政策,使社会主义的苏联面临东西夹击的威胁。到1936年,这种理论上的威胁演变成现实。在东方,日本大本营加紧了对苏联开战的准备,开始实施“北进”计划,并在中国北部的满蒙地区进行战略基础储备。在西方,希特勒法西斯在德国上台后,疯狂地扩军备战,企图侵吞苏联。1936年11月,德、意秘密签订反共产国际同盟。同月2日,《日德条约》又告签订。这标志着日、德将正式开始联合对付苏联及共产国际。不仅如此,德、意、日三国反共轴心也进入酝酿形成阶段。
此种情势的出现,苏联早有预见,并已进行了战略应对筹划。苏联认为,应对西部队已经同共产党合作,因而扣留蒋介石及其下属,目的是迫使中央政府停止进攻共产党并采纳共产党方面最近宣布的更积极地反对日本的方针、恢复政府的革命政策,以及对苏俄采取更友好的政策。”(24)随着真相逐渐曝光,美国政府和舆论界对西安事变的估计逐渐变得客观。美侨在上海所办的英文周刊《密勒氏评论报》,在19日的社论中赞同张学良提出的八项主张,但认为“可以采取体面的办法,但扣蒋是严重错误的”。《字林西报》主张国民党可与共产党联合,以保持国民政府不落人亲日派手中。美国政府认为,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是由于“许多中国人恐怕蒋介石将军保存国家实力,为个人统治计,而不用去对日本的侵略抗争。同时也有可能是张学良愿望把远东烽火勃发的可能性,明白指示日本,指示西方。”(25)美方在评价中国发生的西安事变时,始终与可能对太平洋地区均势构成的影响,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相联系。特别担心由此引发日本侵略中国而危及世界及远东均势。《纽约先锋论坛》这样写道:“南京国民政府若依从张学良的要求,承认共产党,日本便要解释为对于日本武力干涉的恳挚的陈情”。而“蒋介石将军所采取的态度是尽可能不给日本以侵略的口实。张将军的政变只能害中国,并引起西方人对远东权益的焦虑”。(26)《民声讲坛报》也发表评论,认为“张学良此次行为,适足以肇害中国,而西方各国在远东保有利益者,亦为之感觉不安矣”。(27)因而,美国政府对西安事变的公开表态,采取的是避免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的做法,即奉行“不干涉他国事务之政策”。而实际上,却采取了与英国政府一致的立场,反对中国内战,主张和平解决。并与英国一起,维护上海金融市场的稳定,赞成英国驻华大使提出的和解建议,并将此建议提交给国民政府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
苏联:被日本列为“北进目标”,担心事变成为对日开战的借口,又面临德、意法西斯威胁,在自身利益驱使下苏方奉行谴责西安事变,主张“和解放蒋”的策略西安事变发生时,苏联正处于险恶的国际环境之中。
美、英在几年前就开始奉行“祸水东引”战略,他们对德国在欧洲的侵略活动,采取绥靖政策,对日本在亚洲的侵略采取纵容政策。这一政策,使社会主义的苏联面临东西夹击的威胁。到1936年,这种理论上的威胁演变成现实。在东方,日本大本营加紧了对苏联开战的准备,开始实施“北进”计划,并在中国北部的满蒙地区进行战略基础储备。在西方,希特勒法西斯在德国上台后,疯狂地扩军备战,企图侵吞苏联。1936年11月,德、意秘密签订反共产国际同盟。同月2日,《日德条约》又告签订。这标志着日、德将正式开始联合对付苏联及共产国际。不仅如此,德、意、日三国反共轴心也进入酝酿形成阶段。
此种情势的出现,苏联早有预见,并已进行了战略应对筹划。苏联认为,应对西线德国的进攻是它的战略重点,它的心脏地带在欧洲,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在这里。因而,它把主要力量摆在了战略重心所在的西线。而对于远东,它认为,日本只有解决了中国之后才能腾出手来对付苏联。也就是说,只要中国抗日,就能牵制日本,减轻它在东线的压力。
这一战略估计不能算错,问题出在其所选择的依靠力量上。在斯大林看来,中国要抗日,只能依靠国民党和蒋介石。大革命时期,斯大林就是这个思路。那时,为了争取蒋介石革命,坚持“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立场,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几乎取消了军事工作,结果在蒋介石举起屠刀、发动反革命大屠杀的时候,导致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受到空前严重的损失。
如今,为了抵抗日本、拖住日本,斯大林再一次片面看重蒋介石的军事实力,而把中国抗日的希望完全地寄托到蒋介石身上。
蒋介石的思想根子是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他不可能为了保卫苏联而去抗日。当年他装出革命的样子,赢得红色苏联的信任,得到苏联的军援,而一旦迅速崛起之后,很快就露出了反苏反共的面目。这一次在蒋介石被扣之后,在他所领导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同样向苏联打出了“日本牌”。
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紧急召见苏联驻中国代办,赤裸裸地威胁说:“西安之事,外传与共党有关,如蒋公安全发生危险,则全国之愤慨,将由中共而推及苏联,将迫我与日本共同抗苏。”(28)孔祥熙这番话的意思是,以共产党与事变有关而向苏联施加压力,希望由苏联出面来做共产党的工作,确保蒋介石安全脱险。
耐人寻味的是,苏联的官方喉舌《真理报》于12月14日发表了一篇社论,就西安事变表示了这样的官方态度,社论竞说:“汪精卫利用张学良部队中的抗日情绪,挑动了这支部队反对中央政府”;张、杨是“利用抗日运动以营私,名义上举起抗日旗帜,实质上制造国家分裂”。(29)也是在这一天,南京国民政府急电指示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指示他抓紧与苏方交涉,敦促莫斯科向中共及张、杨施加影响,使蒋平安获释。蒋廷黻对此项使命颇感棘手,因为前一天苏联“两大报纸同时发表重要社评,用意在使世人不疑苏联与叛变有关。”蒋廷黻深知,苏联希望蒋介石抗日,还不希望他“剿共”。南京如能与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定会受到苏联欢迎。这也正是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前不久秘密会谈时,苏方向蒋介石提出的要求。如果南京能够这样做,苏联定会出手相助,使蒋介石安全获释。于是,在当天傍晚给南京的复电中,蒋廷黻爽快答应与苏联方面尽快交涉,同时建议南京“如能于短期内与西北红军妥协,似亦有补。”(30)接到南京指令后,蒋廷黻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两次会谈,表达了此一意思。蒋廷黻说:“苏联态度不仅影响中国共产分子,即不信共产主义者亦不少对苏联怀好感,至于用何种方式促进解决,我无建议,我所请者即用尽苏联之道德力量。”并说:“南京责成他探明苏联能否除了表示同情以外,再通过其他途径给予援助。”李维诺夫则回答:“我找不到这样的途径,因为自从张学良离东北后,我们与他没有任何接触。”
12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再给蒋廷黻发去“铣电”,令其加紧与苏联当局交涉,注意搜集苏联与西安事变关系的证据,并询问与苏联谈判需付出什么代价等。
17日,蒋廷黻复电南京,建议:停止“剿共”。他强调只有如此,才能得到苏联帮助。并说:“张叛变如与俄无关,则俄不能助我,如有关则俄必索助我之代价。俄望我抗日,亦望我不“剿共”,俄视两者同重,惟不“剿共”尤急,不出此代价必无成。”关于“苏联与西安事变关系”问题,蒋廷黻当时也“无把握”,他提出,张学良在1936年春曾向他透露,“彼主(张)联俄容共抗日”;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回国原因各说不一,“疑其为避嫌疑”,回国后至12月14日才来见我(蒋廷黻),怀疑其“似有意避我”;蒋廷黻赴任中国驻苏联大使时,南京国民政府授之以“全权交涉一切问题”,但苏方“始终推诿”;怀疑张学良有代表驻莫斯科等。蒋廷黻认为,这只是几个疑点,实感“证据不足”。蒋廷黻还建议南京对西安实行“明急而暗缓”的策略,不急于下“讨伐令”,因为“如积极推动军事,院座必有生命危险,且阻碍此间交涉”。(31)从12月13日至17日,南京国民政府与驻苏联大使蒋廷黻的来往电报,以及苏联政府与苏联的所有交涉,基本上都是围绕怀疑苏联政府与事变有关,如何请苏联帮助安全释放蒋介石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