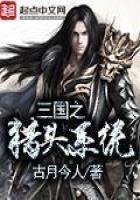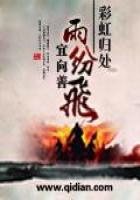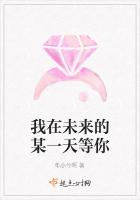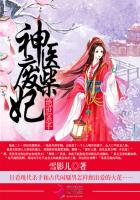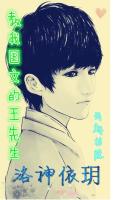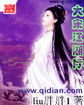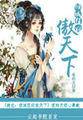回避他所同意的谈判条件,是为了他的领袖面子呢?还是准备日后反悔?毛泽东从他的《通电》和《训词》中洞察到蒋的用意。为了逼迫蒋介石兑现他在西安的承诺,防止他撕毁协定,12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对蒋介石所谓的“训词”进行了剖析。毛泽东评论《训词》“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毛泽东指出:
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末,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以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12月26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
毛泽东在声明中还公布了蒋介石在西安已经答应的六项条件,指出,蒋介石是因为接受了这些条件才恢复自由的,并警告蒋介石:
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将席卷蒋氏以去。(19)毛泽东的声明公开了西安谈判的内幕,使蒋介石企图美化自己、掩盖真情的图谋大白于天下。
受到毛泽东批判的《对张杨的训词》,实际上是杜撰出来的。它的执笔人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陈布雷。蒋回到南京以后,找来陈布雷,由蒋口述主要内容,陈执笔代蒋草拟了这个“训词”。此文写完以后经蒋介石过目,当晚即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用电讯通稿形式向各大媒体发出,27日就在南京国民政府控制的各种报刊上刊登。为了使人们相信《训词》的真实性,发表时所加的按语说:这是蒋介石在离开西安前,亲自对张、杨口授,并由宋美龄笔录下来的。
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假的。因为,释蒋的时间是25日下午2点多张学良约见杨虎城后才定下来的,定下后,已快3点,张学良马上回公馆与赵四小姐告别,而杨虎城也回去作了一些准备。3点30分左右,张学良准时来到高桂滋公馆,而杨虎城较晚一点来到高桂滋公馆,他到的时候已经看到张把扶着蒋走出高宅的大门,准备登车了。于是,他们马上出发,4点钟就到达了西郊机场。也就是说,自定下送蒋时间后,张、杨便没有与蒋会面的时间,怎么能聆听蒋的所谓“训词”呢?
后来,宋美龄在回忆录中对此事的描述,也证实了他们离开西安时是匆忙而紧张的。宋美龄写道:
正焦虑间,子文忽入门,携来喜讯,城防司令杨虎城已同意我等成行矣。张曰:“日去暮矣,曷勿明晨迳飞南京?”余呼曰:“尚欲等候耶?离此愈快愈佳!岂将等候彼之改变态度耶?当知今日为圣诞日。不!决不能做片刻留!应速行,毋再滞疑。”(20)这段文字记述的大概是25日上午的事,因为,宋子文得知杨虎城同意放蒋的消息,而张学良却与宋美龄在一起,这个情况只能是上午因释蒋问题张、杨发生争执后,周恩来让张稍加休息,而自己去做杨虎城工作这段时间。但此时,杨虎城并没有同意蒋几时走,蒋、宋生怕杨虎城改变主意,恨不得即刻起飞,这种焦虑的心情之下,要举行一个从容不迫的告别谈话,显然是不可能的,何况,杨还与周恩来在一起,也没有时间去聆听蒋的训话。
蒋介石在发表《对张杨训词》的同时,打电话把宋子文找来,让宋通知张学良写份“报告”,宋对张学良说:现在各方面说法比较多,委员长也有他的难处。既然来南京了,就写个东西,走个过场,让委员长的面子也好过。
张学良再一次相信了蒋介石。因为,就在一天前,在洛阳逗留时,蒋还告诉宋子文:“你要照顾些汉卿。”当晚,张钫由潼关前来洛阳谒见蒋介石时,蒋还夸奖张学良:“真是东北的汉子。”蒋介石亦与张学良亲谈,不必再送到南京。说:“你就回西安。你若到南京,我反不好办。”此时,张学良以为宋之要求就是走走过场,于是,很痛快地答应了宋子文,给蒋介石写了请罪书。全文如下:
介公委座钧鉴:
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反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文,不能尽意。区区愚忱,俯乞鉴察。专肃。
敬叩。
张学良26日(21)
蒋介石拿到张学良的请罪书后,立即呈报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蒋在呈文中说:
谨呈者:此次西安事变,皆由中正率导无方,督察不周之过,业经呈请钧会(府)予免去本兼各职,并严加处分,以明责任,谅蒙钧察。查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代理总司令职务,而在其管辖区内,发生如此巨变,国法军纪,自难逭免。现该员已亲来都门,束身请罪,以中正为所直属上官,到京后即亲笔具书,自认违纪不敬之咎,愿领受应得之罪罚。中正尤以该员统军无状,尚知自认罪愆,足证我中央法纪之严明,故该员有尊重国法悔悟自投之表示。理合将该员来书录呈钧会(府)鉴核。应如何斟酌情事,依法办理,并特予宽大,以励自新之处,伏候钧裁。(22)蒋介石这个呈文为法办张学良立了案。
张学良却蒙在鼓里,他仍在为蒋介石效劳。在西安放回被扣的军政大员之后,蒋又令宋子文向张提出,放回空军在西安、兰州的70架新式马丁式飞机,张学良表示同意,很快西安方面就放回了这批飞机和驾驶员以及500名地勤人员。
27日,张学良已经发现情况有些不对,但尚不知蒋是幕后“导演”。这天深夜,他致信杨虎城,透露了南京诡异的政治空气。他说:
京中空气甚不良,但一切进行,尚称顺利,子文兄及蒋夫人十分努力,委座为环境关系,总有许(多)官样文章,以转还(圜)京中无味之风,但所允吾等者委座再三郑重告弟必使实现,以重信义,委座在京之困难,恐有过于陕者,吾等在陕心中仍认蒋先生是领袖,此地恐多系口头恭维而存自利也。(23)张学良所谈的能给他提供安全保证的人,此时也被蒙在鼓里。还是27日这一天,孔祥熙去宋公馆回拜张学良,还信誓旦旦地对张说:“要处分,我陪绑去。”28日,阎宝航去西安前去看望宋美龄时,宋还对此前她对张的安全保证说:“我们牺牲一切也要做到。”但当他们知道内幕后,谁也无能为力。蒋介石躲到陈布雷家中,闭门谢客,连宋氏兄妹也不例外,另一个保人端纳则已是自身“难保”。
原来,在严惩张学良的恶浪中,端纳也成为众矢之的,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诬指端纳是奸细,要予以严办,至少也要驱逐出境。端纳本是“救驾”头功,只因为他劝蒋接受张、杨的联共抗日主张,便成为“奸细”。德国军事代表团得知端纳处境困难,立即指派一名上尉到端纳住处,担任警卫,以防不测。端纳知道缘由后便找宋美龄。最后,是蒋介石下令,《中央日报》才发表声明撤销该社论表示认错,并以该报社社长丢官而告一段落。
端纳只是虚惊一场,而张学良可没有那么幸运。
29日,国民党中央召开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处理西安事变有关事项。会议由居正主持。会上先由蒋介石报告西安事变经过,然后讨论蒋介石提请的“西安事变引咎自请处分并请免去本兼各职案”。讨论的结果是,作出了一项蒋介石所期望的决议。决议说:
蒋同志驰驱国事,督教三军,昕夕勤劬,不遑宁息;最近再度入陕,即以(孙)总理大仁大勇之精神,教化部属,统一军心。此次西安事变,事出非常,更能于蒙难期间,持浩然之正气,昭示伟大之人格,使倡乱者衷诚感动,悔悟自白。蒋同志对此次事变,毫无引咎可言。所请辞职,应予恳留;自请处分一节,应毋庸议。(24)接着,中常会举行第32次会议,仍由居正主持。会上讨论蒋介石同一呈文中依法办理张学良一案,这次会议决议:张学良案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第二天,中常会内定李烈钧为审判长,组织高等军法会审,商军事委员会遵办。军事委员会自然按照蒋的意图,确定由李烈钧、朱培德、鹿钟麟三人组审。
给张学良“治罪”终于罩上了一层法律的外衣。
蒋介石挑选这三个人来会审也颇费心机。第一,三人不是蒋的嫡系,没有亲疏之嫌;第二,三人均是资深的陆军上将,与张学良的军衔相当;第三,三人都听命于蒋,不至违背他的意旨。
李烈钧久经官场,知道朱培德与蒋的关系深,不敢轻易与朱商议如何处置此案。他悄悄问鹿钟麟:此事怎样办才好?鹿给出了三策:“问而不审是上策,审而不判是中策,问、审、判全承担下来是下策。”鹿告之李烈钧:“我们应该力争上策,不得已适当地兼取中策,下策万不可为。”
李、鹿商量好的力取上策到蒋介石那里立马变为只此下策。30日晚,李烈钧来到蒋的官邸请求会审事宜。蒋先问李:“审判长对这个案子如何办理?”李答:“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叛逆’行为,有谋害主帅的打算。但能悔改,亲送委员长回京,愿委员长宽大为怀,赦免对他的处罚而释放他。”蒋介石对李烈钧的意见不置可否。这使李烈钧立刻感到“中策”也过不了关,他拿出“下策”向蒋试探:“国民政府既任烈钧出任审判长,一切当以军法办理。”结果,蒋说出“君慎重处理可也”的话,这说明张学良既入蒋之手中已是插翅难逃了。抗日战争时期李烈钧在昆明与人谈起“审张”案时,道出了他的无奈,他说:“那简直是演戏,我不过是奉命演这出戏的主角而已!张汉卿光明磊落,对话直率,无所畏惧。”(25)李烈钧只能按照蒋介石圈定的结果组织审判!
1936年最后的一天,张学良在宋子文的陪同下来到军事委员会军法处接受公审。尽管宋一再解释,审判仅仅是个手续,但张学良心中依然窝火,因为此举对他十分不利,他在国人心目中一下子成为被告,从此他便失去主动权,任凭蒋介石宰割。在候审室,鹿钟麟与张学良握手后说:“汉卿,今天开庭,有话尽管说!法庭内不许携带武器,如身边还有武器,可放在外边。”张说没有武器。
担任审判长的李烈钧,早年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参谋部长。1922年张作霖派人与广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联络,接洽人便是李烈钧。因此,张学良一向把李烈钧视为长辈。此时,看到被告席上的张学良,李烈钧多少有些尴尬。他以张学良是陆军一级上将,又是未遂罪为由,在法庭上为张学良设了专座,并让人代他赶写照例应该询问的被审人年龄、籍贯等项目,以示优待。
上午10点审判正式开始。
李烈钧说:“我们准备了一份向您提问的问题,要你逐条回答。你愿意先看看这些问题吗?”
张学良说:“好,请给我看看。”
李烈钧准备提问的事项一共有8条,如:
不虞危害国民乎?何因出此?
当时你们聚会密谋此事的实情如何?党员官吏向中央提出建议,向来有一定程序,你难道不知道?
你即使有什么主张,理应向中央及蒋委员长陈请采纳,而不日你未曾向中央有所建议,突然发动事变,你有什么可辩解的?
在临潼竞派重兵将委员长行辕重重围困,用机关枪、步枪齐发如雨,是不是有残害统帅之心?
你在临潼劫持统帅,禁闭中央大员,残贤害善,这些行为,你都是首谋,你有什么可说的?
张学良阅后,一一作了回答。关于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张说:
我对蒋委员长是极信服的,我曾将我们的意见,先后数次口头及书面上报过委员长。我们一切的人都是爱国的人。我们痛切的难过国土年年失却,汉奸日日增加,而爱国之士所受之压迫反过于汉奸,事实如殷汝耕同沈钧儒相比如何乎?我们也无法表现意见于我们的国人,也无法贡献于委员长,所以才不得不采用这一特殊手段,以要求领袖容纳我的主张。我可以说,我们此次并无别的要求及地盘、金钱等,完全是为了要求委员长允许我们做抗日准备及行动,开放一切抗日言论,团结抗日一切力量起见。我们认为目下中国不打倒日本,一切事全难解决。中国抗日非委员长领导不可,不过认为委员长还未能将抗日力量十分发扬,而亲日者障碍高过于抗日者之进行。如果我们有别的办法达到我们的希望,也就不做此事了。
关于送蒋回京的感想和到京后给蒋写“认罪书”,张说:
我这次来京,也有三点意见:(一)维持纪律,不堕我中国的国际地位;(二)恢复及崇高领袖之尊严;(三)此事余一人负责,应当得应得之罚,我并无一点个人的希求,一切的惩罚我甘愿承受。我给委员长的信,不知道他要发表的,否则我不写。
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有错。(26)
不等张学良说完,审判长即打断他的话,问道:“你知道你犯的什么罪吗?”
“不知道!”
审判长翻开陆军刑法给张看,并指着“胁迫统帅”条款问道:“你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还是你自己所为?”
张学良从容回答:“完全出于我个人所为,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所做的事,我自己承担,我岂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吗?”
说到这里,张学良反问李烈钧:“现在我想问审判长一句话可以吗?”
李答:“可以。”
张问:“民国二年,审判长在江西曾起义讨伐袁世凯,有这回事吗?”
李答:“是的。”
张问:“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为的是反对袁世凯的专制和称帝,对吗?”
李答:“对!”
张学良理直气壮地说:“我在西安之举,就是为了谏止中央的独断专行……”
张学良此语似是对此时的他无罪而被审的嘲弄。也是警示李烈钧:我张学良是无罪的!
尽管李烈钧深知张学良的苦衷,他来审张也是无奈,但他却不能容忍有损审判长和他本人尊严的言词出现在公堂之上。他再一次打断张学良的话,大声斥责:“胡说!委员长人格高尚,事业伟大,岂袁世凯所能望其项背?你不自省冒昧,演成西安事变,自寻末路,怎能归罪于谁?”
朱培德、鹿钟麟两位审判官见李烈钧大动肝火,怕把事情闹僵,又照顾到李有高血压病,就建议休庭。
复庭之后,又审了几句,就草草宣布结案。
在会审记录呈送蒋介石后,很快蒋就把由陈布雷事先拟就的、以军委会军法处名义发布的判决书,送达高等军法会审判庭,命令宣布判决。判决书说:
本案被告张学良,劫持统帅,强迫承认其改组政府等主张,有该被告之通电可证。至戕害官员,拘禁将领,均系公然事实,虽属其部众之行为,但该被告先实为主使发动,已极明显,自应负起罪责。核其行为,实犯陆海空军刑法第67条第2款前段法第271条第1项、第2项第302条第1项之罪。但查其所犯诸罪,乃系一行为而触犯数项罪名,或犯一罪之方法与结果而触犯他项罪名,应以陆海空刑法第15条、刑法第55条,及陆海空军刑法第67条第2款前段,从重处断。惟被告经奉蒋委员长训责后,尚知悔悟,随同旋京请罪,核其情状不无可恕,兹依刑法第59条,于陆海空军刑法第67条第2款前段,减处有期徒刑10年;并依刑法第37条第2项,褫夺公权5年。
整个审问和判决过程没超过2个小时。